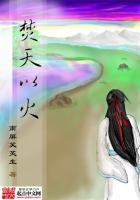屋外似乎下了场雨。
而周围是空气里弥漫着水雾,这四周并不那么的宁静。
施佰春在一堆半干不湿的稻草上睡得正香甜,却被一阵足以撼天动地打斗声吵醒,她极不情愿睁开眼,眼前蒙蒙眬眬地看不太真切,放眼望去一片陌生景象,她惊讶地发现自己不知是在哪个山野间的破庙中,雨从庙顶年久失修的破瓦间滴落布满一层厚灰的供神桌上,扬起些微灰尘。
“这里是哪里呐……”施佰春呐呐地问着自己,有些茫然,完全不晓得怎么会身处破庙之中,之前不是才她好像跟欧意雪在喝酒,然后欧意雪说,“这样你会演的更加真一点”然后欧意雪就给了她一蒙棍子。施佰春在心里十分客气的问候了欧意雪的祖宗十八代。
而这时周围的打斗声越来越近,似乎来到了破庙外头。
施佰春摸索了一下发现欧意如还算有娘心,事先给她准备包裹,把行囊背好,也顾不得自己一身脏乱,施佰春风风火火地冲到外面去看热闹。
双脚一瞪轻轻跃到树上,踏着密林枝干前行,轻盈的步伐偶尔弄落一两片叶,身影动作之迅速,如闪电一般。
雾蒙蒙的弯月挂梢头,天边还飘了点零星小雨,藉着微弱的月光与自身极好的眼力,施佰春看见了底下混乱的景象。
二十来个红衣人隐匿在月色中,无数把兵器举着低着,上头沾了血,血是既红又黑的。
血衣人围起的无形墙中困住了一个人,白色的身影衣袂飘飘,衫子却染了血,血色红中泛黑,唯有白衣人手中那柄银白色的剑没有染到一丝血,即使穿透血衣人的胸膛,仍是未沾到任何血迹,干净得太过了。可见白衣人手里的兵器之锋利,定是一把神器。
从那些血色,施佰春知道白衣人中了毒。她摸了摸下巴,白衣人再这么打下去,没先因血气运行过速毒气攻心而亡,也会因为失血过度去见阎王。
在她思量救不救之间,白衣人率先发现了施佰春的气息,那人抬起头来,晶亮冰冷的眸子对上施佰春的大眼,施佰春眨了眨眸子,不敢相信自己看见了什么。
美人!好一个倾国倾城的漂亮美人啊!眉似青山黛,眼似水波横,眼尾蓝色蝴蝶刺青生动飘然,一剑一舞若凌波,剑锋过处却又似千军万马,凌厉气势浑然天成。
美人、美人啊!美到她下巴掉了合不起来,口水像那滔滔江水不停流。
擦擦口水,可惜又是个女的,一出门就碰到两大美人,可惜哇~都是女人。
欧意雪不是说,她会把弟弟逼到这里来吗?怎么是个女人?又一看,袭击白衣美人的是血衣人不是欧意雪的金甲兵,那么自己也不用管这闲事了。
只是,施佰春一愣,瞧见那双眸子在看她,眼眸美虽美,却少了份柔软多了份轻蔑,目光所及一片冷冽寂寥,像是了无情感的枯槁之人,更像是在鄙视她,这点让施佰春有点小小的难受。
“欧意如,别再挣扎了,束手就擒吧!教主说过死活不论,你不会有机会逃脱了。”为首的血衣人阴阴笑着,手里的利剑毫不犹豫的刺下。
“哼!”美人有骨气,只回一个字,一个侧身躲过去。又与其他几人继续缠斗。
施佰春见美人收摄心神,只看了她一眼便不再有兴趣,便将注意力放回血衣人身上继续挥剑缠斗,然而却只消那么一眼,轻轻的那一眼,施佰春便决定了。
她施佰春怎能任如此美人香消玉殒,此人死不得。
施佰春拿出怀中的药瓶洒下,清风朗月刚刚好,细微的粉末被风一吹,吹到了血衣人阵势当中,施佰春口里喃喃念着:“一、二、三……”
血衣人堆里那个貌似是头领的人发现了她的存在,大声喝道:“何方鼠辈!”
“四、五、六、七!”施佰春眨眨眼睛,砸吧砸吧嘴继续念,直至七声以后,十几个血衣人乒乒砰砰地一个接一个倒得乱七八糟,只有这中间身穿白衣的美人儿还能勉强以剑撑地支持,没有往泥地上贴去。
施佰春笑了一声,从树梢上俐落跃下,踢了踢血衣人首领,惹得那人白她一眼。
“你是谁,胆敢与我血衣教作对。”
“我是你祖宗,我怎么不能和你那什么衣什么教作对。”施佰春摇摇那翠绿的琉璃瓶,笑得那一个叫得意。施佰春特制“七步就倒”,一出场就得了个满堂彩,十九个倒了十八个,而美人儿似乎功力比血衣人深厚了些,一时半刻倒不了。
“你!”血衣人气结,差些说不出话来。
这些血衣人都是江湖第一邪教血衣教门徒,平时别人见他们都是绕道走,只有施佰春这个不知死活的丫头才不知死字怎么写。
施佰春还在得意的望着自己的杰作。
这时,美人儿一双冰眸冷冷看着她,施佰春收起药瓶往美人儿走去,她伸出手想扶一把这个叫作欧意如的美人,没想到对方却举剑一击袭来,招式快狠直逼她要害。
施佰春吓了一大跳,好在对方内力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这招没多大杀伤力,她侧身弹指震飞那把剑,反手顺势扣住对方脉门。
命门被扣动弹不得,欧意如冷然的神情中一抹嫌恶闪过。
欧意如见眼前这人披头散发、浑身又湿又臭还沾满污泥烂草,不知是哪里来的乞丐,但却偏又有一身功夫和诡异迷药。被这样的脏东西碰到,他浑身不自在地起了鸡皮疙瘩。
“放开。”欧意如直欲作呕。
探了探对方的脉象,又察觉对方脸色有异,施佰春随即笑着表达善意,并且松手往后退开一步。
欧意如这时再也抵挡不住“七步就倒”的药力,跌落地上。
当脸贴到雨后泥泞地面,欧意如又是一阵皱眉。
脏死了。灰尘、树叶、泥土、水洼,和一地斑驳血迹。
“姑娘,你身中剧毒。”施佰春蹲在欧意如身前不远处没和他靠太近,望着对方的眼说着:“而且还伤得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