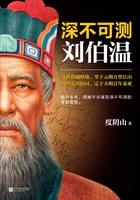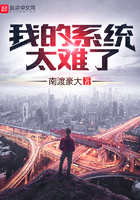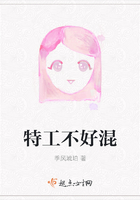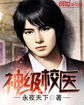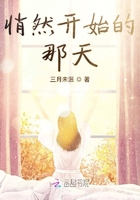1942年考入中央大学艺术系在重庆师从于徐悲鸿的戴泽,毕业后也追随出任北平艺专校长的恩师徐悲鸿来到北平艺专任教,1949年后他成为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
我们的摄制组在采访他时,他对于徐悲鸿当年对北平艺专的改革如数家珍:“他的改革举措有很多。第一个,一年级,不管你将来要学什么,先画素描,这是他的主张。还要做雕塑,制作雕塑,画素描。还有一个,他认为国画系的名字不好,国画只能教国画,油画是教外国画,而徐悲鸿认为这油画也应该是国画,可以画中国题材。绝对不能说光国画是中国画,其他的诸如版画之类都不是中国画,这讲不通,所以他把国画这个名字改作彩墨画,说这种画是用墨跟彩画出来的。他的意思就是说油画也应该是中国画。当时的油画1946年徐悲鸿担任北平美术工作者协会的名誉会长,与协会会员合影被称为西洋画,他想把这个改过来,不要‘西洋’这个名字。”
北平艺专可以说给了徐悲鸿一个舞台,让他充分地推行自己的艺术主张,尤其是对于中国画的改良。但他的举措又并非照搬西方。他有他的原则。为了更好地开展教学,徐悲鸿上任后的第二项改革重点就是聘用有真才实学的知名画家担任学校的教师。戴泽告诉我们,“当时有个照片很说明问题,就是徐悲鸿来北平后组织了一个北平美术作家协会。因为那个张道藩主办了中华美术协会,中国全国美术协会。中国全国美术协会当时是有北平分会的,北京这些老画家都加入了张道藩主办的那个协会,所以他要跟那个协会不一样,另外搞了个北平美术作家协会,成立的时候还照了一张相,那张相就可以说明了艺专的这些老师。”
李桦、叶浅予、艾中信、吴作人、冯法祀、董希文、李可染、齐白石等中国书画界的名家都被徐悲鸿邀请到了北平艺专讲课。其中齐白石应该是年龄最大的,时年82岁。说到齐白石,戴泽回忆起北平美术家协会成立之初的一段往事:“协会成立的时候,大家一起吃了顿饭,齐白石也在。徐悲鸿就来介绍,说这个是谁,那个是谁,最后介绍到我,徐悲鸿就说,说他是我们这儿最年轻的了。我那时候24岁。
于是,齐白石说,如果他是我这个年纪,就跟徐悲鸿学素描。”
徐悲鸿比齐白石小32岁,他们忘年交的友情也是中国美术界广为传颂的佳话。早在1928年,徐悲鸿就曾将这位被美术界视为“山野人士”的齐白石聘为北平大学艺术学院的教授。当年,齐白石孤独地站在北京画坛保守派的一片唾骂声中,唯有徐悲鸿极力赞扬他“致广大,尽精微”,并且力挺他的画作。因为在徐悲鸿的眼中,齐白石笔下那些栩栩如生的虾,停留在残荷上的蜻蜓,看上去毛茸茸、活泼可爱的小鸡,所有这些让保守派瞧不上的东西都是从生活中反复观察得来的。在徐悲鸿的极力推荐之下,前半生一直默默无闻的齐白石,几乎一夜成名。
后来,齐白石曾在一幅山水画中题诗表达对徐悲鸿的感激之情:“最怜一口反万众,使我衰颜满汗淋。”
徐悲鸿的另一个得意门生侯一民于1946年9月考入北平艺专,成为徐悲鸿上任后第一批北平艺专的学生,后来曾担任中央美术学院的副院长。在采访中,侯一民回忆道:“其实当时我是考入国画科的,因为各种原因,很快我就转入了西画科,三年级时徐悲鸿主要教我们这班。徐悲鸿是什么人,我个人,甚至可以说在某些方面是蛮天真的一个人,很性情的一个人。爱画如命,和学生之间比父子还要亲。”
如今已经成为著名油画家、美术教育家的侯一民教授,那时候是名进步学生,加入了北平艺专的地下党。在那样一个时期,在国统区从事地下工作是非常危险的。后来,徐悲鸿挺身而出保护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学生运动的爱国师生,引起国民政府的强烈不满。于是,他们暗中组织画坛保守派发动了1947年的“倒徐运动”,以国画的革新作为倒徐的焦点,因此也被称为“新旧国画之争”。
与1929年那场“二徐笔战”的民主氛围相比,这一次的论争几乎满是对徐悲鸿的个人攻击。北平市美术协会散发铅印传单,称徐悲鸿是美术界的罪人,北平艺专的三位国画教授甚至罢教。北平报纸也将罢教一事大肆宣扬,闹得满城风雨。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种种诽谤,徐悲鸿针锋相对。他召开记者招待会鲜明地摆出自己的观点,并亲自代上三位罢教老师的课,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当这场风波渐渐平息,徐悲鸿的新国画主张也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
1946年,1947年,1948年在北京的一次国画论战,那时候我是亲身体会到的,很厉害。”侯一民教授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说,“中国画吸收西法在中国老画家中间有那么一批人认为大逆不道。徐悲鸿则主张国画要能够反映人民的生活,所以就和那种比较保守的主张针锋相对了。那么试问关于国画改革问题,你今天再回过头来看中国的历史,究竟改革是正确的,还是保守是正确的呢?
侯一民还告诉我们:“其实,这种改革并不是仅从徐悲鸿开始的,在中国美术史上近代一些大画家,包括任伯年、傅抱石、黄宾虹、吴昌硕,还包括岭南的一些画家,差不多都受西方的影响。任伯年画过素描,至于李可染、李苦禅就不用说了,再往后这个问题就一直继续到1957年反右,又给姜峰加上一个罪名,主张画素描就是消灭国画,这么一个观点就被划成了右派,所以中国画的改革问题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从20年代一直贯穿到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而在徐悲鸿的旗帜之下,究竟今天你看胜利者是谁,给人民带来了一个崭新的国画改革,国画革新这样一个潮流是谁推动的,谁首创的?”侯一民说到这里,情绪不免激动起来:“这之后有了黄胄,有了大批的中青年一代的画家,他们走向人民生活,走向大自然,摆脱了那种‘四王’的束缚。当然我们对‘四王’也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虽然这当中可能难免有些否定过头的偏颇,但是从发展上讲,从改革的意义上讲,从进步的意义上讲,徐悲鸿始终是站在改革和进步这一方面的。所以我不说当年是怎么争论,怎么闹,我是从历史发展到今天的现实来看他一代一代的学生做的事情,以及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给抗战带来了什么,给1949年以后人民的思想和生活带来了什么。所以在艺术上,我觉得徐悲鸿这个人在这一点上,他的坚持是有他的历史价值的。”
在当年被围攻的情况下,徐悲鸿为了坚持自己的主张,有时会冒出一些极端的语言,常常被后来推崇现代主义的人抓住把柄,而侯一民却告诉了我们一个真实的徐悲鸿:“他有时候说话很天真,马蒂斯叫做马蹄死,马一脚给踢死了,他有的时候有这种话,但是他也偷偷喜欢很多东西,我有证明。印象派,他不是太主张,因为太贵族化,他觉得印象派的内容对于中国实际国情没有太多可取,但是他对他们的技巧是很喜欢的,他把大量的印象派的画册给我们看。所以他是懂什么叫画意的,但就是不等于他要推崇这个方向。他是这么一个人。”
在撰写纪录片《百年巨匠徐悲鸿》的第三集脚本时,我们也曾感到了一丝困惑。是不是艺术家与政治相关就会在艺术上不再纯粹了呢?
然而,看着徐悲鸿的画作,听到这些历史见证人的口述,让人更加相信,在历史的迷雾中,那个真实的徐悲鸿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他依然是那个对艺术怀揣着最纯真的热爱的画家,对于好的技法他从不会因为不属于自己的主张就一概否定。而他与政治如此紧密的关联也许是他所处的时代与他内心那份救亡报国的情怀相互作用的结果。真不知他若生活在今天,会不会更平静地专注于创作,甚至致力于现代派绘画的研究。因为,新的时代又会有新的信息、新的需求。
“一口反万众”,正是徐悲鸿在坚持信念时最常有的状态,他不是一个事不关己只读圣贤书的文人,不是一个胆小怕事、不敢担当的投机派,他会在关键的时候开口讲话,在认为重要的问题上固执己见,决不退缩。
在他的一生中,徐悲鸿从不屈服,更不向权势低头。而对于自己的学生和子女,他却有着无比慈爱的一面。
在五十出头的年纪,徐悲鸿开始更多地把期望寄托于年轻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