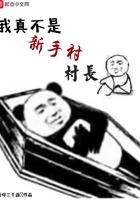有一种痛死不瞑目
虞非子
也是“好人冯二哥”冯亦代先生出版《悔余日录》的那一年,即二〇〇〇年,“一个四十度的大热天”,我的朋友黑马去给冯亦代先生送稿费——黑马的小说《混在北京》重版,将冯亦代的《热闹的黑马(混在北京)》作为代序。二〇〇九年春,章诒和怀着“裂骨锥心之痛”写下《卧底》之后,黑马又想起了那个“大热天”的冯亦代:
那时他刚刚大病初愈,赢弱得不成样子,几乎一阵风都能吹倒他。估计那种健康状况与他决定出版自己的日记后的复杂心情有关。只是,当初他的日记,我们都没仔细看,看了也因为不了解情况,根本不懂……我握着他的手,那手一点力气都没有……我当时只是为他的健康心痛,但不知道他的病痛后面有这样大的精神压力……(黑马《冯亦代先生:又一座丰碑倒了下去!》)也是那个“四十度的大热天”之后不久的一个晚上,“正处在临终关怀阶段”(黄宗英语)的冯亦代接受了一次访谈。当采访者询问他抗战时期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及文化活动提供帮助的“故事”时——冯答:“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讲。”冯亦代沉默了半天,又说:“我做的事都是党让我做的,一些党内的事是不可以公开的。做得不对是我能力有限,是我的责任,但是一开始都是党交给的工作。我只能讲到此为止。”
(张者《文化自白书·冯亦代:相见时难别亦难》)
“沉默了半天”之后展开的这一段话,现在看来,或许可以视为冯亦代对其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那段“卧底”生涯的某种“阐释”——“都是党交给的工作”。
的确,这是“党交给的工作”,但那段生涯却是怎么也不能再“交还给党”便释然的,所以那天的采访者留下了这样一则手记:“冯亦代的痛苦无处诉说,也无法诉说一生的苦难,只能拉着我们的手哭泣……”
所以当采访者请他简单地用几句话总结自己的一生时,他只用了一个宁:“难”。
“难”,难言之隐,隐痛……一九九四年一月十日,冯亦代撰写的《热闹的黑马(混在北京>》“改定于七重天”。文章写道:
“书中的人物虽系虚构,却的确隐藏在北京的忙忙碌碌的人流之中,也许你我身上,都有他们的影子……”而“最妙的是黑马引用了《圣经·路加福音》中的话,作为代题记:
‘父啊,宽恕他们吧,他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意味深长”。
同样意味深长的是,就在“改定”这篇“书评”前十四天,冯亦代写下了《记前纱络胡同》,回忆了他“卧底”时期的旧居——“清时权贵的马厩”:
一九五七年“祸从口出”,原来住的美轮美奂的房子,终有一天被“勒令”搬家……我原来的住处,有三间大房,容得我历年收罗的书籍……新居之湫隘,简直出乎意外:一家四口的住处,不过是一间不到十平米和一间可以容得一床一桌二椅的地方大概是因为有些“党交给的工作”“到死也不能讲”的缘故,一九九三年岁末的冯亦代,在这篇文章里特意将这段“卧底”生涯“翻译”成了“蛰居”生活:
我那时家居养病,一清早听见邻家有人在催取牛奶,便醒了过来,晚上则挑灯夜读,直听到叫卖夜宵声过了,才熄灯就寝,真是“日出而读,夜深而息”……这就是我蛰居胡同的现实。
以后成为摘帽右派,调了工作,住进了二居室的宿舍,邻近胡同,但与胡同里的四合院大不相同:幽居的情趣,便成为过眼云烟了。但我总不能忘掉前纱络胡同,偶有闲时,便到那里去踯躅一番……从冯亦代“翻译”出来的“幽居的情趣”看,他“偶有闲时,便到那里去踯躅一番”是出于怀念,但透过“原着”《悔余日录》,透过“一前一后”收入《归隐书林》一书的《记前纱络胡同》和《热闹的黑马(混在北京)》,却可知他“踯躅”时口中念叨的多半便是很多年之后“沉默了半天”所说的:“我做的事都是党让我做的……”耳边回响的则是“父啊,宽恕他们吧,他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踯躅”着,是因为终于知道自己曾经做了什么——无论是以谁的名义,甚或某个组织,乃至于国家、人民的名义,任何行为的道德责任最终都要由具体的实施者个人来担当,哪怕不是全部的责任,因为这毕竟是“我做的事”。
有一种痛,时间也无法治愈,或许,只有死亡能让痛者“解脱”。冯亦代的“踯躅”、发表《悔余日录》便是源自这样一种痛,一如“把床第之语,也当作政治言论,拿到大会上去揭发”的浦熙修,在临近生命终结时向组织上要回罗隆基给她的十几封私人信件一样。
有一种痛死不瞑目。章诒和的“裂骨锥心之痛”或许也是,因为那一段“深情厚谊以及那笑脸后面的一片慈祥”的后面竟是但这种足以将人“击倒在地”的痛,无论对冯亦代、浦熙修,还是对章冶和,终究也是一种觉醒,所以章诒和的《卧底》是这样结尾的:
……成功的光环无法销蚀有耻有痛的记忆。一个人不论你做过什么,能够反躬自问,就好。
从抢记王芸生临终回忆说起
林谷
最近读了一本由王俊义、丁东主编的《口述历史》丛刊(第一辑),其中一篇题为《临终片语:所谓“反苏”》(王芸生口述,王芝琛整理并注释)的材料引起我的注意。王芸生先生(1901-1980)是我国着名报人,也是我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之一,历任《大公报》
编辑、编辑主任、总编辑、社长等职,并长期参与和主持《大公报》笔政。他撰写的《大公报》社评视野开阔、气势宏大、充满爱国激情,有很强的感染力,例如他写于抗战时期的文章现在拿出来重读,还会让人激动不已。王芸生的文字还有一大特点,即深厚的历史沧桑感。由于他坚持独立办报原则,不为党派观念所左右,也不受市俗利欲所驱使,因而能冷静、公正和如实地反映历史真貌,并针对发生的种种历史事件发表看法,所以,他的文章本身就是一部活历史,一个民间舆论思想库,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同时,他还有长期写日记的习惯,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起,四十多年从未间断,被人视为“中国近代史见证”。遗憾的是,这部极为珍贵的日记竟在“文革”风暴乍起的一九六六年,被他付之一炬了,真是让人痛惜。后来,他的老朋友赵朴初、程思远等先生一再敦促他将自己的一生经历回忆写出来,好作为一份珍贵史料留给后人,他自己也有这样的心愿,但这件事却拖延着迟迟未能实行,直等到他临终(一九八〇年五月三十日去世)前几个月,才就他的一生经历跟他的公子王芝琛讲述,这就是由王芝琛记录整理,但至今尚未出版的王芸生口述传记。《口述历史》丛刊登载的只是王芸生口述自传的一小部分,主要讲他在反右运动中被初定为反苏型右派(后因毛泽东开恩未予戴帽)的经过,并进而披露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苏军出兵东北后大肆掠夺和阻挠国军收复东北的历史真相。王芸生口述时已经是风烛残年,但他的记忆力仍相当好,一些扑朔迷离的历史纠葛经他一讲,就变得面目清晰起来,而这些问题却长期被有意无意遮掩着,恐怕至今还有很多人给蒙在鼓里。关于当年苏军在东北拆走大量机器设备并奸淫妇女的情况,我少年时也曾耳闻。那时抗战宣告胜利不久,我正在天津上初中,忽然有一天学校里来了一批东北大学生,他们向同学揭露苏军在东北的种种劣行,我们听后都很气愤,事后天津各校学生还上街游行,以示抗议。
但这件事到解放后却有了新的说法,好像苏联从东北搬走一些机器也算不了什么,而对此持有非议的却是“反苏”了。
那么,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呢?让我们来听听王芸生是怎么讲的:“要说蒋介石真是吃了个‘哑巴亏’,他冒着当‘卖国贼’的风险,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让苏联占尽了便宜,只求得他们进东北打日本,他们进来了,日本已投降了,国民党蒋介石非但没有得到他们的帮助,还被他们拒之于东北大门外。中苏盟约订明,苏联要帮助中国的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而实际上他们事事处处帮助共产党,使共产党一下子在东北组成近三十万人的东北民主联军。”王芸生还指出,苏军进入东北除了把许多重工业机器宣布为“战利品”外,还大量发行所谓“军用票”,大肆搜刮中国人的财富。二〇〇五年七月出版的《苏联出兵东北始末》(人民出版社)一书对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有十分详尽的叙述,一些资料正好用来作王芸生口述的注释。当年苏军从东北到底拆走了多少机器设备,又交给中国共产党多少武器弹药呢?该书披露:据当时重庆考察团调查,苏联拆走的东北工业设备价值达八亿五千八百万美元,如果加上拆装损坏的部分,则高达二十亿美元。一九四六年一月苏军还拆走嫩宁铁路一百八十公里的铁轨,而这条铁路在日本侵略东北前就已存在,是中国人自己筹建的,根本算不上日本资产。又据杜鲁门派遣的美国调查团的调查,苏军拆走的东北电力设备达一百万以上千瓦,占东北电力设备的百分之六十五。此外苏军还从银行掠走价值三百万美元的金条和五千多万的东北货币,并在东北发行了十亿元的军用票,用以套购黄金和其他物资。至于交给中共多少武器弹药,该书也提供了一组数字:除曾克林率领的十六军分区拉走的一批武器弹药外,仅苏军第一、第二方面军交给中共军队的武器弹药就有三干七百门大炮、阻击炮和掷弹筒,六百辆坦克,八百六十一架飞机,一万二干挺机枪,六百八十座仓库和部分舰艇。此外,苏军还从朝鲜运来两军列武器交给了中国共产党,又从大连向北满中共军队送去五十节车皮的武器,用这么多先进武器装备起来的中共军队真是如虎添翼,已有足够力量与国民党一争天下了。过去我们读中国现代史“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即解放战争)这一时期,总会碰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的军事较量为何能这么快即见分晓,仅仅用了两三年的时间就把一个有美国佬支持的国民党政府打翻在地,其原因何在?一般历史教科书及有关着作都从人心向背,毛泽东战略战术英明或国民党腐败无能等方面来分析,但对当初苏联出兵东北后对中共军队的大力帮助却避而不谈,或许这顶多是个外部因素,不值一提吧。但是,王芸生却大胆地讲出自己的看法,他说:“国共两党打内战,最后共产党把国民党蒋介石赶到几个小岛上去,咱们这边说,是小米加步枪打败美国的飞机加大炮。
我的看法是:苏联的帮助起了重要的作用,把东北拿下了,其他都好办了。”王芸生讲这话时大概已知道自己离大限不远,对讲真话会带来什么后果已无须顾忌,历史的力量在真言,王芸生临终话语之可贵正在其真。
“文人论政”是王韬、梁启超开创的报业传统,王芸生与张季鸾、储安平等人一样正是这一传统的忠实实践和扞卫者。可惜,由于形势剧变,制度更易,这一优良传统也不得不戛然而止,从此,我们再也听不到王芸生那忧国忧民、慷慨直言的声音。但这次读王芸生的《临终片语》却有一个小小的发现,想不到从这位已不久于人世的老人口中,又听到早已沉寂的议政话语,不过,这只是对亲人讲的窃窃私语,声音显得有点微弱罢了。王芸生临终前的时政批评涉及政治民主、对外关系,以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权状况等。关于民主问题,他说:“咱们这边经常嘲笑美国的议会民主是假民主。我认为美国确实有的地方似乎有表演性质。咱们这边对美国批评并没有全错,但不管怎么说,他们重大事情都要由议会多数通过,这一点比我们这边强。‘文革’中,毛主席最新指示一发布,全国无论男女老少,不管你在做什么,都得马上表态,马上上街游行,表示拥护。……‘文革’中,所谓的‘民主集中制’
简直成了‘帝制’。山呼海啸,九叩六拜,蔚为壮观,英国女王、日本天皇也都只能叹为观止,甘拜下风!”王芸生这段有点辛辣的批评虽然是在二十多年前讲的,但今天听来,也并不过时。封建专制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它像个幽灵长久地徘徊不去,要想彻底铲除它谈何容易,例如神圣的“人权”二字虽已堂而皇之写进宪法,不还是屡屡发生余祥林杀妻冤案一类的事吗!中国有句老话是“良药苦口利于病”,这些话真值得好好听听。
关于对外关系问题,王芸生的议论也是我们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且听他如何道来:“记得我就听了不少‘反修报告’,声称苏联不行啦,变修了,咱们毛主席要举起国际共产主义大旗,我看咱们主席有点当仁不让的劲头。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咱们送给全世界强大的思想武器,不外乎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小米加步枪’、‘游击战加运动战’。
……其实咱们这一套,在国际市场上买卖也有限。说句难听的话,还对世界和平起个‘搅局’的作用。”历史的发展正如王芸生所指出的,我们勒紧裤腰带竭力支援的那几个“小兄弟”:如今都哪里去了。
王芸生还谈到解放前他为何犹豫未去解放区的问题(实质上是对人权状况的一种间接批评),这对研究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历史转折时期的思想也颇有价值。
他说:“关于苏联内部情况,我也略知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