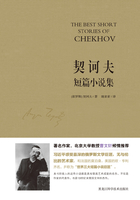“真是人心隔肚皮呀,鬼知道他把我们的粮食偷回家了多少呀!”
社员一经发动起来,群情激昂,众口一词,一口咬定是我父亲偷了保管室的苞谷,不让父亲开口,不容父亲分辩。
邓书记几次开口,说要调查清楚后才能下结论。但他的话都被打断了。何必为更是把手指指上邓书记的鼻子捣上邓书记的脸。指责邓书记是“捂盖子”、“护短”、“包庇”、“放纵坏人”。
在人们的讨伐声中,父亲一声不吭,双眼在保管室内搜索着。突然,他的眼神落在那扇门上不动了,定格在那扇门上了。
邓书记发现了父亲异乎寻常的眼神,也朝那扇门望去。
父亲朝邓书记望了一眼。邓书记好像从父亲的眼神里看出了什么,微微朝父亲点了一下头。
父亲朝邓书记也微微点了点头,一转身就冲出了保管室。
何必为高喊:“曾明俊,别跑,跑是跑不脱的呀!”
社员们也一齐跟着吼叫:“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们到他家里去搜呀!”
邓书记已胸有成竹,大吼一声:“都给我闭嘴!等着看事实吧!”
邓书记走出保管室,紧随父亲进了隔壁的那间教室。那间教室门上的铁锁早已不翼而飞不知去向了。
社员们也一齐拥进了那间教室。
进了教室一看,人们顿时傻眼了,只见那扇门下有不少苞谷,门的半腰有个新钻的洞口,大拇指可以伸进去。苞谷就是从这个洞里源源不断地流出来的。
何必为见了,慌忙改口说:“真是外面的强盗偷的呀!这强盗也太猖狂了呀!险些把老曾给坑害了呀!”
邓书记朝他狠狠地瞪了一眼。
我发现何必为有些慌乱。
父亲仔细地搜寻着那扇门边的一切。他突然发现苞谷里面有个光闪闪的东西。他走过去,扒开苞谷,看见了一枚毛主席像章。他拾起那枚像章,我们也看清楚了。那枚像章是正方形的,别具一格,特大,金光闪闪。父亲把那枚像章看了又看,然后交给邓书记,小声地对邓书记说:“我们生产队只有一个人戴过这种像章。”
邓书记一听,心里就明白了。
邓书记从我父亲手里拿过那枚像章,用手高高举起,说:“社员同志们,请你们仔细看看,你们看见过这枚像章没有呀?”
社员们一起伸长脖子,看了看邓书记手中的像章。
邓书记又大声问道:“你们见过这枚像章吗?”
几乎异口同声:“我们看见过!”
邓书记跟着问:“你们在哪里看见过呀?”
不知是谁先说出了声:“何组长一直戴着这样的像章。”
邓书记走近何必为,问:“何组长,这枚像章是不是你的呀?”
何必为乱了方寸,语无伦次,“这,是,不,不是。现在有哪个人没有像章呀?像章又不是我一个人才有的。您怎么独独只问我一个人呀?”
有个社员说:“何组长戴着这枚像章在我们面前炫耀过,他说这种像章在我们县就只有他这一枚。”
邓书记问何必为:“有这么回事吗?”
何必为强作镇静:“有是有这么一回事,我那是同他们日白的,哪晓得他们还当真了呀!”
邓书记跟紧追问:“你那枚像章呢?怎么没戴起呢?你不是说,忠不忠,看行动,像章从来就没有离过你的身吗?”
“我舍不得戴,把它收藏起来了。”
“收藏起来了呀?这么好的像章不戴在身上多可惜呀!我跟你一起到你家看看那枚像章,饱饱眼福啊!”
何必为惊慌失措了,“这,这……”
邓书记不动声色,说:“老何呀,你就不要这呀那呀的推让了呀!走吧,耳听是虚,眼见为实呀!”
邓书记把何必为的手一拉,说:“我们走吧!”
何必为耷拉着脑袋,跟着邓书记往他家里走去。
邓书记进了何必为的屋里,一下子就发现了堆在床底下的几大口袋苞谷。邓书记指着苞谷问:“何必为,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呀?”
何必为终于低下了头。
事实终于真相大白。
何必为引火烧身,斗争的矛头一下子就转向了他。
邓书记让我把社员们召集在一起。他当众宣布:“今晚召开群众大会,开展大批判!”
父亲握住邓书记的手,说:“邓书记,您给我洗冤了!”
邓书记说:“我还不知道你呀!一开始我就没有怀疑过你。没想到贼喊捉贼,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呀!”
社员们说:“害人终害己呀!”
我真想补一句:“墙倒众人推呀!”
父亲笑了笑,他那是苦笑。他哪里是笑,分明是在哭呀!
邓书记握住父亲的手,说:“你想开点,乌云是遮不住太阳的。”
父亲喃喃自语道:“毛主席又救了我呀!”
谁也没听懂父亲的这一句话。
只有我听懂了。
天有不测风云,父亲真是祸不单行。
母亲的病情加重了。
母亲实际上已病了好多年。
几年来,父亲带着母亲求医,翻山越岭,涉水过河,走遍了大半个县,找了十多个卫生所、医院的医生为母亲看病。父亲找过的医生也都为母亲诊断了,也都为母亲开了药。有的医生开的药喝了,开始几天似乎还有点效,但过了几天后又将病还原了。有的医生开的药根本就没有效,喝的药就跟喝了白开水一样,没得一点儿反应。眼见母亲的病日渐严重,父亲心里更加着急,忧心如焚。父亲不会放弃,他没想过要放弃,就是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他也要去争取。他要让母亲到我们县最大的医院去看病。他借来队里的板车拖着母亲,去了那家医院。在医院里,医生给母亲作了检查后,把父亲拉到一边说:“我也不瞒了,直话直说,你妻子的病很严重,是子宫癌,也就是农村常说的崩病,已经到了晚期,在我们这里是无法治愈了。你还是要早些有一个心理准备呀!”父亲没有办法,只好又拖着母亲回家。
回到家,父亲又急又愁,他还不能把病情告诉母亲,那样会加速母亲的病情恶化。他强忍痛苦,装着无事一般,把医院抓的药,熬了给母亲喝,还安慰母亲说:“你就安心休养吧,医生说不要紧,只要坚持喝药,你会慢慢好起来的。”母亲说:“真是辛苦了你,里里外外你一人忙进忙出。唉,老天爷真是不睁眼哪!我躺着,你就不要管我了,去忙你的吧。”
“嗯。”父亲答应一声就出了门。
父亲是去找刘队长的。
见到了刘队长,父亲说:“刘队长,月芬已经不行了,医生要我准备后事,我想先给她把枋子做起,想请队里批一副枋子的杉树。”
刘队长没说长短,给父亲批了十六根杉树。
批到了木料,父亲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父亲不想让母亲知道批木料做枋子的事,就请人帮忙砍了木料,请来了做枋子的木匠,悄悄在生产队保管室里做。枋子做好以后,又去弄了漆,请来漆匠师傅,把枋子刷了一遍。刷好漆以后,就把枋子放在了保管室里。
父亲还是不甘心,不死心,特别是那天枋子做好以后,枋子木匠对父亲说:“老曾哪,其实你不必这么赶忙做这副枋子呀!”
父亲忙问:“那为什么呀?”
枋子木匠说:“我们枋子木匠都有一个秘密,一个绝窍,只要我们一动斧头,就知道这副枋子的主人睡不睡得上。”
父亲追问:“是什么秘密和绝窍呀?”
枋子木匠说:“这是不能对外言说的,否则,上天就会惩罚我们!你也不必问了,只要知道你妻子用不上这副枋子就行了哪!”
枋子木匠的话也许是随口便道,也许是自我吹嘘,或者是对父亲的一种安慰。然而,枋子木匠的话却点燃了我父亲的希望之火。
听了枋子木匠的话后,父亲便四处打听医术高明的老中医。功夫不负有心人,父亲终于打听到,一百多里路外的天柱山上有一位老中医,八十高龄还在行医。听说,找他看病的人接二连三,络绎不绝。不少被别处的医生判了死刑的人,他都起死回生,把人救活了。人们都说他是华佗重生,神医再世。父亲听了,心里为之一振,顿时充满了希望。去天柱山没有公路,老中医住在山顶上,与云雾作伴,同禽兽为伍。去他那儿,只能步行,还要有胆量。父亲为了治好母亲的病,他什么都不怕。他用背架子背起母亲就上了路,走了两整天才上了天柱山的山顶,找到了那位老中医。老中医听父亲说背着母亲走了一百多里路,很是感动,就急忙地给母亲看病,老中医看了母亲的病后对父亲说:“我给你妻子开了三服药,你对妻子的真情会感动上天的,菩萨老爷会保佑你们的!喝完我弄的这三服药后,你妻子的病应该会好的。万一不好,我说的是万一,你也就不必来找我了!”
父亲千恩万谢告辞老中医,又背起母亲下山了。回转时,父亲归心似箭,他要让母亲早点把药喝下去。只一天一夜,他背着母亲到家了。
一回到家,父亲就架火烧水,找来煨药的陶罐,把药倒进罐里,再倒进开水,放在火里煨开了,提起药罐给母亲倒了一大碗。
母亲一口气把药喝下去了。
喝了三餐,母亲的气色转好了。
喝了三天,母亲的脸上变得红润了。
喝了三服,母亲的病症完全没有了。
母亲病好了,全家欢喜,父亲更是喜上加喜,也就嘴无遮拦了,说:“月芬呀,真把我急死了!现在总算好了哪!你不知道吧?我连枋子都给你做起了呀!”
母亲很感激父亲,嘴里却说:“你还不是怕我拖累了你,想我早点死呀!”
父亲说:“你瞎说!”
母亲说:“你不想我早死,你怎么就想到给我做枋子的呢?”
父亲说:“眼看你只剩下一口气了,我能不作最坏的打算吗?”
母亲说:“我跟你说得好玩的呀!”母亲停了停又说:“没想到我到了鬼门关前,死鬼子不让我进去呀!我被他们硬是赶了回来呀!”
彤华说:“妈,您说得不对,不是死鬼子赶您回来,是爹把您救了回来呀!”
母亲笑着说:“我晓得!没有你爹,我早就到阎王爷那里报到了哪!”
保管室被盗事件之后,我继续在我们大队工作了半年。接着就发生了很多我不曾料想到的事情:
县文化馆换了新馆长,杨馆长调到一所乡下中学当校长去了。新馆长也姓杨,是同老杨馆长对调过来的。新杨馆长上任后,向全馆宣布了“两不准一必须”的大政方针,即:不准用公家的时间搞私人的创作;不准用自己的名字发表作品,只能为工农兵代言代笔;群众文化必须为中心工作服务。因为农村路线教育是当时最中心的中心工作,因此,我被抽调到农村路线教育工作队。我被安排到我们区同湖南交界的南岭上的一个大队搞路线教育,成了农村路线教育工作队队员。
我离开我们大队不久,我们大队也派来了路线教育工作组。路线教育工作组到我们大队不久,说邓书记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背离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带领群众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摘了他的乌纱帽。项会计被工作组指定为支部书记。我所在的小队队委会因放任资本主义泛滥被一锅端了,让人意料不到,也无法理解的是何必为当上了生产队队长。刘队长和父亲被撵出了队委会。
工作组进大队后,高举阶级斗争的大旗,在我们大队大抓阶级斗争、大批资本主义、大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声势浩大,轰轰烈烈,深入开展了路线教育运动,成了全县路线教育的先进典型。全县在这里召开了现场会,大队党支部项书记和工作组组长作了典型发言,县广播站组织了专题报道。
路线教育抓上去了,农民的阶级觉悟提高了,农业生产无人抓了,田里的庄稼荒芜了。农民见了心里就有气,都敢怒而不敢言。忍着没做声。下了台的刘队长却忍无可忍了,他指着田里的庄稼气愤地说:“这种的什么田呀?草比庄稼长得还高,稗子比稻子长得还旺,这人是吃草还是吃粮食?是吃稗子还是吃稻子?”
这话不知怎么就传到工作组长耳朵里去了。工作组组长姓左,一个如日中天、正当红的姓氏。社员们知道他姓左,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想知道他的名字,左组长三个字如雷贯耳,在我们大队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听到了刘队长讲的话后,大发雷霆,说这是阶级斗争的新事实,是下台干部的新反扑,是反社会主义、反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新动向,必须反击,必须批判,在全大队开会批判刘队长。左组长在批判大会上说:“我们就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稻子!走资本主义道路会掉脑袋的。饿肚子总比掉脑袋好呀,所以,我们宁可饿肚子也不要搞资本主义!”项书记强调说:“左组长的话是真理,我们要坚决执行左组长的指示,辨明大是大非,认清形势,端正思想,坚决走社会主义不动摇,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线路不动摇!”
闹腾了三个月,我们大队的路线教育总算结束了,工作组凯旋而归了。路线教育无论怎样开展,开展到什么时候,十年,二十年,甚至一百年,却改变不了农民的命运。农民依然还是要种地、锄草、施肥、收割,日出而作,日没而息。路线教育结束了,田里的稻子也黄了,工作组一走,社员们就全力投入到抢割稻子的农忙中。
曾家畈有一畈水田,三十多亩,那是我们生产队的当家田,旱涝保收田。可现在却是大减产。朝那里一望,凡是种田的人哪个不痛心哪!满田满田的稗子没有扯过,稗子比稻子长得还高还饱满。割稻子要在稗子里面找。这样割稻子,曾家畈人还没有这样的经历。
割稻子那天,天上乌云密布,阴沉沉的,风雨欲来。
那天,春燕也被叫去割稻子。
何队长站在田坎上催工道:“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割稻子也是革命,都要鼓足劲,抢在雨下来之前,把稻子收割完。”他发完话就走了。
社员们在泥泞的水田里,一把一把地割着稻子,你一言我一语地发泄着怨气:
“草是社会主义,庄稼倒成了资本主义!”
“这一块田,只见稗子不见稻子,怎么割呀?”
“稗子当不了饭吃,却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的稗子再长不得了呀!”
下了台的刘队长听了,忍不住劝大家:“大家不要发牢骚了,发牢骚也没有用了。今年肯定是大减产了,你们发再大的牢骚也增不了产哪!还是面对现实吧,大家都加把劲,把稻子收割完,免得耽搁了今年的冬播,影响明年收成呀!”
大家听了刘队长的话,“唉”了一下就不吱声了,集中精力地割着稻子。
春燕是第一次下水田割稻子。她才学割稻子,生怕割慢了,就格外加了把劲。她头不抬,手不停,一股劲地往前割。不一会儿,她就满脸流淌着汗水,头上的汗水流进了眼里,眼眶里涩涩地。她用手背去擦了一下汗,汗还在不住地流淌着。她不管它了,用一只手扒开稗子,一只手用镰刀去割稻子。她虽然是第一次割稻子,却并没落在人家后面,割在她前面只有几个人,那几个人中有父亲。她要追赶上父亲,父亲也在不断地回过头来地望望、笑笑。她加劲地挥舞着镰刀,拼命地追赶着前面的那几个人。眼看快要追上了,她忽然“唉呀”的一声惊叫。割稻子的社员一齐把目光投向她,问道:“春燕,怎么啦?”
父亲扔了镰刀,跑到春燕身边,着急地问:“怎么啦,春燕?”
左手指被镰刀割了。她抬起来,大家一看,见她食指、中指都被割破了一个口子,鲜血直流。她慌忙用嘴捂住刀口,鲜血又从嘴角流了出来。她又连忙用另一手紧紧捏住伤口,鲜血又从手指缝里流了出来。
父亲见了,着急地说:“春燕,这不行,赶快去卫生室找赤脚医生去弄药。”
社员也都催促道:“春燕,快去!弄了药就回家休息。伤口怕水,碰到了水,容易感染的呀!快去!”
春燕急忙奔向卫生室,沿途滴下了点点血迹。
到了卫生室,卫生室的赤脚张医生拿起春燕的手,看了看,就用酒精棉球给她擦了擦,止住了血,抹了些紫药水,就说:“不要紧,没事了。千万不要让生水碰到手上的伤口呀!”
春燕看了看手指上的伤口,不放心地问:“不敷别的药啦?不要包扎一下呀?就这样能行吗?”
张医生说:“你的伤口不大也不深,不会有问题的,你放心好了。”
春燕只好离开卫生室。
她没回家,又要下田去割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