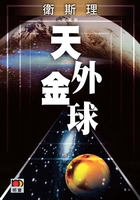自从那件事情发生之后,连续几天姑姑都不敢做肉食在桌上。他也不知道如何安慰妹妹,如何让妹妹摆脱这种处境。他去问了问医院里心理科的医生,那个老人说,不要太在意这些,过些时间就会好。这像是可以给人安慰的句子,但是潜意思,其实根本就是没有什么好的措施。时间,总觉得只是说得简单,就像描绘生存,似乎很简单的词语,但是当活在生存中时,却并不是像口里说的那样容易。
他坐在值班室里,洛兰没有和他在一起,或者说,洛兰今天根本就没有来医院——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只是因为正好轮到她休假而已。
他盯着值班室窗户的方向,注视着每一寸飘过的尘埃,似乎担心有什么藏在那里。
已经到了中午的时候,他想去买点什么吃的,就当是中午饭,但是现在只有他一个人在这里,要是离开总有些不方便。不过过一会儿,护士长就应该到了,本来今天是没有她的工作的,但是她执意要来一趟看看,倒不是放心不下自己一个人留着,她是翻了翻关于病人的簿子,才决定今天来的。当她走后,他也将那簿子拿来翻看,并不厚的名单,记载的都是些哪个病人什么时候要换药,什么时候要挂点滴之类的东西,他也看过很多遍,而且有些病人的治疗信息他已经记得,但现在,他还是想拿来看一看。
其实他一直有些疑惑,在这个簿子上并没有出现袖未的名字,不只是这个簿子上,只要是他能够看见的关于病人的信息,都没有这个应该很显眼的名字。大概就是像洛兰说的,“不要接近狐家的人”这样的句子,显得比较好解释,既然不要接近,就干脆将她剔除,避免出现她的名字,或者,干脆就当她不存在的好。
似乎今天要换吊瓶的很多,换药的似乎只有两个,一个是被烫伤的叫莫卓的人,还有一个,就是走廊尽头的那间病房住着的,眼睛绷着纱布,或者更确切点说,是脑袋绑着绷带的人。似乎,那穿透耳膜的嚎叫还在耳边留着余音。
对了,莫卓,就是妹妹学校的那个老师,之前碰到的,和姑姑在一起的那个。他笑着,虽然没有说过什么话,但似乎和姑姑是熟人,这样对于他也可以算是个熟人了。
这个莫卓的换药是交给他来进行的,但是似乎护士长没有向他提过要帮那个眼睛绑着纱布的人换药,不知护士长要在自己休息的时候赶来这里,是不是就是要亲自给这个病人换药。大概给这个病人换药,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若介。”值班室的门被推开,护士长已经走了进来。
“帮我准备一下胶带、医用棉和医用纱布,还有双氧水和止血膏。”护士长的步子显得急促,似乎在为什么着急,“我去倒热水和准备毛巾。”
热水和毛巾?似乎这不是这个时候应该出来的东西。
果然,护士长是走向那个走廊尽头的房间。他将托盘放在了一旁的桌上,护士长拉来一个椅子坐在床旁。
“你先出去吧,这里有我就好。”护士长说,“等下说不定莫卓会来,你去稍微等一下。”
他点了点头,将门轻轻合上。
护士长向着门前回头。他稍微走离门上的窗口。
安静的病房,安静的走廊,一切仿佛都在屏息。不是屏息,似乎是什么浓厚的气息堵住了鼻子,堵住了喉管。或许是凝固的空气,或许只是心跳掩饰了呼吸。
他掩饰不住好奇,透过门上小小的窗,望向房间里。
房间里的什么,正在进行着什么。
解开的最后一层纱布,丢在一旁的地上,沾满的鲜血,如同在血泊中浸过一样。像是忽然涌出似的,浓烈的刺痛着双眼。背上溢出的汗,贴着身上的衬衫。
双氧水,不知是如何在被使用,然后是止血的药膏。
他只能看见护士长的背影,看不见那将被纱布重新覆盖的脑袋。
护士长将扭干的毛巾在他的脸上擦拭,不久,一只沾鲜血的毛巾,就丢在了装着热水的盆子里。
看着手上的动作,似乎已经差不多包扎完了。他始终没有看见那纱布之下包裹着什么,能够确定的是,一定已经不是正常人应该有的眼睛。护士长忽然将他枕着的枕巾抽了出来,塞进了口袋。他在那么一瞬看见,似乎也是沾着鲜血,像是被鲜血流淌而过,最后扩散。她从口袋里拿出一条新的枕巾,重新放回他的脑袋下面。
她端起盆子,走进了房间里单独的卫生间。
他知道,自己应该离开门口了。
“咦?这不是若介吗?”似乎正是时候,当他坐在值班室里的时候,莫卓走到了门口。
“啊,是莫老师啊。”若介仿佛一直在这里,拿起桌上的膏药,还有医用纱布,向着莫卓走去。
他想去吃点什么了。
到了下午,值班室里有了人,他也可以走出去,买点什么吃的,作为中午没有吃到的午饭的补充。
他走进电梯,按下去往一层的橙光,像每次落下时一样。
“叮!”一楼,门开了。
似乎和想象一样,眼前,穿着灰白病服的人,消瘦的身影。他扬起嘴角,向着那双没有焦点的眼。她走了进来,除了流过嘴角的妩媚和脸颊透出的单纯,似乎没有其他什么东西。
他重新让手指明亮,指向,代表地下室的橙光,就像是点亮一颗有限界的太阳,只照亮指尖一方的金属,泛开温暖却冰冷的光。
黑暗像是侵入电梯的触手,在门打开的一瞬暴走,就像将袖未推在墙上激烈的亲吻的若介一样。身后仅存的光,有一方变作挤压的形状,最后的一线光芒,消失在十指交缠的墙上。他像是沙漠的求水者,浸入那一弯清泉荡漾,不结实的纽扣,耷拉在身旁,像是从嘴角留下的唾液,晕开了交糅的霜。
“轰……轰……”
身后,电梯下降的声音?突如其来,没有防备。
他向身后转头,惊异,有些不知所措。
她,却拉住了他的肩膀。
“叮!”门开了,走出的是一个不知道在几楼值班的护士,能够确定的是并未到三楼的住院部。这个人或许是他见过的,但大概即使他再看见了,也不会有什么印象。她推开存放着医用品的一扇门,走进去。她在里面找寻着什么,过了半晌,似乎是找到了要用的东西,便重新推开门去,再度走回电梯。
他听着隔壁的人离去的声音,舒下了一口气。
似乎,人是走了。
他定下眼睛,适应了黑暗的视线,似乎都已能看见。他感到诧怪,这让他难以想象的场景,竟然会出现在这里!
“这里是……手术室?”他的惊异似乎超过了平时。从他进这个医院,他就走进过好几次这个地下室,却一直都是进的储藏的房间,似乎从来没有注意到储藏室旁还有一扇没有锁上的门。而这扇门里,竟然有一个简单的手术室。
看得出,这里很有段时间没有人使用,而且已经被搬出去了一些东西,但是用作手术的床,还有那巨大的灯,还留在这里。不远的地方,还有那可以拖动的手术工具车,上面没有排放着剪刀手术刀止血钳之类的,却还沾着没有清洗掉而结成痂的血迹。
“这里……”若介走向那手术台。黑暗中泛蓝的皮,冰冷的接线。
“为什么这个手术室会在地下室里?”他转过头去,望向袖未,“而且,你怎么会知道这里?”
袖未靠着墙,没有言语。
他依旧望着她,似乎觉得她一定会回答,即使,她已经沉默半晌。静静的房间里,听得见的,是胸口跳动的频率、跳动的时间流过,视线,却似乎未随着时间流去。
“这里,是我出生的地方。”
阴冷的空气,弥散在耳鼻。他屏住呼吸,或许只要鼻翼淡淡地抽吸,就会被这异常的阴冷呛到鼻子,一直冻结到喉咙,直到凝固的动脉都失去跳动。
“这里,原本不是迎接生命的地方,但我却出生在这里。”
他听不懂她的言语,却似乎能够感觉到,这里似乎有着什么故事,有着什么不知可否告人的秘密。
“这是……什么意思?”他试图追问。
“这里,是阻隔生命诞生的地方,但是我却在这里诞生。”
更加莫名其妙的话语,像是长着倒刺的脚,勾住了他的思绪,却没有让它前进的动力,试图拨动,只觉得疼痛更深地刺入肉体。
她忽然咬住了亲吻她的嘴唇。
“好疼……”他变了呼吸,却没有松口。她却松了口。继续这相互的透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