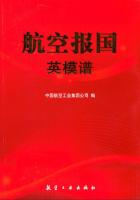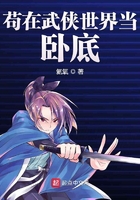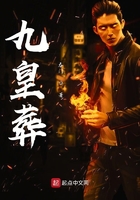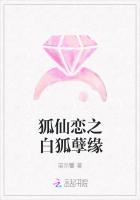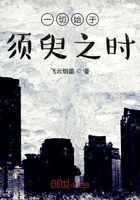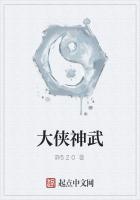玛莎的父亲所罗门·克洛尼奇·克莱恩拉比(RabbiSolomonKl-onitzki-Kline)是一位著名的犹太教法典学者。他出生于立陶宛,担任过科夫罗(Kovno)一所犹太神学院的院长,那里离拉扎勒斯的出生地仅55英里。他的著作《希伯来语同音异义词词典》和《塔木德释义辞典》,为他赢得了“文法王子”的美名。后来,由于立陶宛的犹太族群遭到沙俄迫害,克莱恩迁去了美国。他的一个女儿嫁给了美国人,另一个女儿玛莎则去了加拿大做护士。玛莎的工作签证到期后,克莱恩的美国女婿把他介绍给了一个旨在协助新移民安居乐业的加拿大组织——该组织的主席便是里昂。就这样,克莱恩结识了里昂,而玛莎和内森也因此相识相恋,最终结为连理。
幼年的莱昂纳德很少见到身在美国的外祖父,但听说了不少关于他的轶事。玛莎告诉莱昂纳德,好多人不远万里地跑去听外祖父讲课。玛莎还说,他是一位远近闻名的优秀骑手——莱昂纳德对这一点尤其感到高兴。实际上,相较之头脑,莱昂纳德更在乎体魄。他想上军校,想驰骋沙场、建立功勋,就像父亲当年那样——虽然父亲现在体弱多病,有时连上楼都困难,所以不得不尽量待在家里,由母亲照顾着。莱昂纳德印象中的父亲都是羸弱的,但是他知道,父亲曾是一位战士,他在一战中用过的手枪就放在床头柜里。有一次,趁大人不在,莱昂纳德偷偷取出了这支枪。点三八口径,沉甸甸的,枪管上镌刻着父亲的名字、军衔和军团名称。莱昂纳德小心翼翼地将它捧在手心。金属的重量感和冰冷的触感,让小莱昂纳德心中充满了敬畏,几乎为之战栗。
贝尔蒙特大道599号的生活忙碌、规律、井然有序。这里是莱昂纳德童年世界的中心,他所需要做的一切,想要做的一切,都紧紧环绕着它运行:叔叔们和表兄弟们的家就在附近;犹太教堂也在附近——他周六上午得跟全家人一块去那儿做礼拜,周日得独自去那儿上“主日学校”;他每周去两个下午的希伯来语学校,往山下走几步就到;他接受常规教育的罗斯林小学,以及之后的韦斯特蒙中学,也都不远;茉莉山公园更不用说,和莱昂纳德的卧室就隔着一扇窗,他在那里度过了一个个光着膀子尽情玩耍的夏天和哆嗦着堆雪人的冬天。
韦斯特蒙犹太社区的邻里关系和睦而紧密。在英裔新教徒为主体的大社区里,犹太人是少数族群;但在以法裔天主教徒为主体的蒙特利尔和魁北克,英裔新教徒却是少数族群;可若放眼整个加拿大,法裔天主教徒又成了少数族群……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活在边缘,每个人又都为自己的族群感到骄傲。“这里具有一种‘浪漫的、诡秘的氛围’,是一个‘血脉、土壤和命运之地’,”莱昂纳德说,“这就是我成长的地方,对我来说,一切都很自然。”
皇家山十字架1的光辉;家里的女佣玛丽时不时地用手在胸前画十字;学校里每年一度的复活节和圣诞节的庆祝活动……它们提醒着莱昂纳德,这是一座天主教徒的城市。当然,莱昂纳德也有些独特的记忆,比如每周五日落时父亲亲手点燃安息日蜡烛;比如山下气势雄伟的犹太教堂,教堂墙上挂着的曾祖父、祖父的肖像,他们的眼睛静静地凝视着小莱昂纳德,仿佛时刻提醒着他,你的身上流淌着犹太人的血液。
在莱昂纳德看来,他们的家庭生活堪称“紧张激烈”。科恩一家经常集体出动:去犹太教堂,去工厂,去莱昂纳德祖母家……“每个周六下午我们都会去祖母家。下午4点左右,祖母家的女佣会准时推出小餐车,上面摆满了茶、三明治、蛋糕和饼干。”莱昂纳德祖母家位于市中心的舍布鲁克街,那里是蒙特利尔所有盛大巡游的终点。莱昂纳德的堂兄大卫·科恩说:“祖母虽是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女士,但也相当赶时髦。”莱昂纳德对祖母的印象极为深刻,在小说处女作《钟爱的游戏》(The Favorite Game)中,他详细地描写了在她家进行的茶话会。在《钟爱的游戏》里,莱昂纳德的长辈和兄长大都既“严肃”又“正式”。但大卫的哥哥拉兹是个例外。莱昂纳德认为拉兹“对各大夜店了如指掌,跟歌舞团的妞儿和演艺圈人士很熟”。另一个特例是内森的表亲埃德加·H.科恩。埃德加也是个商人,但爱好文学,出过一本叫《风流小姐:妮侬·德·朗科洛斯传》(MademoiselleLibertine:A PortraitofNinonde l"Enclos)的书。妮侬是17世纪法国著名的交际花兼作家,伏尔泰、莫里哀等大文豪曾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莱昂纳德与埃德加走得很近。
莱昂纳德的童年生活舒适安宁,与当时大环境的动荡不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他5岁生日前夕,德国入侵波兰,二战正式爆发;1942年,在蒙特利尔的圣劳伦斯大道,爆发了法裔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反犹太示威活动。这些人排犹的理由十分可笑,比如他们声称,犹太人已经控制了加拿大整个服装产业,目的就是为了逼迫端庄的法裔女孩穿上“不正经的纽约风格晚装”。示威活动期间,几家犹太人的商铺、餐馆遭到了打砸,墙壁被种族主义者涂上了极端标语。但对于一个韦斯特蒙的7岁孩子而言,这些就像是发生在另一个世界的事。他依然安坐在卧室中,翻看着超人漫画书。“战争,社运……它们似乎都没有触到我们。”莱昂纳德说。
大人的要求小莱昂纳德都能轻松做到:保持小手干净,讲礼貌,成绩好,入选冰球队,穿着体面的服装出席晚宴,睡前将擦得晶亮的鞋子整齐地放在床边……童年时的莱昂纳德并未展露出圣徒般的悲悯和天才式的忧郁。从业余摄像爱好者内森拍摄的家庭录像中,我们看到一个快乐的小男孩,有时蹬着小童车,有时与姐姐手拉手走在路上,有时跟他的狗一起玩耍——他的脸上始终绽放着灿烂的笑容。那只狗叫Tinkie,是黑色的苏格兰梗犬。玛莎原本给它取名为Tovarich,是俄语“同志”的意思。不过这个名字被内森否决了。他觉得,玛莎身上的俄罗斯味、不标准的英语和鲜明的性格,已经够引人注意了。“过于引人注目并非好事。”莱昂纳德说。
1944年1月,内森去世,享年52岁。这一年莱昂纳德9岁。大约14年后,莱昂纳德在他两篇未发表过的作品《仪式》(Ceremonies)和《我姐姐的生日》(MySister"s Birthday)中描述了当时的情形:玛丽坐在餐桌旁,双手交叠着放在膝头。她告诉莱昂纳德和埃丝特,明天不用去上学了,因为他们的父亲已于当晚过世。“保持安静,”她说,“夫人在睡觉,明天还要举行葬礼。”“可是明天不行啊,姆妈,明天是姐姐的生日啊……”
翌日上午9时,六个人抬着棺材走进起居室,把它放在皮质长沙发旁。玛莎和女佣一起,将房间里所有的镜子擦拭得干干净净。中午时分,参加葬礼的人们陆续到来。家人、朋友、工厂的员工……每个人进门前都忙着抖落靴子和外套上的雪。棺材是打开着的,莱昂纳德偷偷朝里瞥了几眼。他看见内森身上裹着银色的祈祷披巾,脸色苍白,胡子墨黑。莱昂纳德觉得父亲看上去有些烦闷。贺拉斯叔叔来了,他同内森一起上过战场,后来俩人共同管理着弗里德曼公司。贺拉斯轻声对莱昂纳德说:“我们一定要像士兵一样勇敢。”那天夜里,埃丝特问莱昂纳德:“你敢没敢看爸爸的脸?”两人一聊,才知道他俩都看了,并且都觉得父亲的胡子一定被染过。
这两篇文字有着同样的结尾:“我对她说,别哭,今天是你的生日啊。”
在《钟爱的游戏》中,莱昂纳德第三次描述了当时的情形。这次的叙述更加镇定自若,一方面是其文笔已渐趋成熟,另一方面,后者的体裁是小说(不过经莱昂纳德证实,确有其事)。
……小男孩从父亲卧室里拿走一个领结,剪开,将一张纸藏了进去。翌日,小男孩自己为父亲举行了一次秘密的纪念仪式。他来到花园,刨开积雪,在地上挖了个洞,将领结埋了进去。
莱昂纳德后来说,那张纸上有他的处女创作,不过他已记不得当时究竟写了些什么。在他看来,这个仪式极具象征意义,它象征着自己写作之路的开启。他说自己之后“在原地挖了多次,想要找回那张纸,但每每无功而返”。
作为显赫的宗教世家科恩家族的一员,摩西的兄长亚伦(犹太教第一位大祭司)的后代,莱昂纳德曾豪言壮语:“我是科恩家族的一员,这意味着我重任在肩,我将让《摩西五经》更上一个台阶……”但更多的时候,莱昂纳德对自己祖辈修建的教堂实在兴趣索然。他说希伯来语学校“令他感觉非常无聊”,他还说:“除了听唱诗班唱颂歌时有过触动外,我对宗教并没多大感觉。”据1948年被任命为“天堂之门”犹太教堂拉比的苏查特回忆,事实的确如此,莱昂纳德作为一个学生而言最多算得上“还好”,“他对做学问兴趣不大,他为创作而生。”
莱昂纳德并未因幼年丧父而哭泣,几年后Tinkie去世时,他反倒流了不少泪。“父亲辞世并未给我带来深深的失落,”莱昂纳德1991年接受采访时说,“也许是因为他一直重病缠身。他的死似乎很自然。他是那么虚弱,然后他死了。也许是我心肠太硬了吧。”
诚如他所说,父亲的死对他影响并不大。这不是因为他年幼不更事——他9岁了,已经很懂事。但在他内心深处,还是泛起了波澜。他第一次意识到人生无常,原本单纯完整的内心,也第一次出现裂痕,不安或孤独,随即无声地钻入;而他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父亲静静地躺在棺木中时,贺拉斯叔叔将他拉到一边,告诉他:“莱昂纳德,你成了这个家庭的男主人。你要承担起照顾家中的女人——你的妈妈,你14岁的姐姐埃丝特的责任。”“我倍感骄傲,”莱昂纳德在《仪式》一文中如此写道,“我是长房长孙。我像个继了位的小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