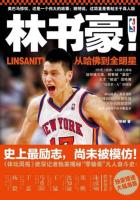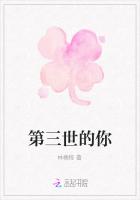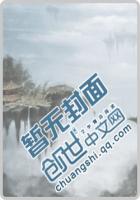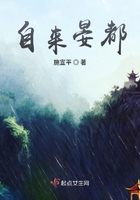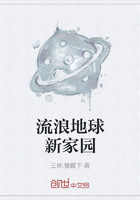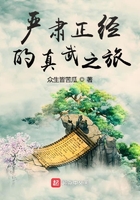希望在你面前我是七岁时就想成为的那个完美男人一个杀手——《我的写作之因》(TheReasonI Write)节选,《诗选:1956—1968》(SelectedPoems:1956—1968)
司机驶离主干道和占去大半个街区的犹太教堂,沿着对面街角的圣马蒂亚斯教堂驶上了山坡。车后座坐着一位27岁的迷人女子,五官分明,衣着入时,怀里抱着一个初生的婴孩。这一带的街道整洁漂亮、设施完备,两侧绿树成荫。也许你会以为,路边那些高大的砖石结构宅邸会被自己不可一世的自负压垮,但它们依然屹立于斜坡之上。司机继续朝坡上驶去,之后拐进一条辅路,在路的尽头——贝尔蒙特大道599号停了下来。这栋英式豪宅的深色墙砖给人以凝重之感,但在屋前的白色门廊、屋后茉莉山公园14英亩的碧绿草坪与鲜艳花圃的映衬下,显得柔和了许多。从这里往外远眺,圣劳伦斯河和蒙特利尔闹市区一览无遗。司机走下车,打开后座车门。小莱昂纳德被妈妈抱着走过白色的门前阶,进入了属于自己的房间。
1934年9月21日早上6点45分,莱昂纳德·诺曼·科恩(LeonardNo-rman Cohen)出生于皇家维多利亚医院。这家加拿大首屈一指的医院就坐落在科恩家族居住的蒙特利尔富人区韦斯特蒙(Westmount)。那是“大萧条”和二战中间的一个周五,掐指算来,他母亲怀上他应该是在蒙特利尔漫长而寒冷的冬天,犹太光明节到圣诞节之间。
莱昂纳德·科恩是在西装堆里长大的。莱昂纳德的父亲内森·科恩(Nathan Cohen)是位富有的加拿大犹太商人,从事高档服装生意,他名下的弗里德曼服装公司以生产正装闻名,而他自己也永远都是一身正装,就连在非正式场合也是如此。内森对西服的品位,正如他对住宅的品位一样,偏爱英式风格。莱昂纳德的母亲玛莎·科恩(Masha Cohen)比她丈夫小16岁,是俄罗斯犹太人,一位拉比的女儿。她是加拿大新移民,1927年才来到蒙特利尔。来这边不久,她就嫁给了内森,两年之后,两人有了第一个孩子——莱昂纳德的姐姐埃丝特(Esther)。翻看内森和玛莎年轻时的照片,你会看到他俩无论是外形还是神情都迥然相异:内森方脸盘、宽肩膀,身材矮壮;玛莎则苗条圆润,比丈夫要高出一个头。她看上去神情高贵,热忱善感,略微有些孩子气;内森则双唇紧抿,面容严肃,显得矜持得多,“英国”得多。婴儿时期的莱昂纳德胖墩墩的,脸蛋有点方,跟他父亲一样。不过之后,他的外形越来越随有着瓜子脸、浓密卷发和乌黑深邃眼眸的母亲。从父亲那里,他继承了对整洁、体面和西服的偏好,不幸的是,还有身高;从母亲处,他秉承了个人魅力、骨子里的忧郁和音乐天赋。玛莎的嘴里总是哼唱个不停,大多是她童年时学会的俄语和意第绪语民谣。在想象出的小提琴伴奏下,她用醇美的女低音一首接一首地唱着,从欢快的歌唱到伤感的歌,周而复始。莱昂纳德形容他的母亲是“契诃夫式的”。“她的欢笑和哭泣,都是那么地强烈,”莱昂纳德说,“她的情绪也是说变就变。”韦斯特蒙的居民都是富裕的中上层阶级,他们不是英裔新教徒,就是第二代、第三代加拿大犹太人。在这个族群隔离极为严重的城市,新教徒和犹太人之所以聚居到一起,仅仅因为他们既非法裔,也不是天主教徒。在“寂静革命”1(QuietRevolution)发生之前,在法语还未成为魁北克惟一的官方语言之前,佣人是韦斯特蒙惟一的法裔群体。科恩家有一个名叫玛丽的保姆,不过是爱尔兰裔天主教徒。除了玛丽外,他们家还有一个女佣和一个名叫克里的黑人园丁兼司机。毋庸讳言,莱昂纳德有着优越的家庭背景。他从未否认过自己的出身,摒弃过自己的家教,排斥过自己的家庭,也从未做过改名换姓、假借身份的事情。他家很富裕,但并不是韦斯特蒙最富的;他家的宅子很大,但并非独栋而是联排;他家也有司机,但开的并非卡迪拉克而是庞蒂亚(Pontiac)。但就社会地位而言,即便是韦斯特蒙最富裕的家族都无法与科恩家族比肩。实际上,科恩家族是蒙特利尔所有犹太望族中,声名最显赫、地位最重要的家族之一。多年以来,科恩家族的成员在加拿大兴建犹太教堂、创办报纸,资助并管理过多个犹太慈善社团。莱昂纳德的曾祖父,拉扎勒斯·科恩(Lazarus Cohen),是这个家族第一位迁入加拿大的成员。拉扎勒斯生于1840年代的俄属波兰,早年在维尔科夫斯基(Wylkowyski)一所以严苛著称的著名犹太神学院任教,30岁不到,他就决定暂别妻儿,出国闯世界。他先在苏格兰待了一小段时间,随后漂洋过海,来到了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小镇马伯里(Maberly)。在这里,拉扎勒斯从零售木材干起,经过一步步的奋斗,成为了一家煤炭公司的老板,公司名称就叫“科恩父子”——“儿子”指的是里昂·科恩(Lyon Cohen),也就是内森的父亲,他和母亲是拉扎勒斯到加拿大两年后搬来的。后来,拉扎勒斯带着妻儿来到了蒙特利尔。在这个彼时加拿大的第一大城市,他将自己的黄铜铸造公司和疏浚公司经营得风生水起,就这样,科恩家族在蒙特利尔扎下了根。
拉扎勒斯初到加拿大时是19世纪60年代末,当时这个国家的犹太人还很少——19世纪中叶时,蒙特利尔的犹太人全部加起来也还不足500人。而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期,也就是拉扎勒斯就任“天堂之门”(Congregation Shaar Hashomayim)犹太教堂主席1时,蒙特利尔的犹太人已经激增至5000多人了。这股移民潮缘于沙俄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到19世纪末时,加拿大犹太人的数量又翻了一番。蒙特利尔成了加拿大犹太人的聚居地,而留着长长的花白胡子的拉扎勒斯,也成了当地犹太社区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他主持修建犹太教堂,同时创办了诸多社团以帮助犹太移民在加拿大安家落户;1884年,作为蒙特利尔犹太垦殖协会的代表,他还去巴勒斯坦买了一大块地。之后不久,拉扎勒斯的弟弟,茨维·赫希·科恩拉比也来到了加拿大,他后来成为蒙特利尔的首席拉比。
1914年,里昂·科恩继任“天堂之门”犹太教堂主席一职时,“天堂之门”已是拥有4万犹太居民的蒙特利尔城里最大的犹太教堂了。1922年,由于原建筑面积已无法满足教徒的需求,里昂在韦斯特蒙新建了一座“天堂之门”,它十分壮观,几乎占去了大半个街区。从贝尔蒙特大道那栋宅邸出来,一路下山,只需几分钟车程即可到达。12年后,内森和玛莎在这间犹太教堂里登记了他们惟一的儿子莱昂纳德的出生信息,并给他取了个犹太名字:以利以谢(Eliezer),意为“我有神助”。与父亲一样,里昂也是位非常成功的商人,不过他从事的是服装和保险业。除去做生意,他还参与了许多公共事务:早在十几岁时,他就被任命为“英裔—犹太人协会”秘书;他创建了一个犹太社区中心和一家疗养院,并在救济大屠杀难民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曾当选为加拿大犹太议会(CanadianJewishCongress)、加拿大犹太垦殖协会等全国性组织的主席;他曾拜访梵蒂冈教廷,与教皇对话;他与另一位犹太人领袖联合创办了加拿大第一份针对犹太读者群的英文报纸《加拿大犹太时报》(TheCanadianJewishTimes),有时还在上面发表文章;他在16岁时还写过一出名叫《以斯帖》的戏剧,并自导自演。里昂去世时,莱昂纳德才两岁,所以他对祖父没有什么印象。不过,他俩之间似乎存在一种强烈的情感纽带,随着莱昂纳德的成长,这种纽带也愈发清晰。里昂的人生准则、职业道德,以及他对“知识分子的贵族性”的认同,都让莱昂纳德深以为然。
里昂也是一名坚定的爱国者,一战爆发时,他发起了征兵宣传活动,呼吁蒙特利尔犹太人参军报国。率先登记入伍的正是他的长子内森与次子贺拉斯(三子劳伦斯年龄尚小)。内森在军中官至中尉,是加拿大陆军第一位犹太军官。莱昂纳德爱极了父亲的戎装照。不过,从战场归来以后,内森的身体状况就一直不好,也因为此,作为长子的内森没能顺理成章地继承犹太教堂的管理工作,更不用说参与其他公共事务了。就连家族企业弗里德曼服装公司,名义上内森是董事长,实际上则由贺拉斯掌控。内森与他的长辈不太一样,他既非知识分子,亦非宗教学者。他的书架上摆着乔叟、华兹华斯和拜伦等大诗人的作品,不过它们长久以来都形同摆设,直到被莱昂纳德翻得皱皱巴巴。“父亲更喜欢《读者文摘》这类的书,”莱昂纳德说,“他很有教养,是位绅士;他是个保守的犹太教徒,不狂热、不固守意识形态或教条。”在内森家,宗教话题很少被提及,也没有人想提及。“鱼儿不会提到水,我们也很少提到宗教。”但对于他们来说,宗教、传统、族群就像水之于鱼一样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