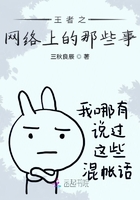整个早上,空色在临时用屏风围成的空间里接受着一系列的检查。黑一娇看不到,但看着医护人员推着一台台的检查仪器进进出出还真有点惊奇,到底要接受几项检查才能完?难怪那天他从早上检到傍晚都还没检完。
那天他检查中途突然逃掉也成为她至今不知道的疑团(或许是因为她不敢知道),但仔细想想还是知道一些,这种冰冷死寂得令人窒息的空气,他从小孩子到成年的二十多年里,每个季节都得面对一次,还不算每月每星期的中检查小检查的,难怪他会想逃。
中午,陈渔还在里面指导着检查,但也没忘记吩咐给她准备午饭。
屏风那边传来了各种仪器那有点死亡气息的声音,还有医护人员的低语,黑一娇仍能大口大口地扒饭,足见她这样的适应能力是遗传自小强的。
然而,很快,她就感觉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那边的仪器声依旧,可她总感觉有点不妥。她也吃不下了,放下筷子,竖起耳朵听着那边对面的动静。
开始时,陈渔说得很轻,像哄小孩子一样,
“色,再忍忍,快行了。”
“想吐就吐,别忍着。”
可渐渐地,陈渔语气突然变得有点着急了。
“该死!都叫你别忍着,被听到又怎样,死要面子!”
“把你的手放开,又握出血你就死定了!”
“你想咬舌自尽是不是!马上给我呕!”
随着陈渔那越来越冲的话,黑一娇的心变得焦躁不安起来。
病房里突兀地响起玻璃摔到地上碎裂的声音,她神经质一般冲过去,把屏风拉开
只见空色侧身蜷缩在病床上,头发凌乱,脸色死白,却没半滴汗水,如果不是他耳根以下的一条条青筋暴突,如果不是他的全身微微颤抖,她会以为那是一具尸体。病床上的床单皱皱巴巴的,难以想象他在这里是怎样地挣扎。一条手臂垂在床侧,死白的指尖下面的地上是碎裂了的玻璃。她看到这里又回头看向他的脸。
空色看到她,瞳孔迅速收缩,闪过一丝气急败坏。但紧接着他就半撑起身体把头伸到床边,一阵肆无忌惮的干呕,扯动起他全身的神经,像会要了他的命。
陈渔把刚抽出来的软管递给身边的医护人员,轻轻地抚着空色的背。
黑一娇一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上去冲着陈渔破口大骂,“陈渔你丫死变态,现在连山旮旯里的医院用的都是无痛胃镜,你居然还给他插管!他是感觉不到痛可也是会难受呀!你怎么当医生的,要犯虐待瘾了找你他妈老婆解瘾去!”她说着说着抡起拳头就往陈渔身上狠狠地砸。
陈渔慌忙躲开,不甘示弱,“你这女人发什么疯!我是医生,只有我最清楚他最适合做的只有这个,要发疯到边去,别妨碍我工作!”
“反正我不让你这么虐待他!”黑一娇扶起渐渐不再干呕的空色让他靠在高高的枕头上。
终于能正常一点呼吸的空色说的第一句话却是:“把ta关厕所里。”
黑一娇以为那个ta是陈渔,笑了,“花瓶你变幽默了呀,其实也不用那么狠,毕竟他是医——”
两名医护人员扣住了她两边手臂。
“花瓶你——”
空色只冷冷地别开眼。
“死花瓶,我还好心好意替你说话!你个死没良心!”黑一娇双腿腾空的不断地瞪着被人提进了厕所。
门刚锁上,黑一娇还在里面骂骂咧咧的瞬间,空色弹起来趴到床边吐出了一大口血,然后又是一阵恐怖窒息的干呕。
很长一段时间,他慢慢把呼吸平息下来,无力地靠回床上。
陈渔拿白手帕重重地擦着空色嘴边的血迹,“如果接下来的检查比这还糟,你就别指望出去了!”
空色也没力气说话,疲惫地闭上了双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