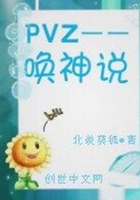汤小姐叫完也就再没出声,酒品是相当的好,即使在这样悲愤的情形下。
窗外渐渐飘起了小雪,细细密密,洋洋洒洒。我躺在床上,看着窗外的雪,虽然细小,却仍然能铺天盖地,就像心里只是有点凉,也终能变得疼痛不堪。
“文竹,文竹。”我连叫两声,外头有人匆匆忙忙跑来应了,又跑下楼去叫,原来她不在房间边上,大概先前的争执也没有听到。跑上来的时候手上端着一碗鸡汤,腾腾地冒着热气,表面浮着一层金黄的油。“二小姐,刚炖好的,你快喝。”
我接过碗勺,“你帮我收拾东西。”
“恩?”文竹愣在那里。
“收拾东西干什么?”程昊霖站在房间门口,带着外面雪的寒气。“文竹,你先出去。”
她吐吐舌头,将门带上。
“收拾东西干什么?”他铁青的脸还和方才一样,走到我跟前,我原本已经将碗放在柜子上,起身去拿箱子,被他拉过坐在床上,“静养,医生让你静养。”
“我就是想回去,我,觉得家里比较好。”
“哼”他干笑一声,我自己也觉得心虚,那不过是租了半年都不到的房子。
“你就把这儿当家。”
“我不想住在这儿了。”直截了当地跟他说,旁的借口都可以被驳回,唯独一个“不想”是他没有理由搪塞过去的。
“你不要听她的。”他很生气,捏着双拳,“听到没有?”
我望着眼前这张脸,乌黑的双眸能将人吞噬。我蓦地想起外白渡桥上的那一夜,三辆军中的轿车从眼前缓缓驶过,其中一辆那漆黑一片看不清里面的车。猛然惊觉,那竟是我们头一次相见,都是因为王依,才搅和到了一起。
“我后悔了,虽然没有用,但是我得说出来,我真的后悔了。”我管不住自己的嘴唇,每一次呼气吸气都要啜泣出来,偏过头看着床头的台灯,“如果可以选,我希望没有这个孩子。”
“我觉得孩子是很可爱的,我马上到而立之年,遇到你、遇到这个孩子,对我来说是恩赐”他捏着我的胳膊的手指一紧,有点疼,“你不是王依。”声音软了下来,不像方才那样怒气冲天,抬手想要碰我的脸颊,被闪躲开来。
虽然泪水仍然往下淌,我突然缓过气来,心里仍然很疼,是另一种悲哀,是不是王依又如何,他许是像集邮一般集着和我们这些年轻女子之间的过往。
“你不想住这儿,也行,这才觉得原来家里也繁杂得让人没法静养。明天我送你去安静的地方。”他的手沿着胳膊,握到我的手,捏在掌心里,“我知道,你是冷伊,你是独一无二的。”
外面有个佣人用力地敲门“少爷,外面来了两个人,请你走一趟。”话语间都是惊恐,仿佛来者不善。
他一脸凝重,竟然是意料之中的事,只拍拍我的手背,“你好好歇着,有时间我们再……”回头喊文竹“伺候你家二小姐吃完晚饭,早点躺下,你帮着收拾点要穿的要用的。”说着已经站起身。
我一把抱住他的手,自己都难以置信,先前还想着要离开他的,我抬头看着他,“你,出了什么事?”
他叹口气,坐在床边,抚了抚我的脊背,“例行的谈话,今天军政部有半数的人都谈了,没事的。”
我觉得很慌张,有种听到郑州围困消息时的惶惶,摇着头,“什么时候能谈完?”
“可能要到后半夜,你别等我,明早我一定在的。”他扳过我的下巴,在额上轻轻吻了下,“你早点休息。”这回头也不回地走出门,门口那个战战兢兢的女佣手上拿着他那件黄绿色的呢大衣,他顺势套上,一脸冷峻消失在门边。
北面传来阵阵叫骂声,五十来岁妇女的声音不绝于耳,不刻意听也听得到“没用”“半点无用”类似的语句,应该是大太太在训斥汤小姐,这是她娘家的晚辈,平日里亲切地唤她姑妈,现在翻脸却能这样地咒骂,可以想象,当时守在一边的程虹雨为何如此忍气吞声。
“大太太睡醒了,又在发脾气了。”文竹把饭菜端好,“听说她从前只是威严了些,这回病倒之后性情都变得很古怪了。”她到哪儿都很机灵的,不消一会儿就和其他人打成一片,我先还觉得惊讶,因为再怎么说我都是个不速之客,其他的佣人应该对我们唯恐避之不及才对,现在想来,大概汤小姐从一开始也没打算使什么坏心眼。
“汤少爷在郑州炸的,啧啧。”她咬牙吸了鼻子两下,“那叫一个惨烈,听说——”她凑在我耳边,“全尸都没有,还是程将军帮他把剩下的尸骸收殓起来的,大太太一听说就昏厥过去了,直念着,最终自己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
果然她是一心想要汤尔跃取代程昊霖的,虽然是典型的偷鸡不成蚀把米,但看着这个情形,这样的风凉话却万万说不出口。
“从前她都是对大少爷小姐一味苛责,生病的时候反倒是一直怨恨程家老爷。老爷去了几年了,以前她从来没半点怨言。跟着她久了的人说,哪怕是年轻的时候老爷纳妾,她连滴眼泪都没落过,从来不和他争执,现在突然如梦初醒似的,忽然恨毒了他,也不再说大少爷小姐的不是,只说这是自己的劫难,宅子里的老人都觉得摸不着头脑呢。”文竹神神秘秘地说。
从前只听过程昊霖的描述,觉得他的亲生母亲过完了自己凄凉的一生,以为大太太也是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现在看看在偏楼里睡思昏沉、不辨日夜、喜怒无常的大太太,才觉得她这个正房夫人又何尝不是辛酸地过着自己的生活。也许这都不是她们能够左右的,也许这是大宅子所具有的的威力,必定要一点一点吞噬其中女人的青春、快乐和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