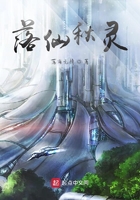第二天,我的船跟随塞科勒斯的船队回航马赛。
站在甲板上,我双手环胸心不在焉地看着船上的水手们忙忙碌碌地跑来跑去,咸湿的海风吹过面颊,我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放松自己的身体享受大海带给我的乐趣。
菲菲迪娅说得没错,即使我现在的处境看似处在劣势,但我并没有错失主动权。无论那个让塞科勒斯“奉命遣送”我回马赛的人到底想做什么,我手中的“卡曼德拉航海图”的残片都让我牢牢地抓住了主动权。
一想到这张已经跟随了自己这么多年的航海图残片,我就有些忧伤。不管怎么样,从我接受这张航海图的那一天起,我就已经走上了一条无法回头的路——无论是现实还是虚幻。
我用七年的时间磨炼自己的意志、武装起自己的心,为的就是能让自己将来可以承受更大的冲击。我用七年的时候让自己学会等待,时间已经够久的了,如今应该是到了去寻找答案的时候了。
我走回到船长室,到桌子旁边从自己随身带着的小包里拿出了那张残破的“卡曼德拉航海图”,在桌子上慢慢地把这张破旧不堪的航海图纸展开、平摊在桌子上。
指尖轻轻地划过这张老旧残破的羊皮纸卷,我实在想不明白它究竟有什么地方那么吸引人——每一次我当着别人的面拿出这张图纸残片的时候,无论是谁看到脸上都会浮现出一种莫名的表情,那种复杂的表情里面有惊恐、羡慕、敬畏和怀疑,甚至还会带有一丝贪婪,关于这张残破不堪的航海图上到底记载了什么样的秘密,为什么会让这么多人对它又爱又怕,我也曾试着找一些人去询问过,可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告诉我真相。
这张残破的航海图不光是我寻找这个世界答案的线索与钥匙,也是我与现实世界最有力的联系,虽然我到现在还没有猜出它里面含有什么样的秘密,但我有一种预感觉得离解开这个秘密的时间不太远了。
就在我魂游天外的时候,我那可爱的胖猫儿“牛奶”也轻轻巧巧地跳上了桌子,它先是小心翼翼地嗅一嗅这张破烂的航海图,然后又用肉肉的小爪子轻轻地碰一碰图纸,在确定面前的东西对它没有什么威胁之后,牛奶便很放心地走到航海图上,接着就一屁股坐在了航海图上面。
我被牛奶的动作逗得笑了一下,伸手点一点它那淡粉色的小鼻子说:“小淘气,知不知道你的屁股下面坐着什么?这或许是一张很值钱的藏宝图,而你这个小家伙儿正坐在一堆宝藏上面呢!”
牛奶被我点得眨了一下眼睛,有些不明所以地看着我,然后用一种撒娇的语调软软地“喵——”了一声,尾巴摆了摆。
我索性坐在椅子上向后仰靠,双手环胸抱住,然后把双脚举高,很不淑女地架在了桌子上。
我刚坐好没一会儿,船长室的门就被人大力推开,冒冒失失闯进来的迪那瑞被我这样的一个姿势吓了一跳,继而站在船长室的门口打量了我一下突然不屑地哼笑了一声。
迪那瑞带着一脸嘲讽的笑容走近桌子,故意用一种痞痞的、有些不太正经的语气对我说:“苏曼戴莉船长,刚刚塞科勒斯元帅派人传话过来,让我们的船要紧跟船队,因为这一带的海域不太平静。”
我并没有看他一眼,只是用脚尖儿逗弄着牛奶,用很淡漠的声音说:“这个我知道,用不着他这个元帅大人操心。不过倒是你,迪那瑞,你在海事学院里难道就没有学过在进别人的屋子里之前要先敲门的基本礼仪吗?”
迪那瑞在听到我不算客气的问话之后,依旧是一副皮笑肉不笑的德行:“我在海事学院里当然学过礼仪课,苏曼戴莉船长!但是,我觉得在您的船上似乎不必过于死板地遵守某些烦人的礼仪细节,况且我也觉得像您这样一位优秀的船长应该是不会跟我计较这些事情的。”
“哦,你还真是了解我。”我把双头交叉垫在脑后看都不看他一眼,漫不经心地说:“迪那瑞,我不敢肯定你究竟在海事学院里学没学过礼仪课程,但是我敢肯定的是,你在海事学院里可没少学会拍马屁的本事!”
迪那瑞就是我在牙买加海事学院里遇到的那个衣服上绣有奇怪图腾的男孩子。菲菲迪娅曾经在私下里向我透露过,这个迪那瑞是牙买加埃得克斯男爵的独生子,别看他现在只有十九岁,但是据说他从十二岁起就已经开始随船出海航行了,行船经验不比那些老水手少。
但我一直都对迪那瑞没有什么好感,不光因为他是个贵族子弟,更让我有些反感和戒备的是,他在平日里的言行明显是在刻意地模仿着我原来的大副亚历山大!让人不免奇怪难道他们之间彼此很熟悉吗?另外,从他在牙买加海事学院里与我擦肩而过的那一番对视之后,我已经在心里将他划分到了敌人的行列里。
发现他在刻意模仿亚历山大之后,我突然想起了原来大副在身边时就总觉得他的言行和习惯都在模仿着谁,如今突然想了起来:如果说迪那瑞是带着一种恶意地在模仿亚历山大,好像是在时刻提醒我别忘记曾经有一位完美的大副跟在我身边一样,那么亚历山大的一言一行则并非是刻意的模仿,应该是被人有意训练出来的,训练的模版就是我曾经最为熟悉的一个人——马赛海事学院首席教官艾伦·戴维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