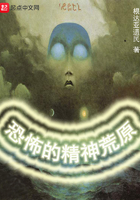惊惧此刻大半都转为了哭笑不得,我跟着他下了桥,他才松开我的手。
下十八盘的时候,两个滑竿手看到他,都笑着打趣他:“老三,你终于救了一个人。”他憨憨地笑,说不出话来,原来他是这样一个老实的人。但那两个人的眼光分明是看异类的眼光,为什么?
他陪我下山,给我讲些山边的景色,但很明显,前言不搭后语。看我神态轻松,他也没有再死跟着我。我奇怪,与他渐行渐远,终于在龙门那里追上了那两个滑竿手。
我拦住他们的脚步,在他们诧异的眼神中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其中一个看我的眼神渐渐平和下来,而另一个则叹口气,说:“他精神上有点儿小毛病。去年我们搭伙抬滑竿,就在观日峰的那个铁索桥上,有个女孩寻了短见。那个女孩是我们抬上去的,一路上沉默寡言的,风景也不看,只顾抹泪。”
到此时,我已明白了大半。他继续说:“当时,他的老婆正临产,他急着要回去。他告诉我那个女孩儿不太对头,但泰山上每天人来人往那么多人,谁会记得谁?我笑他。但是没想到后来出那样的事。从此以后,他就有点儿不正常了,看到一个人上山又不看风景的女孩,就问人家坐不坐滑竿,他会想方设法逗到别人开心为止……”
我微笑着听他讲这个故事,但笑着笑着,却发现自己蓄了满眼的泪水。
原以为我遇上的是一个穷凶极恶的歹徒,没想到却是一个这样的人。心里面的感动啊,一波一波的,让我想起他温暖的脸,想起他身上的汗味,都觉得亲切。
下山的时候,我再次遇上了他,坐在那里,对着我微笑。他还认得我,对我说:“姑娘,其实我们是一样的人啊。父母生养我们不容易啊。”
我的眼泪再一次落下来,他给我带来了好心情,我握住他的手,他却有点儿紧张,傻乎乎地说:“再见就行了,不用握手。”
我决定回去,将这个故事讲给我的男友听,不管他是怎么看这个人,我都觉得,他可能会温暖我的后半生。她绝对相信孩子走进来的时候一定会放声大哭,他的手里是空空的——她注意到了。
一个也没有
周亮/文
小查德是个羞涩而又安静的少年。一天,他回到家,告诉妈妈他想为班里的每一个同学做一份情人节的礼物。妈妈的心沉了下去。她想:“我希望他别这么做。”她曾见过孩子们放学漫步回家的情景,她的查德总是走在最后面。孩子们说着、笑着,手臂搭着肩膀,而这些孩子里面从来没有查德。尽管如此,她还是决定遂了孩子的心愿。她买回了做卡片的硬纸、胶水和彩色蜡笔。一连三个星期,每日每夜,查德费尽辛苦做好了三十五张隋人卡。
情人节终于来了,查德别提有多高兴了,他小心翼翼地把卡片叠好,放进一个袋子里,飞快地跑出了家门。他的妈妈决定为他烤他最爱吃的甜饼,准备在他放学回家的时候,把这些美味可口、热气腾腾的甜饼连同一杯牛奶一起端放在餐桌上。她知道,他会很失望的,或许这样可以稍稍地安慰他。想到孩子可能得不到什么情人节礼物——甚至一件也没有——她的心在痛。
下午,她把甜饼、牛奶端到桌上。一听到孩子们的声音,她就向窗外望去。是的,他们回来了,大声笑着,非常开心。而查德依旧走在后面,却比平常要走得快些。她绝对相信孩子走进来的时候一定会放声大哭,他的手里是空空的——她注意到了。门开了,她强忍住要落下来的泪水。
“妈妈给你准备了甜饼和牛奶。”她说,可孩子却好像没有听见,只是继续大步走过她身旁,脸上放着光,嘴里不停地说着:“一个也没有。一个也没有。”
她的心在向下坠。
孩子却又兴奋地说道:“我一个也没有忘记,一个也没有!”
现在我们仍然在一起,而且我们有了两个男孩。我感谢上帝给我送来了约翰尼·特拉别克。
感谢上帝送来新跑鞋和他
金姆·洛耐特·特拉别克/文
我不知道我们要去哪,我也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只是不停地走着。我在回想这些年以来丈夫对我的虐待:我被打过,骨折过,被枪击过,被刺伤过,被强暴过。我最终鼓起了勇气离开他,同时带走了我的两个小女儿歌蒂和凯蒂。
这是我们流浪街头的第三个星期了。我试图找份工作,可是我付不起白天请人照看孩子的工钱。她们分别只有2岁和4岁。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我去过一些当地的救济机构,但他们通通拒绝了我们,因为我走得急,没有带小孩的出生证明。我不可能再回那个家了,绝不可能!
当地的一家肯德基炸鸡店会把放在保暖器里过久的鸡肉扔掉。我与经理谈了谈,问他是否可以把那些准备扔掉的鸡肉给我的小孩吃。他说可以.但是我得等很久他们才会处理那些鸡肉。饥饿不是一件骄傲的事情,一位收银员无意中听到了我们的对话,她告诉我,他们会把那些鸡肉放在垃圾桶的顶部,不倒进去。我们就这样吃了几天饭。
一天,我带孩子去肯德基之前,去了当地的一家比萨店,看看能不能为,我的小孩要一杯水喝。在那里我看到了他——一个健硕而英俊的意大利人。他是我见过的最英俊的人。我知道我们当时的样子看上去一定非常糟糕,但是他还是对我们报以友好的一笑。我问他我们是否可以要一些水。他让我们坐好,他会去取。
他给我们取来了水,然后开始说他知道在这样一个城市里养一个家是多么不容易。他离开了一会儿,去接一个电话,等他回来的时候,他拿来了许多食物——比我这一个月见过的食物还要多!我尴尬极了。我告诉他我没有钱买其中的任何一种食物。“这是店里请的。”他说,“只有像你这样的美丽女士才会获得这样的待遇。”我想他一定是疯了。
我们又坐了一会儿,聊了聊天。接着,他开始问一些让我紧张的问题。“你的脸上为什么会有这些瘀伤?”“你为什么不穿一件外套?”……我尽量冷静地回答了他所有的问题,他若有所思地听着。最后,我把剩下的食物包好,放进婴儿车的袋子。我在盥洗室给女儿清洗了一番,也把自己弄干净了。我的样子很糟糕。出门的时候,我向他表示感谢,他对我说,随时欢迎我们再来。我并不想滥用他对我们的这份欢迎。但是,冬天很快就要来了,我必须做出一个决定:或者找一份工作,或者设法回到乔治亚州我的家人身边。
我们离开了比萨店,开始寻找晚上过夜的地方。我们漫无目的地走着,突然小女儿呕吐起来。我记得那位男子在食物中放了一些纸巾。就在我找纸巾的时候,我摸到了塞在里面的9美元。我想,他大概在包食物时不小心把这些钱也放了进去。我知道自己不能拿这笔钱。于是,我们掉转头又向比萨店走去。
他还在那里。我告诉他我发现了他的钱,过来还给他。“我故意放在那的。”他和气地说道,“很抱歉,我身上只有这么多了。”
他为什么这样做呢?他是天使,这是我的第一个念头。我只好又一次结结巴巴地向他表示感谢。“明天中午再把她们带来吃午饭。”他回答道。他为什么对我们这样好?因为实在别无他法,我同意了他的建议。说过再见,我们又一次离开了。
走到街上没多久,我就感觉自己被跟踪了。我很紧张,因为我要保护两个孩子。我迅速地转到一个小巷子,并让孩子们不要出声。我觉得有人走近了,我屏住了呼吸。
是比萨店的那个人!
“我知道你没有住的地方。”他说。
“你怎么知道的?”我的心怦怦直跳。他要把我的小孩交到州政府吗?
“我从你的鞋子看出来的。”
我低下头看自己的鞋。我的运动鞋已经破烂不堪了,满身洞眼和缝缝补补的线。我的脸立刻涨得通红。“啊,”我结结巴巴地说,“这双鞋穿起来比较舒服。”
“你想在一个暖和的地方待上一晚,洗个澡吗?”
我犹豫着。我完全不认识这个人。虽然我喜爱温暖了我的心的他那双褐色的眼睛,但这还不足以让我做出到一个陌生人家过夜的决定。
“谢谢你。”我轻声说道,“我们不需要。”
他随手指着我们上面的一套公寓,说:“如果改变了主意你只需走上去,敲敲门就可以了。”
我再次谢过他,并看着他离开了。是时候拾掇拾掇准备过夜的地方了,我尽量收拾得舒服些。当我在婴儿车旁坐下的时候,我看到楼上的一扇窗户下有一个影子,是他。他在那坐了好几个小时了,看着我们。最后,我还是不安地睡着了。由于过于疲倦,我甚至没有发觉下雨了,所以起初我也没注意到他就站在我身旁。时间是凌晨3点。
“我求你把孩子们带到楼上去吧,我不想你们生病。”他说。
“我不能。”我回答道。
“那好,那我就只好在这里陪着你了。”他说着便坐到了地上。
我只好屈服。“没必要让所有的人都淋湿。”我咕哝着。我让他抱着婴儿车上楼。他让我和孩子们睡他的床,而他自己则睡在沙发上。
“这样做合适吗?”我小心翼翼地问他。
“你就睡觉吧。”他跟我道晚安。但是我根本就睡不着。我并不是害怕这位温和的绅士,我只是……紧张。
第二天,他出门给孩子们买来了些新衣服和新玩具,给我买了一双新跑鞋。这是6年前的事了。现在我们仍然在一起,而且我们有了两个男孩。我感谢上帝给我送来了约翰尼·特拉别克。我们现在有一个安稳而爱意浓浓的家,不再有任何的伤害。
妇女犹豫了一下,叹了口气,那只高举的拳头无力地垂了下来。妇女从怀里掏出了一块用纸裹着的面包,轻轻地递到伤号的面前。
给仇人一块面包
寒心血/文
二战时期,前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浴血奋战,在付出巨大的代价之后,终于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
战争胜利的当天,上万名疲惫不堪、无精打采的德国战俘排成长长的纵队,在荷枪实弹、威风凛凛的前苏联士兵的押解下走进莫斯科城。
得知法西斯战俘进城的消息后,人们几乎倾城而出,纷纷拥上街头。在宽阔的莫斯科大街两旁,围观群众人山人海,挤得风雨不透。在围观的人群中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儿童。
苏军在战胜入侵的德国法西斯的同时,自己也付出了重大的伤亡。这些老人、妇女和儿童都是战争的受害者,他们当中许多人的亲人,在这场异常残酷的战争中被入侵的德国法西斯杀害了。
失去亲人的痛苦把原本温和、善良的人们激怒了,他们怀着满腔的仇恨,将牙齿咬得格格响,一双双充满血丝与复仇火焰的眼睛齐刷刷地向俘虏走来的方向注视着。
为了防止出现意外,大批的军队和警察出动组成一堵墙,排在愤怒的人群前面。
战俘出现了,近了,更近了。围观的人群开始骚动,有人喊出打倒法西斯的口号,有人叫骂着让杀人的凶手偿命,接着人群潮水般地向前涌。负责维持秩序的警察企图阻止,马上被汹涌的人潮冲得七零八落,最后警察和士兵手拉手组成人墙,好不容易才将人潮挡住。
此时,战俘已经来到人群前面,他们个个衣衫褴褛、步履蹒跚,每向前迈一步都十分艰难。他们有的头上裹着绷带,有的身带重伤,有的失去手脚躺在担架上不断发出痛苦的呻吟。
面对激怒的人群,德国战俘呆滞、木讷的目光中充满了恐惧与惊慌。出于求生的本能,他们不住地后退。许多战俘本来就身负重伤、疲惫不堪,在遭如此惊吓后瘫软在地,无力逃脱,拼命地哭号呼救。”
这时,一位中年妇女在混乱中拼力挤过人墙,冲到一个受伤的战俘跟前,举拳要打。
这是一个失去双腿的重伤号,他头上打着绷带,破烂的军装上沾满了血迹,脸上的稚气表明他绝对不会超过二十岁。面对扑面打来的拳头,他无力躲闪,瞪着惊恐的眼睛,发出绝望的哭泣。
蓦地,中年妇女停住了,木雕泥塑般站在那里。她怔怔地看着年轻的战俘,心头一阵剧烈刺痛,在这个年轻伤号稚气的脸上,她看到自己刚刚战死的儿子的影子!
妇女犹豫了一下,叹了口,那只高举的拳头无力地垂了下来。妇女从怀里掏出了一块用纸裹着的面包,轻轻地递到伤号的面前。年轻的伤号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用惊恐的眼睛盯着面包,不敢去接。直到妇女硬把面包塞到他的手中,他才如梦方醒,抓起面包连裹在外面的纸都顾不上撕,就狼吞虎咽大吃起来,看得出他一定几天没有吃饭,饿坏了。
看到伤号饿成这个样子,妇女缓缓蹲下身子,用颤抖的双手轻轻抚摩着伤号头上的弹伤,失声痛哭起来!
悲恸的哭声撕心裂肺,骚动的人群一下子安静下来。人们惊呆了,一个个用惊异的目光注视着眼前的一切。空气仿佛一下子凝固住了,整条大街一片死寂。良久,人们才醒悟过来。这时,出人意料的一幕出现了:那些老人、妇女、孩子,纷纷拿出面包、火腿、香肠等各种食品,一齐向受伤的战俘拥去。
以后每每他来看我,我都细心地为他煮咖啡.并且把一块白色方糖放进他的杯中,为他慢慢、慢慢地搅动。
白色方糖
周末在广九大酒店的“卡拉OK”里听歌,看到一个20岁的女孩走上台去唱。也许心理准备得不够充分,旋律响起后,她才唱了开头一句:
“雨潇潇……”
这个女孩跟不上旋律,非常尴尬,正不知所措,再也唱不下去了。
有一个大胆的男孩,从座位上站起,快步走到台上,拿起另一只麦克风,站在女孩的身旁,待乐曲重又过渡到开头的时候,跟女孩齐声唱:“雨潇潇,恩爱断姻缘……”。唱了这开头的一句后,他放下麦克风,大方地回到自己的坐席上。那个女孩在他的“启动”下,有了信心,拉开了嗓子,大声唱到完。
当时我的心不觉涌出了一种感动。
那一年冬天,我独自走在广州的街上。经过公园前的马路,我正想着心事,忽然听到一声响亮的“喂!”接着被一个小伙子拉了一把。一辆红色“的士”飞快地从我面前擦身而过。我被吓了一大跳。当我定下神来想说声“谢谢你”的时候,那小伙子早已跨上自行车无影无踪了。
后来独自逛街过马路,我总会想起这位面影都未曾记着的陌路人。
从前有一个不快活的老头儿,他常来看我。他的老伴几年前过世了,唯一的女儿也嫁到了美国。他不习惯那边的日子,不愿意去住。他说:“我已是快人土的人了,还企望什么呢?”
这位孤独的老头儿没有任何企望,非常的节俭,不喝酒也不抽烟,但唯独喜欢喝咖啡。当我把一块白色方糖投入他的杯盏中,用一只小汤匙不断地搅动的时候,他竞感动得流出眼泪来。
偶然一个小小的动作,却触发了他的伤感,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呵!
以后每每他来看我,我都细心地为他煮咖啡,并且把一块白色方糖放进他的杯中,为他慢慢、慢慢地搅动。我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在这淡淡的苦味的杯盏中,他是否能获得一点儿甜意和安慰、一丝儿温暖?
爱,有许多种。人类的血缘之爱是天赋的。陌路人的爱没有血缘性,体现了人对同类的关心,和人之为人——这样一个大家族的亲密和温暖。这就是一种博爱,一种比血缘感情更深刻的东西,它有一种无形的凝聚力,把人类团结在一起。世上每一个人都需要爱,需要温情,需要帮助。别人给予我爱,我当把这爱,也给予别人。斯丹妮太太安静地听罢,拉过男人的手,将领带夹塞过去说:“好吧,那我就把它送给一个重新开始做好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