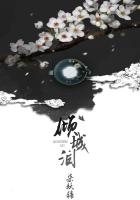杉瑚虽已心灰意冷,闻言却还是难以置信地看着他:“在你眼中,我和爹娘,便是如此对你的?”
对她而言,若真栽在那猪头肉手中,绝非她一个人被毁了那么简单。大庆女不许从商,等她女子身份暴露,就是欺君大罪!
如果祝公子再进一步追查下去,被他爹乃至上官尧发现她是杉瑚,杉家的希望便真的完了。
杉泽聪慧,不会不清楚这一点。
但他,还是如此做了。
华裳看穿她所想,冷冷一笑:“战王害我至此,我也不会放过他,你就放心地去死好了!剩下的,我会做的更好。”
“啪。”
又是一个清脆响亮的耳光,打碎了华裳扭曲的笑容。
杉瑚这次根本不给他任何反映的时间,上前一步,纤白五指来去如风,噼里啪啦就是十多个耳光,狂风暴雨般卷去。
她没有用内力,但力气之大,打得华裳晕头转向两耳翁鸣,扑通一声坐倒在地,杉瑚方才停手。
华裳漂亮的脸完全肿成了猪头,血红青紫开遍。他勉强撑开眼皮瞪着杉瑚,再说不出一个字,眼神之中震惊与后悔交织。
这已经不是他印象中的杉瑚了。
曾经的杉瑚,散漫悠然,从不与人计较。就算再生气,也不会对人掌嘴羞辱。
华裳浑身颤抖,比生命受到威胁更让他惊恐的是,他突然发现,他敢如此嚣张地设计她、暗害她、与她叫板,竟是因为……仗着她纵容他。
“竟然是这样。”
华裳不顾绽裂的嘴角,忽然凄厉大笑,笑声之中满是自嘲。狼藉不堪的脸不断抽搐,血沿着下巴滴落。
竟然,是他从来不如她!
可任他笑得如何疯癫,杉瑚并没有再分任何一丝注意力给他。
指头有些发麻,她认真地观察指尖红肿的程度,用另一只手力度适中地按揉穴位。
妖粉色的气体剥茧抽丝般自她指尖溢出,杉瑚讥诮地挑挑眉,手指一搓,那气体即刻凝固成团,被她弹泥丸一般弹了出去。
“香门引,果然不错。”
连这也奈何不了她?!让他当初一夜之间零落成泥的香门引,被这么轻松地解决了?
华裳笑声骤停,骄傲挺直的腰像被一下子抽去了骨头,颓然地一分分弯下。
在额头即将触到地面的前一刻,他停住:“胡老板,华裳错了。你宰相肚中能撑船,莫……杀我。”
言毕,“嘭”一声,额头实实在在砸在冰冷的地面上。
那一刻,杉瑚似是受到震动,缓缓抬起了眼。眼神落在虚空,她半晌一拂袖,避开他的叩首,错身向外走去。
直到出门,没有给他哪怕一个眼风。
华裳咬紧充血的下唇,缓缓抱紧了自己的身体。他跪在冰冷的地上,头顶抵地,蜷缩成小小一团。后背华袍之上,突出脊椎清晰的轮廓。
他藏了似笑似嗔的面孔,人们或许才能发觉,艳名远播的绿竹轩华裳,其实只是一个瘦得肌骨支离的少年。
今年,虚岁十四。
一门之外,杉瑚才合上静室的门,脚下就是一个踉跄。
她身体一抖,猛地躬身捂住胸口。红潮仿佛被压抑许久的猛兽,毫无预兆地反弹,汹涌地扑上她的脸。
短短几秒之内,她白皙如常的脸色便已消失得干干净净,红得似要滴血。
香门引能被奉为欢场第一狠药,哪里是她修习了两年的粗浅内力可以压制的?
强行驱逐,只让内息与药毒纠缠成团,四处乱窜!不觉情热燥动,有的却是刮骨抽筋之痛。
杉瑚咬紧牙关,勉强又走了几步,眉心一紫,身体霍地倒下。
闭眼前最后一个念头是:猪头肉急色至极,居然没来察看?
祝公子并没有转性,他确实心急如焚,但被横腰挂在苍天大树之巅摇摇欲坠,除了白着脸大叫救命,他还能做什么?
与此同时,只见墙倾如雪化,白影一闪,穿墙而过,半空之中突然出现了一个人。
墙灰浓密得遮挡视线,他却白衣如雪,泾渭分明地悬浮其间。好似盘古刚刚开天辟地,混沌乍破,烟雾腾飞之中突生玉莲一株。
他一袖子抽飞祝公子后,因懒得去寻机关,直接暴力毁墙。
人影又是一闪,路阶白在杉瑚身前蹲下,委地的长袍眨眼间便晕开一丝红。
她呕出的红,在他白衣上晕染出血色桃花,映入他的眼底,却似一点火星遇上火药,瞬间炸碎那片亘古平静的星空,怒火烈烈地烧起来。
他伸出手,触到她脉门的时候颤了颤,随即轻柔地将她抱入怀中。
身后有嘈杂的声音响起,祝公子终于被参将府的高手救了下来,此刻躺在一顶软轿之中,被士兵们簇拥着抬来。
见到倒地的杉瑚,他眼中一喜,随即就看见了路阶白,顿时气急败坏地坐起身来:“来人,来人,放箭!这个贱民擅闯官邸,打伤贵族,营救疑犯,论罪格杀勿论!”
“是!”众兵轰然应答,弓弩手立即里三层外三层奔上,围住了里面一蹲一躺的两人。
抬手一抹,刹那弓箭上弦,动作整齐划一。
路阶白却视若不见,眼神温柔如水,只将怀中之人笼罩。他抱起她,护住她的心脉。指腹轻轻擦去她唇上的血迹。
不怕,师父给你报仇。
现在。
随即他站起,转身,漆黑的眸子,冷冷盯住了祝公子。
祝公子心口一跳,莫名的恐慌让他杀猪般大叫:“射!给我射!”
“慢!”突有人长啸而至,啸声充斥着惊怒和警告,初时还远在长街,很快便到了近前。
一道身着戎装的魁梧身影发狂般扑来,他拼命伸手,胸腔之中爆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投陋!”
然而,已经晚了。
万箭离弦的那一刻,一枚红色圆物破空而来,“嗖”地穿过戎装者健壮的手臂,速度不减,带一溜血珠,从祝公子前额没入,击穿了他整个颅骨。
血箭飙射,洒一地殷红。
祝公子嘴一张,一个“射”字的余音还未消失,身体猛地一跳,随即向后软倒。
戎装者虎目欲裂,他看得分明,那只是一块凝结的血迹!
那人,呼吸之间,竟然剥离血块,融凝为珠,穿他手臂而不损!生生把他唯一的儿子,杀灭他怀中!
“啊啊啊!”仰天一声怒吼,仿佛天上降下惊雷一道,震得整个参将府都抖了三抖。
朱雀营第一参将祝雷,深得战王上官尧欣赏,如今已经快要拜将。但一直子嗣不旺,娶了十房妻妾,将近五十还是只得一子。
祝公子是祝家的一根独苗,如今却在他眼前被人杀死,祝雷只觉得理智都被那一道血箭击得粉碎,怒吼一声,抡起两把板斧,疯虎一般扑向路阶白。
此时箭雨落下,路阶白正抱着杉瑚。
他下意识要躲闪,但看见箭雨密集,突然想到倘若躲避之间有所疏漏,伤到她怎么办?薄唇一抿,他向前踏上一步。
一步,似踏入虚空,刺目白光突地大盛,将他的身影吞没。
浓烈至极的草木冷香之中,路阶白全身罡气陡然外放,从他周身开始,向外形成辐射之势,四方之箭一顿,顷刻碎成齑粉。
箭碎的同时,却也是他后继无力,护体真气破开的一刻。
巨大的阴影铺开,两道雪白的寒光从天而降,刹那已经逼近眼前。
路阶白不敢调动护着杉瑚心脉的那部分内息,没有任何迟疑,他微微一侧身。
板斧自背入肉,鲜血四溅。
但闻“咯”的一声,令人齿酸的骨裂声里,路阶白面无表情地回首,真气已经续上,重又流转自如。
宽大的白袖倒卷,犹如铁板般横拍,顿时将祝雷震飞。
两柄板斧自他体内飞出,流星般落在祝雷身边地下,劈出两道深沟。
祝雷噗嗤喷出一口黑血。
路阶白神情从容,但眼尖的人看到,板斧离体的瞬间,他身体微不可查地晃了晃,脸色一白。
雪衣已然形如血衣,他笔挺的后背上两道猩艳还在飞快扩散,似要从中生出一对血翼一般。
祝雷理智全无,满嘴是血,牙都裂了一半。他却呸地吐出染血的碎齿,漏着风厉喝:“这厮已经重伤!朱雀营八、九小队,速速斩杀!”
正在此时,一人狂奔而来,气尚未喘匀,便嘶声大吼:“国师在此,谁敢无礼?”
一群人浩浩荡荡拥入,冠盖如云,除了颜色为白,花纹为金色莲纹外,竟然与皇帝仪仗一模一样!
柳藻一看路阶白满身的红和杉瑚眉心的青紫,只觉怒发冲冠。
他一回头,从身后捧着皇帝御赐之物的人手中夺过那把“尚方宝剑”,噔噔噔冲到祝雷身边,举剑便砍。
“逆臣贼子,竟敢伤大庆国之圣尊!”
然而,一道指风掠来,竟然打歪了柳藻手中的剑。
“你报子仇,本座谅你。”路阶白淡淡开口,清冷的眼神对上祝雷,怒意尚存,却并非针对他。
柳藻气得直跺脚,但也无可奈何。国师原本坐在马车之中,但半路却突然冲出马车,直奔某处而去。他太快了,他们跟不上。
可是,后面仪仗不过跟丢了片刻,天下无敌的国师怎么就弄成了这副模样?
“柳藻。”
“是,大人。”
路阶白视线移动,落在祝公子的尸体上,眼底寒意森然,字字斩钉截铁:“将此子,鞭尸三百,挫骨扬灰。”
说完,他便抱着杉瑚转身。她从未重伤至此,是生是死不过一刻之间,他要立刻上车给她治伤。
但却听“啪”的一声,半空中突地一声脆响!
风声尖啸,一条长鞭犹如毒蛇出洞,闪电般扫来,竟似要把路阶白带杉瑚都拦腰抽成两半!
“在本王参将府中耍威风,你当本王是死的?”一人长眉入鬓,唇红如火,煞气凛冽地冷笑道:
“国师在此又如何,本王倒要看看,对他无礼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