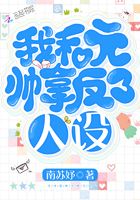“文化”也好,“流氓”也好,想来都不绝对是现代文明创造出的罕物,而“文化流氓”则似乎更是古已有之。
“古已有之”往往被视作支持某些结论的强而有力的证据,但懂得一点辩证唯物主义的人都清楚,“古代”往往只是“现代”的过去时,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变化,“现代”已不同于“古代”,有些情况下甚至连最基本的原理也被时间颠覆了。好比亚里士多德已无法与经典力学分庭抗礼,而经典力学却也无法准确地解释高速运动产生的科学疑团。所以总体而言,尤其自然科学,“古已有之”恐怕只能作为一种时间上的印证,连接着的不过是某些不应被忽略的历史渊源,而绝非称量真理的天平的另一端。
“文化”基本上是一个现代概念。古人理解的“文”比我们当今定义的“文化”狭隘许多,尤其“纹”的解释被“纹”分担了之后,“文”便几乎专指和礼乐制度以及文章词句有关的东西了。
而古人理解的“化”则是一个大道行空的宏伟的过程,它象征着通过人类的力量,尤其是精神的力量,把一般事务纳入到一种宏观的“宇宙逻辑”中。“化”的终端是“大道”和“生死”,是古人对于“天人关系”的博大思考。如《素问·五常政大论》所言的“化不可代,时不可违”中“化”便可以解释为“大自然”。而《礼记·学记》所言的“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则把“化”推到了“教化人民”的社会高度。加之我们所熟悉的陶潜的《自祭文》有“余今斯化,可以无恨”的句子,“化”便也可以被解释为“死”。由此可见,无论“自然”还是“人伦”,“化”都是一座连接着本领域制高点的天梯。
无论古人所说的“文”还是“化”与时下流行的“文化”的定义几乎是不着边际的。我们姑且这样认为:当今所谓的“文化”,其涵盖程度和深度基本上处于古人所谓的“文”和“化”的中间地带,在“术”和“道”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的支点。
“流氓”则比“文化”的历史附笔要曲折。因为“文化”毕竟在古代是一个模糊的概念,甚至在一般情况下,“文”和“化”决不能随意地组合拼接。而“流氓”则不同了。
古代当然也有“流氓”,而且即便是套用今天对“流氓”下的定义,也非常的贴切和正宗。只是有一点必须注意——古代的“流氓”不被称为“流氓”,甚至“氓”字都没有相应的解释和读音。这就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无”中生“有”,“有”中生“无”。
“文化”是典型的“有”中生“无”,人们的手边就有“文”和“化”两块金属,把它扔进历史的大熔炉里,任其成分合理搭配,便烧制出“文化”的合金来。“流氓”则是“无”中生“有”了,“流”和“氓”原本是南极和北极的关系,即便放在一起也是“流民”的意思,而经过一代代文人和百姓的亲历锻造,“流氓”便赫然充斥了文化市场的边边角角了。
历史上的真假流氓千千万,而“流氓”的脸谱历朝历代也描摹得风格迥异。先秦时期的“流氓”大抵等同于“小人”的概念,而“小人”却也并非谁的固定头衔,任何人身上都有“小人”的影子,所以那个时期的“流氓”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涵养、最讲原则的流氓了。而后世尤其门阀兴盛的时期,“流氓”则似乎是对穷苦百姓的蔑称,仿佛没有钱,尊严呀、荣誉呀、甚至个人的真才实学都是无从谈起的。“流氓”发展到这一步“文化属性”已被其“社会属性”所基本掩盖。其实想一想,但凡“文化属性”下降,“社会属性”上升的群体,其队伍是在慢慢萎缩的。先秦时期,但凡挂着些“小人”习气的都是“流氓”,其队伍之庞大,已渗透到各个阶级和阶层;而在后世,“唯穷人是流氓”的时期,“富人”和“地位高的人”就被分出了流氓的队伍……
所以认识“流氓”难于认识“文化”。仔细一想也本应如此,即便“流氓”是一顶龌龊的帽子,但顶着“流氓”这顶帽子的脑袋却是人的脑袋,人是最复杂的感情动物,“流氓”是人,所以“流氓”也很不简单。“文化”则不是对人群的划分做出的指向,纵使有“文化人”的说法,“文化”也应是一种描述客观事物的概念。看来一和“人”发生关系,就会产生翻天覆地的“化学反应”,有时会颠覆传统,有时会改变世界。
终于该谈到“文化流氓”了。可能前面做的冗长的准备已让你基本糊涂掉了,不过不要紧,下面读懂了也同样会有收获。但我不得不从自己做的“准备”出发来推开“文化流氓”这扇门。
首先,“文化流氓”古已有之,但同现在的相比还不足为外人道。我们所熟悉的余秋雨先生的《苏东坡突围》和《遥远的绝响》等文章,都对古时候文化流氓的轮廓有了较高水准的还原。但不足的是余先生对他们还不够狠,注入的诗意太浓,似乎在远远地、静静地审视一段段历史的情节。而古时候文化流氓耍起流氓来可真的没有什么诗意可言,“文化”往往是他们堂皇的借口和名贵的挡箭牌,“礼义”往往是他们涂在剑锋上的最狠的毒药。一旦获得机会,即便“乌台诗案”这样看似不是机会的机会,所有的毒箭和谗言便瞬间找到了靶心。但请注意一点,古时候的文化流氓一般而言还真的“有点文化”,所咬定的借口和罪名也一般是从文化上剥下的。这便会制造出一种“文化陷害”的模型,有点类似于今天的数学模型和物理模型,“文化陷害”会遵循一定的套路,甚至规则。举个例子,比如“焚书坑儒”和“文字狱”,执行这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必定是些文化流氓,他们的恶言像一把掏心的长钩,心肠像一条锁喉的绞索。然而他们寻找的借口,以及皇帝希望他们倚仗的借口必定是“文化”,诸如“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什么的,今天看来简直是笑话,但我们所没有看到的是——真正的滑天下之大稽不在古代,正在今天!
古代的文化流氓与当今相比,简直成了单纯无比,只是一缕嫉妒心作祟的文人或是兢兢业业、忠于皇权的无辜小吏。当今的文化流氓——触目惊心!在列出一大串劣迹之前先得想想为什么文化流氓继承祖业,发扬光大竟到了今天这种地步。他们的土壤是什么?他们的灌溉者是谁?最后——他们自己究竟是谁?
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土壤是现代传媒。这好比是一片肥沃的田地,既能孕育庄稼,也能喂饱杂草。现代传媒铺设了信息高速路,这帮醉汉就开始高速行驶,横冲直撞。古人最起码还有些文化认知,知道即使罗织罪名也要从文化上下手。而随着现代传媒的兴盛,文化流氓几乎已配不起“文化”二字,所以要保留“文化”的称谓,只是因为他们作践的最终只可能是文化。他们不再关心真正意义上的学术错误,因为那东西整人实在是不大顺手,况且没点儿文化,还真的发现不了什么这方面的差池。现代传媒也不再关心学者们是否把米兰·昆德拉认作是西方现代派的作家,如果有可能,他们倒确实想知道昆德拉究竟有多少情妇和私生子。文化流氓最中意的便是现代传媒提供的无限便利,可以在不翻阅受害者一本书的情况下把他斥责成不学无术、欺世盗名的蠢材,而且绝对一呼百应,诽谤文章也能卖个好价钱。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就没必要一味埋怨“现代化”了。因为再好的土壤,缺少了灌溉者也是不行的。那么灌溉者是谁呢?
我觉得大致有三种人。一种是媒体自身,上文已说过,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爆料才是硬道理”。再而是文化人自己。不要老是抱怨自己被别人骂得狗血喷头的,更不要觉得自己绝对无辜。“学术的沦丧”导致“道德的沦丧”,病根还在握笔的手老干些数钱的营生,讲课的嘴老是不停地寻找山珍海味和舞女们的红唇。
但为什么钱总是被一次次地当做论文的标签呢?这个问题不比本文的其他议论,不是明眼人一眼就能看透的,要想解答,就必须通过长期的调研。由于书斋的凳子已被我懒惰的臀部晤得发热,所以我不敢妄论。
第三种灌溉者是下一代。他们早已熟透了通往黑夜深处网吧的去路,因此也拉开了与传世经典在台灯下的距离;他们的洋文说的一级棒,签名超级酷,因此也告别了平中见奇的作文方式甚至作文语言,当然也告别了“二王”和“欧柳颜赵”。外国人把中国人问倒的情况每一天都上演在全世界的街头巷尾,下一代接受的是从西方的旧教育方式舶来的“通才教育”,其结果便是西方经济危机前所呈现的人才危机。
那么我们更要关注的是:文化流氓到底是哪些人?
诚实地讲:我不知道。
因为任何一家媒体都会在大张旗鼓地报道了什么“艳照门”之类的东西之后迅速沦为“流氓窝点”,任何一个道貌岸然的教授都会在开出天价的讲课费之后沦为金钱的奴才,任何一种观念都会在遭遇现实的拷打和逼供之后变得扭曲而奇特。我们已不能从人群中一眼就认出写着“流氓”二字的那张脸,也许包裹着邪恶的是几缕让人尊敬的白发,也许酝酿滑稽的是一所曾经声名显赫的大学……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侥幸心理,这便有可能在这种地狱一般的社会环境下派生出流氓逻辑,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离黑钱远一点,拥抱文化;离欲望远一点,选择太平”。
文化流氓不会消灭,但决不应是今天这副嘴脸。这个世界上的确有“高低善恶”之分,但一些不被历史所容忍的下作则绝不属于值得做出判定的范畴。
2008年7月23日
浅谈中国文人的审美习惯
中国文人,尤其是古时候的中国文人,对于“美”和“审美”有一种近乎偏执和狂热的喜爱。“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不难理解;但为什么对于“审美”这个过程本身还会投入浓烈的情感呢?
首先要解决的:究竟什么是“审美”?
“审美”当然是一个过程,只是由于它连接着的结果太过诱人,所以我们往往觉得“发现美”是水到渠成的事,中间并没有一段真正意义上的“路径”。这就好比雾蒙蒙的清晨突然在路旁欣赏到一树月季的安恬睡容,你只是一瞬间被“美”给搂进了怀里,而无法察觉它的双手何时插入了你的腋下。而这段在不经意间窥伺到“美”的“路径”,其实就是“审美”。
“审美”按一般人的习惯,分成两步;按文人们的习惯,分成三步或更多步骤。只是所有的“审美动作”类似于精神世界的“肢体语言”,你从头舞动到尾也不觉得有什么筋骨上的疲乏,因为那更类似于“意识的江河”掀起的一场悄无声息的水潮。
一般人的审美只有两步。第一步是“发现美”,第二步是“欣赏美”。而“欣赏美”则占到整个审美过程的一大半。因为我们一般人是不大觉得主动审美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缺少苦心孤诣地发掘审美现场的动机,“发现美”的过程往往是偶然的,所以也大半是短暂的。好比一个忙碌的樵夫,在树桩上看到一朵颜色绮丽的小花,他会怎么对待这个小小的审美现场呢?如果是我,我锋利的斧头就是问题的答案;如果是别人,很可能连发现它的几率都接近于零。历史上,据我所知,似乎只有一个钟子期。
我并不是就此质疑劳动人民对于美的认识水平,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品大都出自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双手。但大多数人会把创造艺术珍品当作赖以为生的手段,好比大型石窟的修筑者和堆砌长城的挑夫们,他们的汗水所哺育的不是东方美学,而是妻儿老小的一日三餐。当真正的“美”被逼到这个地步,就会产生令历史无所适从的尴尬,一方面我们不知该真正感谢谁,是朝廷的虚荣心还是英雄的无名墓;另一方面,以这种方式创造出的“美”必须去被动地等待后辈们发现“美”的眼睛和保护“美”的义举,否则再怎样珍稀的艺术在“铁蹄”和“无知”的夹缝中都身不由己。
至于一般群众“欣赏美”的方式是十分丰富的。文人们的审美往往会遵循一定的套路,审美的结果也大都落于文章,一般群众没有这么深的文化情结,所以大都选择了自己认为最满意的方式去“欣赏美”。比较常见的是北京人的“玩鸟”。玩法固然也有讲究,但绝无刻意的限制。你爱听黄鸟的叫唤,那就听,再怎么喜爱别人也不会有意见,为了锻炼小鸟的一条好嗓子,你哪怕吃糠喝稀如《茶馆》里的松二爷,也不必担心蟹白栗黄地供着小鸟会招人笑话;你想向别人炫耀一番自己的宝贝的毛色,无论是鸟身上的哪一处羽毛都可以拿来吹捧,你也大可以毫无顾忌地随便赞美。而百姓家的“行酒令”则比我们在《红楼梦》里所见的要有生趣的多,不必挖空心思地炫耀文采,也不必大伤脑筋地察言观色,唯一的要求就是“麻利儿着仰脖子干了这一杯”。
而文人们则对“审美”投入了更大的积极性,以致“审美”的历史与“文艺”的历史仿佛并行的两条铁轨,负载着人类沉甸甸的文明列车呼啸向前。
文人的“审美”大致分为三步。首先是“锁定美”,然后是“探寻美”,再而是“标榜美”。“锁定美”的过程往往来自文人手中的书本或是“谈笑有鸿儒”间的偶得,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唐代的文人。他们“锁定美”可谓“稳、准、狠”,即“发现得快,出发得勤,到达得顺利”。一大批诗人都有漫游的经历,以至于当今有些学者认为古时候走得最远的四种人就是“诗人、商旅、军队和僧人”,其实“诗人”和“僧人”的出行动机有很大成分的明显重合,所抱的目的也基本属于文化范畴。我们姑且不论旅行本身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李白杜牧他们还真应该和玄奘鉴真他们坐下来好好聊聊,没准还会爽快地相邀并结伴走上一程。这也顺便印证了另一个论断:文人的根扎在书斋里,叶结在旅途上。一旦找到了令自己心动的终点,就会向《为学》里的“二僧”一样整装待发了。
而“探寻美”则远远比一般人的“发现美”要来得艰辛和漫长。唐朝国运昌盛,治安良好,“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的事也不是总能碰到,李白他们的漫游相对来说要省心一些,可以一路上基本秉持自己的“文化初衷”。而在兵荒马乱时期就没有如此恣意随性了,文人们好不容易决定要朝着一处心中的圣地进发,但一路上哀鸿遍野,兵祸横行,旅行变得小心翼翼,以至于小心到战战兢兢、猥琐不堪,即便最终到达了世外桃源,想必也只是满眼的残山剩水了。所以我格外佩服乱世敢于踏上“寻美之路”的文人,他们实在配得起“侠骨柔肠”这四个字。而能像裴秀那样画出《禹贡地域全图》或是像郦道元那样写出《水经注》的文人,则真正担得起“英雄”二字,是中国文人的楷模!因为在文人的价值观里,对“美”的认真便几乎等同于对“生命”的执着,而对“生命”的执着是世间一切品德和学问的基础。
至于“标榜美”,则颇为复杂。
我们可以很轻易地想象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一个书生在晨诵时读到了一个可以作为审美现场的去处,如获至宝,心情大好;在之后的日子里,尝遍了旅途中的酸甜苦辣,最终衣衫褴褛,步态蹒跚地来到了梦中的精神家园。这样的情节已被小说和影视剧给摆弄得有些变态了,不过发挥我们的想象,从文化的角度出发,“锁定美”和“探寻美”还是一目了然的。但说到“标榜美”,则令人费解。其实顺着我们刚才设计的情节:在精神家园享受到了“美”之后,我们的书生于是从后背取下了书箱,把所有对于“美”的归结性感受交付给笔墨,留下了或许传唱千古,或许烟消云散的人生痕迹。这就是“标榜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