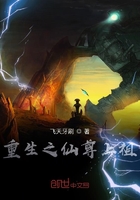王老头是河湾村子里的孤独老人,看上去约摸六十来岁,个子不高不矮,背有点儿驼,走起路来两手或是微向前伸,或是倒背在身后,总是带着一副匆忙忙而又庄重的神情。闲的时候呢,就一个人蹲在墙根下或是盘腿坐在炕上出神,嘴里噙着一杆长烟锅,吧嗒吧嗒地抽了一锅又一锅。他酱紫色的脸上虽然写满一道道皱纹,但这些皱纹都是顺着面部肌肉的纹里展开的。他的眼睛不大,眼球也有些混浊,不过有时也会闪出一点老年人富有经验的智慧。当然,他头发和胡子都花白了,但并没有秃顶。总之,你只要一见到他,就能看出他虽然带有一般孤独者的那种抑郁寡欢的沉闷,便还是一位神智清楚、身体健壮的老汉。他在生产上是行行都通的多面手,有时种菜,有时赶车,有时喂牲畜,包括撒籽踩垛,生产队派他干什么,他都是行家里手,而且从不计较工分报酬。他一个人住一口小窑洞。这小窑洞坐落在村边的沟口,紧挨大路,看起来孤零零的,门口有一棵硕大的皂角树。他住的窑洞里只有一铺炕和两个旧得发黑的木板箱,但收拾得倒很干净。除了一般性的贫穷之外,老人还有因为单身而形成的困难,“出门一把锁,进门一把火”就概括了他的生活。然而孤单的老人好象总有较强的生命力和免疫力,据我所知,他是从未害过病,也没有误过生产队一天工的。
听父亲说,王老头在解放前打了十几年长工,一直没有能力娶个女人。解放后,他分得了河滩几亩薄地。那一年他才三十多岁,凭他下的苦力和在农业生产上的技能,那几亩河滩地居然也长出了丰盛的庄稼。那时,他对未来真是满怀信心,而日子也的确一年比一年好起来。到了四十岁那年,别人给他说了个女人。当然,也没有好的姑娘愿意跟一个四十来岁的半大老汉。他的女人老是病病歪歪的,结果跟他生活了八个月就死了。在这八个月里,连置家带看病,他把几年的积蓄都折腾光了。合作化头一年,现实的遭遇真正使他认识到了单干无法抵御不测的天灾人祸,于是他把几亩河滩地、一头毛驴和她自己都投进了社里。一两年中,生活真的有了起色,他的希望又在一个坚强的集体中重新萌生出来。但是,正在他张罗着再娶个女人的时候,却来了个“******”。他本人被派去亢家河修水利了,他准备娶的那个寡妇并没有等他的义务,就又另找了个主儿远走高飞了。
我辍学那年,由于生产队劳动实行了协作与分工,加之引进了化学肥料和简单的农机具,河湾村土地的产量比过去有所提高,但交公粮、售余粮、卖贡献粮、留战备粮的数量总是超过提高的部分。记得有几年,上面派下的收缴任务甚至只有让农民饿肚子才能完成,这样,王老头只好仍旧打他的光棍了。
六十年代初,陕西、甘肃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庄稼颗粒无收,那年春季,一批一批的甘肃灾民拥到关中平原靠河川的河湾一带。他们有的三五成群,有的拉家带小,也有的独自行乞。他们每个人都背着一条肮脏的布口袋,准备乞讨一些干粮带给留在家乡的亲人。
一天中午,我从王老头家门前经过,从门里望去,老人正准备做饭,门口站着个操外乡口音的女人叫道:“大爷,行行好,给一口吧!”乞怜的声音打动了他,只见他把虚掩的门开开,看见外面站着一个三十多岁蓬头垢面的女人。他把她让了进来,叫她坐在炕沿上,就忙着做两个人的饭。一会儿,要饭的女人看出了这个老汉做饭时笨手笨脚,就小声地说:“大爷,你若不嫌弃,我来做这顿饭吧。”王老头高兴地答应了,自己装一锅子旱烟弓着腰坐在炕上。女人洗了手就开始做饭,动作又麻利又干净。同样的面,同样的调料,可是王老头觉得这是他五十多年来吃得最香的一顿饭。两个人都吃了满满两大碗汤面,王老头还嫌不够,看到要饭的女人像是也欠点,又叫再做些。
正在做第二次饭的时候,老队长薛发德推门进来了。
“嗬!我说你咋还不套犁去呢,闹了半天是来客了。”
“哪……”王老头不知为什么脸红了起来,吶吶地说,“要饭的,做要点吃的,吃了就走……”
薛发德是队长,又是贫协组长。“唉!实在可怜,一个女人家出来要饭。”他在门坎上一蹲,装了一锅旱烟。“是甘肃来的吧?家里还有啥人?”
“就是。家里还有两个娃娃,公公婆婆。”女人低着头腼腆地回答。
“别害臊,这不怪你。民国十八年我也要过饭,我女人也要过饭,遭上年馑了嘛。家里人咋办呢?”
“我们公社一人一天给半斤粮,我出来就少个吃口,省下他们吃。”锅里水开了,女人忙把面条下锅里。薛队长看见她切的面又细又长,和城里压的机器面一样。
“啧,啧!好锅灶!”薛队长灵机一动,爽朗地说:“我看哪,风风雨雨的,要饭遭罪哩。现在要饭又不像过去,每家每户就这么点粮,谁给呢!再说还这里问那里查的,干脆你就留在这里吧,给王老头做个饭干个啥的。王老头绝对让你吃不了亏,这可是个老实人,我知道。”
女人背着脸用筷子在锅里搅和,没有搭话。薛队长转向王老头说:“你先去把犁套上,田贵正找你呢,那几个毛手毛脚的后生近不到青骡子跟,套了犁再来吃饭。”田贵就是他那当队长的本家侄儿。
王老头把烟袋别在腰上,到饲养室去了,抽两袋烟的功夫,薛队长也到了饲养室,喜笑颜开地拍着王老头的肩膀说:“****的,你的艳福不小啊,人家愿意留下,跟你过日子,看你拿啥来谢我呀?眼下她口还没说死,以后你好好待人家,再生下个一男半女的,她的心就栓住了,有钱没有?没钱的话,打个条子,我给田贵说说,先在队上借点,给人家扯件衣服。”
王老头咧着嘴笑着,满脸写着的皱纹像开了一朵花。晚上收工,他一进门,女人就不声不响地给他端上碗热腾腾的油汤面条,她自己也坐在旁边吃着。她梳洗了一下,再也看不出是个讨饭的乞丐了。吃完晚饭,王老头叼着烟锅想说点什么,女人在洗锅抹碗,他才发现整个锅台案板都变得油光闪亮的,油瓶盐罐也摆放得整整齐齐的了。
“王老头啊!恭喜恭喜!”这时,大个子薛队长低头推门进来,他两眼在屋里一扫,忍住笑说:“对,这才像俩口子过日子的样子,真是蛐蛐儿都配对哩!给,这是十块钱,明天队里给你一天假,领你女人到陈村镇看买点啥。”
王老头忙下了炕,把一锅子烟装好递到队长面前,一面张罗着说:“坐嘛,坐嘛!”
薛队长没有坐,掏出自己的“宝成”烟,还给了王老头一支,笑着对那女人说:“是甘肃来的?那地方苦情,我知道。咱这周围村子里还有你们那里的人,也是逃荒过来的,都先后跟庄子里的人成家了。咱这地方自古以来不欺负外乡人,再说王老头可是个好人,这些年来给队上没少出力,你安心跟他过吧!艰苦奋斗嘛!稀的稠的短不了你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