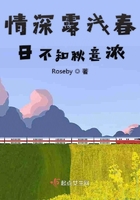而每每如此,她总是那么阴沉地把自己裹在窗帘的背后,绷带是那么厚实地挂在她空了的眼眶里,我再也看不到她的眼睛,但是我却是很明白地听到她说:“你能把你的一辈子赔给我么?”我终是沉默,她也冷笑,指着门就狠狠地叫嚣:“不能就滚!别他她在这儿给我放屁!”
我当然不敢滚,她不会希望我走的,我若走了,我便恨死我自己的,因为亏欠,而无法善终。风还在吹,就在这离天最近的危楼上,命也变得坠落,我抱着必死的心,最后看了她一眼:“我是该死的。”“你真那么想死吗?”她白色的绷带终是受不住凌厉地刮落,我看到了冲过来愤恨的掐住我的脖子,从这个几乎天翻地覆的角度,我看到了她没有了眼珠子的眼睛,是虚无一样,拿再多弥补也填不满的样子。只是,我欠她的不是么,我再没有一辈子,如果我死了,她能从阴霾里走出来,那我愿作太阳,起码地,还须有光,将她看不见的世界,一一点亮。
“是……”我微笑着闭上了眼睛,是真的笑着念着奈何,准备好了拿自己空无得一文不值的灵魂,去祭奠那碗通往来世的孟婆汤。“哈哈哈!哈哈哈哈!……”她开始哭着含笑,那属于她的,冰凉的泪,就这样子打在我脸上:唯一的,右眼的温度。
“柳薪!”我轻轻撑开了那睡得几乎不想醒来的眼皮,她却是走远了,风吹得更厉害了,似乎是成心地,天像从棺材里爬出来的鬼一样,动不动就一片要死的颜色。她就走在那种灰冷的色调里,那步子像吞吞吐吐的云一样欲言又止,我竖起了泥雨一样苏醒的耳朵,然后我听到她头也不回地说:“我走了,别来找我了,只想你知道,我他妈恨你!”
柳薪是真的走了,我去了医院,而病房里那床白色的被褥也该是被她叠好地,四四方方地紧挨着那骨头一样瘦巴巴的床架子,吊瓶还是吊死鬼一样地吊着,她该是不想要那种滴答的流逝,正如她不想要这滴答流逝里滴答跟随的我一样。所以才走了,如云,也如风,干净得不曾来过。床架边白色的小柜上有一个保温壶,当然是冷了的,但还有些余热的,是下头压着的那一封信,我轻轻地把信封拆开,抽出了那里头带有淡淡香水味的信纸来。那是密密麻麻的,书写得很是秀丽的字儿,就睡在纸上,伴着风吹的苏醒诉说:真的走了,你别送了,虽然我是无比地希望能在一回头的时候看见你,看着你那比星星还要亮的眸子,能一辈子,照在我看得到你的地方,能有光,能是灰色天空的涂抹的那金色,而只要能看到,我就不再是瞎子。可是终究看不到的,就在我决心离开你的那一刻起。
总记得,你从不愿正眼看我,尽管我是这么不要脸的坏姑娘,每天戴着很红的头花,一副贱到那么希望你理的样子。可是亲爱的,那有什么办法呢,我一天想你二十四次,每隔一个小时心就激动得敲一次,我是真的病了,以至于再活过来的时候,看不到你,我是那么怨恨地晕过去,呼吸那么地难,我要死了,就像一条搁浅的鱼,缺氧在没有水的空海里,没有太多安息。你该骂我太过不甘了,既然活过了,为什么还要长久?
可是我就是这么贪心的,自始至终我都是个不知足的孩子,幻想着能有和你的牵手,画满我孤独渴望着幸福的星空。实话说,我并不温暖,因为有一个有权有势的爸爸,有了一切,却丢了世界。我总觉得上帝该是个瞎子,我那么高贵漂亮,为什么活得还不如那些平凡庸俗的丑女来得精彩呢?
所以我成了个天生的坏孩子,有很多的男朋友,调很多的情,每天喝很多的酒,换着不同的大奔潜伏到那些想偷腥又怕学坏的乖宝宝家中,看着家长们鄙夷而担忧的脸色,而无比满足地大笑,直到我遇见了你。哦,是的,你。初见时的腼腆少年,我永远忘不了你是那么斯文的戴着眼镜,抱着书跑到食堂去吃饭,因为不想和坏女孩儿打招呼,而说两句话,就恨不得要吓得跑的样子。
从那时我就知道,你不可能喜欢我这样的女生的,所以我是那么地恨,恨自己不是一个好孩子,做不了乖乖女,所以第一次的心动,就那么没结果地死在了无花树上,病怏怏地风干。可是,你怎么就不能爱呢?你定是嫌我烦的,那我可以改的,你定是嫌我孩子气的,那我可以每天穿着校裙,扎着高高的马尾扮清纯的,可是天偏偏捉弄地让我看清,你最终喜欢的是男人,这种我改变不了的偏向,不是风一吹就能虚无地,但是我发誓,我真的愿意为你变成男人,就像你愿意为了那个山孩子,变成女人一样,这是不假的,你看得到我剪很短的头发,穿很拉风的靴子,戴很男人的耳钉,我是那么真心地想要彻底地赌一次,可惜变性机构的技术落后得没法支持,呵呵,这该是多么扯淡的遗憾。
好了,不说了,话说多了,你一嫌烦了,这辈子都不会记住我了,你总说你欠我,现在互不相欠了,因为那只眼睛,就当是我想你正眼看我的,一次不算贵的代价吧,两清了,所以别见了,你可能也不愿意知道我会去哪儿,所以我也不会说,那么就无言吧,就像从初识到分离,我们始终无缘无份一样,不再有天亮,不是因为少了眼睛,而是因为少了你,闭上眼睛,那便是永无天日的:天黑。
“柳薪……”风也似乎无言了,我唏嘘地叹息,紧紧地把那封靠着无言诉说的信攒在了手中,恍若世界都暗了。“真的是你呀,我还以为我老了,看花眼了呢。”虚掩的房门在这时候被推开,我擦了擦湿润到了眼角的泪,这才看清站在病房门外向内张望的,正是那日领窦泌出院的时候,窦泌出言冲撞了的大爷。他拎着一个藏蓝色的布包,而今更为沧桑地两鬓,明显更加斑白。
“寸草那小子还好吧?”他走了过来,笑起来眯起的眼睛,爬满了迎着光发亮的皱纹。“老想他了!”他说:“这小子,嘴皮子利索,他回去以后,我这孤寡的老头子过得冷清哟!”“哦,不,我从他们寨子回来有些时日了,所以他的近况,我不是太了解。”“哦,是么?”“嗯。”我有些抱歉地看着他,他的写着失落色彩的眼里,是微笑着的,慈父般的弧度。“这样呀!”他问:“那你还回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