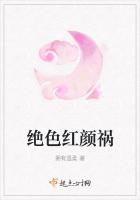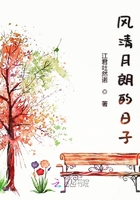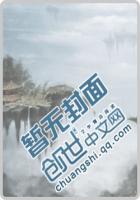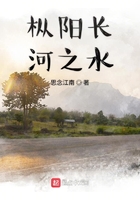朗格指出,生命之物的存在是靠渐次积累的过程,与人们在无机变化中所发现的那种简单的变化法则不一样。它们吸收周围的因素到体内来,而摄来的因素就遵循作为“生命”有机形式的变化法则。摄取非己的因素并使其参与本身生命活动的同化作用,即为生长的原理。除了同化作用之外,还有新陈代谢活动。这里的新陈代谢活动是指每个生命体都要死亡,而以一个新的生命体来使这个种类继续下去。有机体的新陈代谢活动一直在进行着:非生命物质被吸收后,变得有了生命,但这是一个不断氧化的过程,析出的因素也要被排出体外。它们被分解之后重又回到无机结构中,即死去。生长超过颓败时,生命体长得大些;两者平衡时,生命体便维持原状;而颓败的速度快于生长时,生命体就要腐朽了。代谢过程在某一时刻突然停止时,生命即告完结。正是经过这样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每个种类的生命体都会以同一种“永恒的形式”存在下去。朗格认为,“生命物质总是要获得形式的永恒性;但形式的永恒性不是它最后的目标(最后目标终有完结之时),而是一种不停地追求又总是在每时每刻已经达到的目标。因为达到这一目标完全依赖‘生命’活动。而‘生命’本身是一个过程,一个无休止的变化;如果生命停止,它的形式即行解体——因为永恒是一种变化型式。” 在朗格看来,只有生命才能显示出形式的永恒性。也就是说,只要生命付诸运动便会取得某种“永恒的形式”,直到生命终止。但是,作为有机体的人,不同于动物和植物,因为人除去上述两种基本活动(指同化作用和新陈代谢活动)之外,还具有一种集中表现在情感、情绪和其它感觉能力之上的生命活动。天才的艺术家正是巧妙地利用艺术品与生命体之间的类似性,从而把多种多样的人类精神、情感、个人经验和想象向人们展示出来。
关于生命形式的基本特征,朗格认为,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说,是什么样的特征把一切具有生命的事物与无生命的事物区别开来。她的答案可概括为四点,即有机统一性、运动性、节奏性和生长性。就一件艺术品来说,也应该在逻辑意义上不同程度地具有与生命形式相对应的这四个基本特征。
第一,有机统一性。有机统一性是说生命体的每一部分都是极为紧密地联系着的。朗格认为,凡是一切能认识出来的具有生命的事物都是有机的,一切有生命的事物都是有机体,它们所具有的基本特征也就是有机体内有机活动的特征,这就是:不断地进行消耗和不断地补充营养的过程;在这个有机体之内,每一个细胞,乃至构成每一个细胞的细小组成成分,都处在一种持续不断的死亡和再生的过程之中;细胞、由细胞组成的组织、由组织组成的器官以及由器官组成的整个有机体。这整个组织系统都处在永不停息的运动中。一个有机体,初看上去似乎是世界上的最为独特和个别的事物。事实上它根本就不是一种事物,它那各别的、独特的和类似普通事物一样的存在形式实质上是一种变化着的式样,它那统一的整体也只不过是一种纯机能性的整体。但是,在这个整体之内的那种机能性的结合却有着难以形容的复杂性、严密性和深奥性。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一个较为高级的有机体的“自我——本体”(即那些极为精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有机体的自我——本体)比起那些更加永恒性的物质凝结无(如一块石块或铅块)看上去更加可信。因为人类的本体是一种机能性的本体,是一种物质的和精神的式样,是一种活动的连续。
生命形式的这一特点,在任何一件优秀的艺术品中都充分地体现着。这种体现包含了两层意思:其一是说艺术品是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其中的每一个成分都不能离开整体,离开整体的成分必将失去意义。反之,从整体中去掉某一部分,比如从绘画中去掉线条,从音乐中抽去节奏,雕塑中忽略光线,诗歌中放弃韵律等等,艺术都将遭到破坏。其二是说艺术的内在结构呈现出一种有机形式,各构成要素之间,如一定的风格与一定的材料选择;一定的情节内容与一定的音韵、节奏的安排;一定的旋律与一定的和声配器等等,都有一种神圣的契合,这种契合既不可侵犯,也不能随意更换,就像一个生命体中的组织有排异性一样,违背了这种契合,生命形式便被打破,情感的表现便趋于消失。正是因为这样,古今中外的艺术大师从来就强调艺术作品的完整和统一,用有机性一词来比喻艺术创作的协调和准确。朗格则以哲学家的高度,从哲学、心理学的层面去探讨和追踪有机性这一比喻更为内在的实质,指出有机性并非完全是艺术创造的技巧性原则,而是艺术作为情感符号的第一个必要条件。这一原则不是随着艺术发展逐渐为人认识,而是与人类创造情感符号的整个过程同生同在。
第二,运动性。朗格认为,生命体总是在不断地吸收,不断地消耗,细胞和生命组织都处于不断地死亡和再生的过程中,因此整个生命提都呈现一种永不停息的运动状态。运动一旦停止,有机体就随即解体,生命亦随之消失。优秀的艺术品既应当也必须包含着这种生命的运动的形式结构。比如,当我们观看舞蹈艺术时,“我们看到的是力的相互作用,但这种力并不是砝码具有的那种力,也不同于将书推倒时所用的推力,而是那种仿佛推动着舞蹈本身的纯粹外观的力。在一组双人舞中,两个人似乎是接受了一种力的吸引而紧紧地连结成为一体;在一组多人舞中,所有的人似乎都受到同一个中心力量或一种能量的激发。一个舞蹈的构成材料就是这个非物质的力,只有在这种力的收缩和放松、保持和成型中舞蹈才具有了生命。而那个作为它的基础的真正的物理力反倒消失了。如果观赏者看到的仅仅是一种体操和队列,艺术品便消失了,创造也就失败了。” 这就是说,舞蹈创造的是动态的形象,展示的是生命的运动性。同样,一首乐曲是由在时间中运动和发展的乐音构成的,而舞蹈演员所创造的却是一个力的世界,这个力的世界是通过一系列姿势的连续展现而显示出来的。这是舞蹈艺术与其他艺术所不同的地方。但是,既然空间、时间、事件和力在现实中都是相互联系着的,那么所有不同种类的艺术也同样是由这样一些错综复杂和各个不同的关系联系到了一起。因此朗格认为,每一种艺术形象,都是对外部世界某些个别方面的选择和简化,都要经受内部世界运动规律的制约和限定,当外部世界中的各个方面被人类逐一选择和注意到的时候,艺术便产生了。每一种艺术都有自己独特的再现外部现实的形象,然而这些形象都是为了将内在现实即主观经验和情感的对象化而服务的。对人类本质所作的首次对象化必然是动态的舞蹈形象。因此,舞蹈可以说是人类创造出来的第一种真正的艺术。
朗格认为,一切优秀的艺术品都显然包含着人类生命个体永不停息的运动的形式结构。音乐、舞蹈、戏剧等所谓的“时间艺术”固然均表现为一种运动的形式,其中尤以音乐表现得最为直接。汉斯立克甚至把音乐的本质说成是“乐音的运动形式”。但由于在绘画、雕塑、建筑等非时间性艺术中,形象呈现是一次性的,外在形式不可能真的运动,对此朗格便从视觉心理效果的角度来论述其运动特征。她指出,知觉运动有一种自然规律,它使快速运动的点看上去就象不动的线,这一规律的反向运用,便使线条可表现快速运动,比如流水、瀑布。另一方面,线条可以分隔空间的界线或标示具体物质的轮廓线,故能表示静止。由于虚空的创造,艺术品所描绘的事物与自然脱离,当人们观赏艺术时,就会产生运动幻觉,静止的东西在直觉与想象的作用下成为运动的东西。整个艺术品中该动的则动,该静的则静,该快的则快,该慢的则慢,无处不呈现出一种生机,无处不与人的生命合拍。而由线条所创造出的空间又可以根据运动行为本身成为一个时间性的空间,这就是说,它应该成为一个“空间——时间”性的形式,“这个形式随时都可以按需要变成一个表现持久性和变化性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形象,即呈现出生命活动的典型特征的形象。” 朗格的分析是很有见地的,历代的艺术大师、艺术理论家对于静止的艺术也总是强调一个“动”字。法国大艺术家罗丹就曾说过:“如果不首先使自己要表现的人物活起来的话,那是不会感动我们的……在我们的艺术中,生命的幻象是由于好的塑造和运动得到的。” 拉玛札也说过,一幅绘画的最优美的地方和最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能够表现运动。可见,任何类别的艺术都有运动的结构。
第三、节奏性。在朗格看来,任何一个活的有机体中,所有的活动都是一种有节奏的活动。众所周知,我们自身的许多行为——走路、划船、劈柴、敲打地毯等——都会因为具有了节奏性而变得轻松容易起来。但究竟什么是节奏呢?朗格指出,大多数人往往把节奏看作是相类似的事件(活动)在相当短暂和互相等同的时间间隔中的重复出现,亦即把节奏看作是一种周期性的交替。其实不然,在她看来,节奏主要是与机能有关而不是与时间有关;这里所说的事件并不仅仅是指在某一时间片段内持续的事件;事件事实上也是一种变化,亦即一种有开头和结尾的变化过程;举例说,苹果落到地下就应该算作是一个事件,在开始时先是苹果与承担它的树枝相脱离,结尾时便是苹果静静地躺在平地的某个位置上。它落地过程中也包括着苹果落在地上之后在地面上的滚动,而这种滚动又可以被看作是另外一个事件,即苹果落地之后便开始滚动起来的诸动作所组成的事件。当前一个事件的结尾构成了后一个事件的开端时,节奏便产生了。最典型的节奏便是钟摆的摆动,钟摆的下冲动量使摆向着与重力相反的方向(即向上方)运动,从而使它具有了一定的势能,这个势能又反过来继续使钟摆向下冲击;这样一来,第一次摆动便变成了第二次摆动的准备,第二次摆动事实上早已经就包含在第一次摆动之中了。以此类推,所产生的结果,便是一个有节奏的序列。在一个活的有机体中,所有的活动也都是这种有节奏的活动,这种活动有时并不仅仅是由同一串互为因果的事件组成的,而是由许多串具有不同节奏的事件链条的同时作用形成的。在有机体中,最明显的节奏活动自然是心脏的跳动和呼吸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