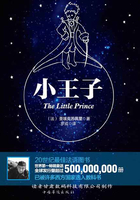复行三个月终抵京畿长安城,远远便可瞻望到未央宫红瓦镏金,飞檐高椯,巍巍立于天地之间。
“阿爹,我们这是到长安了吗?”我问阿爹。
阿爹灰白胡茬不住颤动,嘴里一个劲地感叹:“到了!到了!到了!”
阿娘也钻出车篷,我上前扶阿娘下了车,“阿娘,我们到了,我们到家了!”
一向情绪不外露的阿娘亦是泪光点点,轻咬薄唇不说话。
我不禁眼眶热热的,阿娘伸过衣角给我擦泪,我赶忙嘿嘿笑笑。长安城,天子脚下,我心里起了一份希冀。
“当下最要紧的是有个家。”我在阿娘身侧叨念,“我们一家三口加飞红巾、阿黄,应该先盖两间,一间阿爹阿娘住,还有一间我和飞红巾、阿黄住!”
阿爹去山上砍木头,我和阿娘照着长安草庐的样式搭架。毛坯架好后,我用脚蹭蹭,倒挺结实的,挨几个月没问题。
我拍拍手对阿娘说:“阿娘,夏天住这房子最合适了,我们犁地赶车,到了冬天,有钱再盖新房,要盖土坯房!”
阿娘会心笑笑,“我家丹心不适合犁地,阿娘会找人教你识字,有才学有见地才好。你要想学其他,阿娘也会满足你!”
我黯然撇过头,我怎么能做这样非分的要求?这时阿娘又捂着胸口咳了声,我忙拿过水囊,凑近给她喝了点水,关切道:“舒服点了吗?”
“老毛病了。”阿娘对我笑笑,“没事儿的!”
“今日初几?”阿娘问我。我答道:“初五。”
她若有所思,却只淡淡说了句:“扶娘上榻休息。”
我点头应诺,将阿娘安顿妥帖后,又自个儿忙活,忙到晚上,自己也累瘫了,两腿一抬也上榻休息。
睡到子时,顾及阿娘,我又起身,听得二老呼吸均匀,倒也安分地退了出去。
第二日,阿爹起床下灶,我担心阿娘,又去看阿娘,却见她双目紧合,双唇紧抿,原本苍白少血色的嘴皮竟是泛着青色。我惊慌地喊她:“阿娘,阿娘!”
阿娘却不见反应,我急着冲外头大喊:“阿爹,阿爹!”
“丹心,怎么了?”阿爹听我呼唤,急着进了门,见到阿娘,一把将她搂在怀里,“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听不到回应,阿爹拍着大腿哭喊:“你怎么这样傻呀?”
阿娘艰难睁开眼睛,目光涣散,“老头……我……这次真的要走了……”
“不会的,不会的……这是你的孩子——丹心,他还这样小,他这样乖……”阿爹把我拉到阿娘边上。我泪眼迷离,对着羸弱的阿娘说不出话来。
“他不是我的孩子……”她凄凉地呼喊,“我的孩子早已死了……”
阿娘说完这话时,吐了一口血。
“莫说胡话,我给你找大夫去!”阿爹放下阿娘的手,“我去给你找大夫,长安城的大夫定是最好的,我去给你找!”
阿娘欲拉紧阿爹的手,却被阿爹挣脱。望着阿爹的身影,我安慰阿娘:“阿娘,阿爹给你找大夫去了,你很快就会好的!”我紧紧握着阿娘的手,阿娘的眼睛睁着,泪水衬得她双目清明,我一时竟觉她美得惊人。
她紧拽住我的手,“丹心,你是我唯一的牵挂,记得照顾好……照顾好你阿爹……”
“嗯!”我点头又摇头,照顾阿爹是为人子女的责任,丹心义不容辞,可我不能忍受阿娘和我诀别。我已失去师傅,怎么可以再失去一个亲人?不,绝不可以!
片刻,阿爹领着一个穿深蓝色长衫的中年男子进来,“大夫,这边……”
大夫仔细看了看阿娘的舌苔,又翻了翻阿娘的眼睛,神色凝重,“尊夫人这病怕是拖不了三日……”
我号啕大哭,急着拉大夫的手,“你一定有办法的,大夫!你说,千难万难,丹心也一定做到!”
大夫长叹一口气,“唯一的方法是用西域的天山雪莲和昆仑山上的雪蛤入药,可这两味药千金难买。我看你就是押上你家那头黄牛,连个零头也凑不足呀!”
“大夫,你这样说可是……”阿爹闻言几欲晕过去。
“唉!恕我无能为力,你另请高明吧!”大夫推辞离开,“老夫无能为力!”
“我阿娘不会有事的是不是?你说那天山雪莲我有,那并不是什么稀罕物,想来那雪蛤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拿雪莲跟你换行不?你把那雪蛤换给我!”我抓住大夫的长衫,师傅去阴山采的便是雪莲,我包裹里还装着风干好的莲芯。
“黄口小儿,你知道什么?”大夫扯开被我抓住的衣角,“雪莲可有,雪蛤难求。前者用作清热止咳,只作辅药,一般寒地便可求得;后者却是至寒之地所产至阳之物,怎可轻易得到?你即使把天山上所有的雪莲都摘下来,你摘上十年,才换得来一只雪蛤!”
“我娘得的只是咳嗽,你若有见识,何须用这般稀奇古怪之物?”我死死揪着大夫衣裾,“庸医骗财,是不是?”
“丹心,莫要无礼。”阿爹拉过我,我死拉着大夫的衣裾。
“令堂不是生病,是中毒。”他叹息,“此毒若在寒冷之地,倒也不会要了命,只会经常咳嗽,可长安天气燥热,夫人便有性命之忧。”
“我不信,我阿娘在雪地里也要烧炭火加温暖身,怎么会惧怕长安燥热?”我辩驳。
“我推断是夫人最近受了刺激,心情不稳,加之天气燥热,致使体内余毒侵蚀心脉。”大夫似乎很肯定自己的推断,不禁又摇头,“此毒一经发作,难压呀!”
“你胡说,我娘怎么可能受了刺激!”阿娘心性平和,待人宽厚,怎会平白无故受了刺激?
“我已说明了缘由,那宝贝没千两黄金怕是买不来的。”大夫伸手推开我,拔腿要走。
“那你总得告诉我是什么毒?”我不死心,不肯放手。
“醉仙毒。”大夫正色告诉我。我听得是这毒药,连连退步,直接跌坐在地上。
我听师傅说过,此毒无色无味,可慢可急,经由奇特芙花和特定木屑混制而成。至于具体是何种木屑和何种芙花,我并不知晓。可我清楚地记得师傅说过:“毒入心肺,中毒者咯血;毒入骨髓,几乎无药可解。”
千两黄金,我该去哪儿找?大夫所言虽不一定是真的,可要治好阿娘的病,即使不须千金也是得要花上百金的!
我坐在地上,阿爹拉着阿黄往外走。我起身上前拉住阿爹,“阿爹,你这是要把阿黄卖了吗?”
“还有什么办法,先给你阿娘换几帖药吃吃,真的不行……”阿爹摇摇手,泪又流了下来。
我心里苦涩,看着飞红巾,它正悠哉地吃着我刚从田地里抱来的秸秆,看它吃得津津有味,我于心不忍,泪水又迷离了双眼。
“飞红巾,这次丹心真的对不住你了,阿娘待你我这般好,我们……”我拍拍飞红巾的头,摸摸它的眼睛,它也乖巧地对我眨眨眼,似懂非懂。
“飞红巾!”心痛得紧,我一把抱住它的头,泪水流个不停,“飞红巾,我的飞红巾……”
飞红巾不恼,伸出舌头亲昵地舔我的脸,我脸上的鼻涕眼泪都被她舔干了,脸上麻酥酥的,不由破涕为笑,“飞红巾,你这是要我不哭吗?”
自我打小记事,飞红巾便在我身侧。六岁的大雪夜,师傅带着一匹受伤的小马回家,替它包扎伤口上药,那时的它痛得瘫倒在地,我便伏在地上取悦它,当时马儿似乎与我心有灵犀,也伸出舌头来舔我的脸。那时被逗得浑身痒痒的我,直接在地上打起滚来,在场的赵信大哥和师傅乐得咯咯直笑。师傅、飞红巾、我、赵信大哥,我们都是一起的,从来不曾分开过。小时调皮,我在书上见了“火牛阵”,一时手痒,跃跃欲试,竟用炭火去烧飞红巾的尾巴。看着那鬃毛起火,我又惊又喜,飞红巾惨叫连连,我当时就愣了神,幸好赵信大哥赶到,才未酿成大祸。为此,师傅要狠狠责罚我,好在赵信大哥给我求情,免了我一顿鞭子!
慢悠悠地走在长安的大街上,我一路想:飞红巾,我不骑你背,不夹你肚子,不抽你鞭子……你会不会舒服些?我怎么老待你这么狠心,又蹬你又抽你?
望着飞红巾高壮的身影,泪水又不争气地溢出双眼,我在心底暗骂自己:刘丹心,你真是个不争气的家伙!师傅给的,没一样护得住,什么都丢了!干将剑不在了,飞红巾又要……又要离我而去……
“长安城中自有富贵人家,飞红巾,以后你天天都有苜蓿吃,不会被逼着赶路,天天提心吊胆……”我似在安慰自己,可嘴角抽动,怎么也说不下去,只能抱着飞红巾,埋头大哭。
鬻马救母,欲求千金——飞红巾,我真要把你卖了吗?想着这念头,我眼圈又红了。
我哭着鼻子卖马,引来赶集之人争相观望,大家对我指指点点,不过却都站得远远的,只看热闹。
“哟!我倒是要看看这是什么马,还抵得上千金?”声音很是清亮,我不自觉地转过头,可听得出他言语傲慢,我并不打算搭理。
“我要看看你的马。”他没了方才挑衅的口气。我抬眼便对上一英气公子哥,他身着白色锦衣,眉目俊朗,可眉宇间颇有傲气,一看便知是长安城中有钱人家的纨绔子弟。
“千金可得,良驹难求,如此无礼,便有千金,也难得此马!”我不饶口舌。眼前这少年,不过一富家公子哥,和这样的人议论,实在无趣。何况,我的飞红巾何止值这个价?一想到这,我的心便一阵绞痛,赶忙欺着自己:我的飞红巾,它不是拿来卖的,不是的!
“你!”少年瞋目怒视我,一脚踩在我铺设在地的横条上,一双绣金纹兽的靴子映入我眼帘。我气得跳起身子,也怒目对着他。
“大哥,不要动怒,此马好坏,我们问问父亲便知!”少年边上冒出一个个头跟我差不多的毛小子,正咧着嘴对我笑。
那小子两眼清亮,可门牙居然还没长好!我望着那小子,忍俊不禁,我早在十岁便换齐整了牙齿,这小子应该也有十一二岁了,居然还没长好牙。
他似乎明白我在笑什么,赶紧抿嘴,转头看马。我见他的目光在飞红巾身上流转,颇有贪婪之色,不由瞪了他一眼。这毛头小子被我一瞪,赶紧逃开。
“爹爹,彘儿要爹爹过来做伯乐,给彘儿相马!”不一会儿,这小子拉着一位身着华衣的男子过来。
“好马,好马!此马可是难得一见的千里良驹呀!”华衣男子不住拍手称赞飞红巾,“此马身形俊逸,剽悍精实,头颈高扬,眼大眸明,耳小而聪慧,鬃毛不见有下垂之势,再看那对蹄子……啧啧,纵然是追风闪电,恐怕也是赶不上它的!”
“爷好眼力,此马并非中原小马,而是西域大宛国所特有的天马,十分稀罕。此马是胁如插翅,日行千里!”飞红巾,有人识得你,我真该为你高兴,以后你不会被埋没的,你不用再吃苦了!
“小娃如何识得?”华衣男子面容慈善,上前摸摸我的脑袋,试探着问话,“你怎会有此马?”
我吸吸鼻子,方道:“阿爹为匈奴所虏时,此马不慎受伤,落入我家中。我和阿爹阿娘好不容易得以重回长安城,可现在阿娘重病在卧,不能……”我呜咽着,“爷是识得好马之人,我的飞红巾今天也是遇得伯乐,还求爷能许丹心千两黄金,给丹心阿娘治病!”
他长叹一声:“你娘得的是什么病,这般急切,竟要千两黄金?”
不说明真相,他们是不会信我的,我只得解释:“我娘中了醉仙毒,解毒需雪蛤,雪蛤需千金。”
“你与你娘从匈奴回来?”华衣男子疑惑。
“是,代郡被匈奴骑兵冲破,我一家被送至匈奴人家作苦役,受尽欺凌,落魄至此。”这是阿爹同我说的,我也一一言明。
“我有心买马。”那男子顿了顿,又语重心长地说,“完全是为你孝心感动,敢问可否让我见见你娘,也好让我这个买马之人辨明真相?”
“那我也要先见见你的黄金。”我不动声色望着他,十足做交易的派头。他被逗乐,对着我笑,“千两黄金我手头可拿不出,可这百两黄金断不会是假的。”
他一招呼,仆从拿出一匣金子,我一一验过,成色很足。我又望了望面前这位男子,还有那一大一小的两位公子哥,想着他们气度不凡,随行又能带这么多的金子,便也不再怀疑。
我只肯让这男子独自一人去我家中,大公子哥本是不肯,被做爹的勒令退下,只得悻悻退到一旁。及至家中,我开门喊阿娘,不见答应,又喊了声阿爹,也不见答应,便大胆地领着那男子进去。
“这是我阿娘。”阿娘身上盖着被子,双目紧闭,面色安详,鼻尖秀挺,比起阿爹,阿娘竟丝毫不见老态,只似睡着一般。
男子望着阿娘,面有异色,不自觉地伸手要去抚阿娘面容,被我察觉。我伸手拦住他,抢先质问:“你已经看到我阿娘了,我想我阿娘也是不希望被人打扰的,你若无异议,请将千金直接交由我,或者让我自己去取。”
“好小子,有胆有识。”我领着他出了门,他还在身后夸我,面上笑容和煦,“你多大年纪啊?生于何时?”
“乙酉年七夕之夜。”我冲口而出。
他略一沉思,“才十二岁,和我儿子一样大,英雄出少年。”
华衣男子直接带着我去了城郊一处宅院,令人取出千金与我,谈笑自若,“先帝时缇萦为救其父,愿入身为官婢,今又有丹心鬻马救母,如此种种,可见民知礼乐,教化纯善,大汉之幸,盛世之昌呀!”
我不顾他说的那些客套话,只顾拍拍我的飞红巾,对着它的耳根说:“飞红巾,以后你记得好好跟这大爷过日子,他是宽仁之人,必会善待你的。”
飞红巾对我眨眨眼睛,我心里酸酸的,一掌伸向飞红巾的头,将它推开,“好马儿,去吧!”
飞红巾绕着我打转,迟迟不愿走开,我狠狠心,扬起长鞭,狠狠抽它,“去吧!”
飞红巾长啸一声,蹄子高高扬起。华衣男子俊眉微蹙,接着便是哈哈一笑,“嘿嘿,好马儿!回你主人身边去吧!”
我抬眼,华衣男子笑意盈盈向我走来,“你叫丹心是吧!”
我点头应着:“刘丹心!”
刘是国姓,我说出自己姓“刘”,华衣大爷面露震惊之色,重新打量我。
“我看你和这马关系可不是一般的深,我怎好意思要呢!就当我做个人情,你拿这千两黄金去救你母亲吧!”男子见我被他看得有些不好意思,回神望着马儿,别有深意地对我说。
我的眼睛蓦地清亮,“谢谢爷,谢谢爷!”我跪下重重磕了三个响头,嘴里止不住地道谢。
“要谢就谢我儿吧,得以见你,还多亏他!”男子哈哈一笑,招呼站在一侧的白衣公子和锦衣小子过来,“是吧,荣儿,彘儿?”
“爹爹慈爱宽厚!”两兄弟一齐应道,那个叫彘儿的小子和我年纪相仿。
我牵着飞红巾,拿着凭空而来的千金,走得实在不踏实。我一转身,却见华衣男子依旧含笑看我,目光深沉。他见我回头,不禁疑问:“丹心,怎么不走,金子给少了?”
“不,够多了。”我眼中带泪,知道是他打趣,放低声音道,“飞红巾当留下,千两黄金,丹心受之有愧。”
“拿了你的马,比杀了你还严重!”华衣男子道。
“爹爹!”他怀里的彘儿开心地拊掌,“爹爹当带丹心回家,彘儿要人陪彘儿读书!”
“算这小子有福分。”白衣公子哥居然也为我说话,“若这孩子并非徒有其表,倒也是可造之材!”
我望着这两兄弟,一时接不上话。
“不若你卖身与我,作我家彘儿陪读,也好识几个字。”男子望望我,哈哈一笑,又点了点彘儿的鼻尖,“你小子,怕是要他来教你遛马吧!小小年纪,痴玩成这般!”
彘儿嘿嘿地笑了,对我露了个甜甜的笑容,我也对他嘿嘿笑。
阿爹说没钱送我去识字,阿娘说不要我学犁田要读书,我懂得阿爹阿娘的期许,可现在阿娘病得危急,我无奈摇了摇头,“丹心也盼着识字,可丹心当先征得阿爹阿娘同意,还要等阿娘把身子养好,方能去恩人那!”
华衣男子目光期许地望着我,“等你娘病好了,爹娘也答应,你就去都尉府找汲黯汲大人,说你叫刘丹心,他知道后会带你来见我的!”
我点头答应,目送三人离开。
怀抱着满满的金子,我心间惴惴不安又万分笃定——阿娘,你有药了,我们一家三口会长命百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