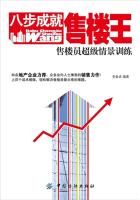“德古拉伯爵不喜欢阳光。”我烦躁的翻了个身。嗤拉一声,窗帘整个儿被拉开了。我暴躁的从床上弹起来:“神经病啊你!”
女人像没听见一样,继续伸胳膊扽腿儿,就跟我刚放了一个特没劲的屁一样。
“我说您能不能穿上衣服再挨那儿做体操?让外头的人看了三天吃不下饭去你说赖谁?”妈的,我这么多废话干吗,我就应该冲过去一把把她按在底下。人说女人刚起床的时候最丑,可是我发现眼前这女的,模样长得还真挺不赖,皮肤嫩得让人有想蹂躏的冲动。女人停下了,下巴微扬,睥睨我一眼,然后挑衅似的更玩命的做体操。于是我跳了过去,女人发出一声尖叫就被我给摁床上了。她发出杀猪一样的声音。我也只好配合情景需要做出杀猪一样的动作。我一只手摁着她,一只手在地上摸索。她的脚胡乱踹着,有几脚差点儿就招呼到我脸上。
我抓起地上扔得乱七八糟的衣服,然后跨到她腿上坐下,这下她踢不动了,两只手还被我摁着,只剩下嘴巴还有战斗能力,就大骂起来:臭流氓!有种别让我活着出去,出去就告你强奸!
我不搭理她,弯腰构了一只烟,点燃,悠哉游哉的吸。
开始她还不忿儿不忿儿的像蛇一样扭动,后来就躺那儿不动了。我把烟一掐,说:“对了,这才是合作的态度嘛。”说完开始把衣服一件一件往她身上套。结果她是老实了,就是我给她穿一件她往下扒一件,成心跟我对着干。
“我说你这女的怎么这么二啊?你再脱我可真强奸你啊!”这镜头弄得跟反强奸似的,谁看了谁不说百分之二百的色情啊!
“你当你昨天没强奸我是么?”一句话差点儿噎我一跟头。我一愣。彻底的愣了。这环境——好像来过这旅馆,这女人——路人甲还是路人乙啊?还有我这着装——跟刚出生似的一丝不挂……我在这儿干吗?答案似乎傻子都很清楚。
“昨儿……?”我玩命回想,可是脑袋就像被钝物撞击丧失了记忆一样,彻底空白伴随着玩命的疼痛。
“自己想去。”女人趁机一把推开我,爬起来迅速穿上了衣服。然后居高临下的俯视着我,跟女王对臣子说话似的:“记着,2005年5月8号,你强奸了我。刚才我用你的手机往我手机上拨了号,所以你手机号我已经记下了。甭想换号,你那身份证号码我也顺便记下了。我找你的时候,你就得出现,否则责任自付!”说完就拎起椅子上的背包,款款向门口扭去。
我晕,这是一女的么?简直一老妖!等等,5月8号……那这么说,今儿是9号了?9号……9号……我怎么觉着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来着?
我靠!大发了!我一拍脑门跳起来抓起地上的裤子穿上,袜子没穿直接踩上鞋就往外狂奔,一边奔一边穿衬衣。一出门没两步就跟一人撞上了,我说了一声妈的别挡道!然后脚步没停以加速度向前奔去。后面好像有个声音在嚷,说什么没听清楚。这时候我的脑袋里就跟让拖拉机轧过了似的,轰隆轰隆的就能听见一个声音:完菜了完菜了……
出门我一挥手截了辆出租,司机缓缓把车停下了,谨慎的看了我一眼,犹豫的问:“上哪儿?”我挺纳闷,看什么看,我脸上是开花了还是长草了?一上车我就摸兜准备提前把钱给了,这一摸,坏了:空的,上上下下摸遍了,兜里比脸上都干净。幸好手机还在,按了一通号码。“喂?棍儿?我!拿两千块钱到商务会所门口来!我钱包丢了!”“啥事这么急啊?房子烧了?我这儿还没起呢。”靠,这小子还有心情跟我开玩笑。“赶紧给我起来!我这儿急着呢!就是截辆警车你也赶紧给我过来!”可能听出我是真着急了吧,棍儿的声音利马严肃起来:“成!你等着!我这就过去!”哎,这就是哥们。挂了电话,我心里开始踏实了。脑子里一团线,跟被猫爪子挠过似的,乱七带八糟的。开始一根一根的捋,就从刚才那女的是谁开始,正捋着呢,司机师父说话了。
“您钱包丢啦?”边说边在反光镜里打量我。估计是在琢磨我是不是一坐霸王车的主儿。
“啊。一会儿有人送来,您就放心吧,少不了您一毛钱。”我接着捋,结果发现捋来捋去脑子里的线团跟被一群猫挠过似的,更乱了。干脆什么都不想的发呆。司机师傅从反光镜里看见我呆滞的表情,手一哆嗦,把车开得闷儿快,好像恨不得下一秒就一个刹车停在目的地。弄得我又挺纳闷:他不怕超速违规啊?到了商务会所门口,棍儿还没到。我说:“师傅您在这儿等会儿,我朋友这就到,我先进去看一眼。”
司机利马按住我肩膀:“别介啊兄弟,你说你要是一去不回了我找谁去啊。”然后特警惕的看着我,好像他是猫我是一耗子,他那爪子一松我就溜了一样。“成,那就等着呗!”我老实坐下,心里头念着棍儿啊亲爱的棍儿啊你赶紧来啊!会所门口满地都是花瓣和彩色的碎屑,可以想象刚才这里怎样的热闹过,一个庞大的红幅横在上面,上面贴在几个大字:XX和XXX结婚庆典。耀眼的颜色伴随耀眼的疼痛。可能是上帝听见了我的念叨,没两分钟就看一富康特完美的一个刹车横在前面。我激动的挣脱开司机的爪子蹿出车去。棍儿从车里下来,从兜里掏出一沓人民币递给我,盯着我看了两秒,说:“怎么这德了?被谁蹂躏了?就你这样儿还想进去哪?跟里头的人似的。”
我对着汽车玻璃一照,吓我这一跳,那脑袋跟颗大白菜似的,衬衫领子还窝在里面,这哪像里头的人啊,整个儿一个越狱犯!怪不得人司机没把我当好人呢。我发现那司机师傅死命的盯着我们看,就对棍儿说。“先把车钱结了去。”于是棍过去了。司机接过钱,谄媚的冲棍儿笑了笑,赶紧上车撒丫子把车开走了。我挨旁边偷笑。我说棍儿我要是一越狱的你丫就是一在逃的。棍儿额头上有一道斜疤,看着特像道儿上混的,他板脸的时候一般人甭说大气儿了就是小气儿也不敢出,也就我知道他那包子里头是什么陷儿。好人,大大的好人。棍儿说歇了吧你,忘了你干吗地的了吧?赶紧的,什么急事啊赶紧办了去!“对对对,正事没办呢。”可我怎么进去啊?这模样进去肯定因为仪容不整让人给轰出来啊。咋办呢?我琢磨着。有了!“来点儿零钱。”
两分钟后我拎着两瓶矿泉水一包口香糖回来。一瓶洗脸漱口一瓶打理头发,口香糖一气儿。扔嘴里玩命嚼,然后把棍儿的上衣扒了下来。在没有上策的时候下策只能充当选择。五分钟之后,我又人五人六的了。棍儿穿着我的衬衫,扯着皱皱巴巴的褶子说:“赶紧出来啊,这……我……也忒丢人了!”我说办完事马上出来,然后就阔步向会所里面走去。没人拦我,倒是一堆微笑砸上来差点儿把我给腻死。我在来宾签名册上签上自己的大名,后面写上两千。前面黑压压的一堆人名和数字,我觉着脑袋有点晕,可能那个红本喜庆得过于耀眼,耀眼得我有点儿恍惚,此时的感觉让我觉得特别陌生,从出生至今没有任何一种感觉能跟现在的重叠。不过现在不是胡想八想的时候。我礼貌的把签字笔还给礼仪小姐,冲她微了微笑,然后向主厅走去,不知道身后的礼仪小姐有没有被我二十瓦的电力电倒。
主厅里人头攒动,几十张桌子已经坐满,剩下的人用来填补空隙。往门口一站,我觉得自己整儿个一门神还不如那填空隙的呢,有人出进人家说句让让就得赶紧给人腾地儿。
最前面的她,变了,变得无与伦比的漂亮,这还不是主要的,她变得大方,成熟,多了很多说不出来的东西。难道婚姻给人带来的东西就这么与众不同?我没在这个问题上多做逗留,只是认真的看着她,看着从未如此美丽动人在我面前出现的她。一袭白色婚纱拖地,明眸浅笑动人,一张俏脸飞着霞红,分不清娇羞和粉黛。所有表情都在向在场的人宣布:我幸福得不能再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