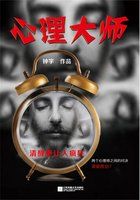“就决定压下来是吗?”刘国权的声音又高了八度。
“对,是这个意思。”
“死者家属见到过死者的尸体没?”
“没有,我们没安排见。不过……”翟建国说着又吞吞吐吐起来。
“不过什么?”
“出事那天,看守所外聘的一个临时工搬尸体的时候用自己手机偷拍了张照片,不知道怎么落到了死者哥哥的手里,我们发现后已经把那个临时工给辞退了。”
“瞧瞧,这就是你们干的事儿,还想压呢,连照片都漏出去了,你们还压个屁!”
刘国权彻底愤怒了,“我一会儿就去见杜书记,把这个事情汇报上去,看你们还怎么压!”
“您别呀!”翟建国终于也急了起来,“这个事情我们还是争取压在内部处理,这不才找您商量的嘛!您一下子给捅到市委杜书记那里,我们工作不是很被动吗?”
“那你们要我怎么处理?”拿着电话沉默了大约半分钟之后,刘国权终于说话了。
“您看能不能跟宣传部那边联系一下。”翟副局长的语调又重新压低下来,“那个死者家属不管告到哪里都无所谓,毕竟尸体已经火化了,他没什么证据。但是半路上突然冒出一个记者来,您也知道现在的媒体很多都不负责任,一旦报道了或是给捅到网络上去,不就麻烦了吗?”
“你们自己不会去找宣传部吗,找我干什么?”
“按照流程,这种突发的事件不都是先报到您这里吗?况且,您不是在宣传部当过一届副部长嘛,所以……嘿嘿,这才找您的嘛!”翟副局长的声音里开始有了一些暧昧的味道,“如果能把这件事情压住,我们高局的意思是一定重谢!”
刘国权思索了片刻,然后把声音也压低下来说:“你们高局呢?”
“高局现在在省里开年终会呢,他刚刚把电话打到我这里,让我和您说说。”
“他怎么不亲自和我说?”
“咳!您怎么忘了,前几天在年终行风评比的时候,您不是给我们高局一个黄牌嘛,弄得我们高局很没面子,那天和您闹得不是很不愉快嘛!所以出了这个事情,他不好意思和您直说。”
刘国权想了起来,就在一个多月前,H市的年终行业评议上,他确实给下面县里的公安局一张黄牌,作为应急办是有资格给所有曾经打过交道的部门打分的,不过那次黄牌确实没有冲着公安局局长高天书个人的意思,完全是因为他们公安局在过去一年里多次发生值班人员脱岗、主要领导联络不上的现象,这对应急办这种24小时在岗的部门来说是不能容忍的。那次评比会上,高天书由于脸上挂不住,确实和他争论过几句,不过很快就被人给劝开了。
“那好,我先和宣传部打个招呼,你转告高局长,工作是工作,不愉快是不愉快,我都忘记的事情,他还记得那么清楚干什么嘛!”
翟建国连声感谢着要挂断电话,被刘国权一声“喂”又给叫住了。
“你在哪里呢?”刘国权问。
“我?我在办公室呢。”
“那么好,从现在开始,你就带上相关的资料到我这里来,跟我一起办公吧,什么时间这事情处理完了,什么时间你再回去。”
“这个……”翟建国有些犹豫,不过马上就爽快地答应了下来,“好,我这就过去!”
“那个记者在哪里呢?叫什么来着?”
“叫江天养,《中国法制观察周报》的。他在哪里我也不清楚,中午他从服务区接走了死者的哥哥后,就上了高速公路,我们的人根本追不上他。”
“你刚才说你们看守所有个临时工曾经给过死者家属一张照片?”
“对!”
“那个临时工住哪里?”
“好像就住在看守所后面的那个岭南村,距离咱们市区40公里。”
“这样吧,你现在就带车过来,咱们先去岭南村。”
“您的意思是记者可能会去那里?”
“换成你是记者,面对这么一个连尸首都找不到的事情,你该去找谁调查呢?
死的已经不在了,当然是去找活的了。”
“对,对,对!我马上就过去接您!”
下了高速公路之后,江天养把车开到路边一个小饭馆里,时间已经快到下午三点,他的肚子已经开始叫了。
在小饭馆里,江天养叫了几个小菜,张玉林趁着江天养点菜的时候从内衣口袋里摸出了一张百元大钞,然后把钱攥在手里。江天养用余光看到了张玉林的动作,点完菜后他放下菜谱笑呵呵地看着张玉林:“你平时看新闻不?”
“不看!”张玉林摇了摇头。
“那么好,我来告诉你。”趁着没上菜,江天养点上了一根烟,“被指控为受贿的记者,其实他们可能什么都没拿人家的,更没花人家的钱,充其量也就是让新闻当事人给买了张车票,或者是请吃了一顿饭罢了,就都被当成了受贿行为,你说我能吃你花钱的饭吗?”
张玉林摇着脑袋说:“您吓唬我吧?哪能呢?您为我的事情大老远跑来了,还救了我,我怎么着也得请您吃顿饭啊!”
“我们这个行业怎么说呢,这么和你说吧!你认为我们记者是算公家人呢,还是算自由职业者呢?”看着张玉林没听明白,江天养只好再进一步解释,“你说我们算是国家干部呢,还是普通老百姓?”
“你们应该算是国家干部吧?”张玉林脱口而出。
“呵呵,其实我们对自己的身份也很模糊,只是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了。”
“这话怎么讲?”
“我们记者很多都是聘用制的,没有工作档案,一纸合同就能让我们当了记者,有朝一日合同到期或者是单位不想用我们了,就可以随时把我们开掉。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不算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国家干部。但是我们经常会因为批评一些地方的政府或职能部门而得罪人,那些被我们所批评的单位想从报道上反驳我们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只好利用我们的身份来找我们的毛病。”
“从身份上怎么找你们的毛病呢?”
“想报复我们的人往往首先会找到向我们提供线索的新闻当事人,利用各种办法或手段去问人家是否给了记者钱,哪怕是给记者买了车票或者是请吃了饭也都会被计算出准确的价格和金额。然后,他们就会让当地的司法机关以受贿罪的名义来追究我们的刑事责任,关的关,判的判!”
“但是你们都是聘用的,不是国家干部啊,你们怎么受贿啊?”
“在他们想报复我们的时候,我们记者的身份就都成了国家干部,而国家干部就可以犯受贿罪了。”
江天养看张玉林不相信,就打开了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打开了关于那几个记者的网页让张玉林自己看。
张玉林一字一句地看着那些关于记者受贿的报道,直到饭馆的伙计上了菜,他才抬起头来咂着嘴说:“你们这行这么严啊?不过今天这顿饭就咱们俩人,我花钱也没人知道。”
“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这句话用在我们身上正合适。何况你说就你知我知,不是还有天知地知嘛!你不正是因为相信很多事情都是天知地知才不会被永远地隐藏的嘛!”江天养拧灭了烟头,把方便筷子劈开,一指桌子上的菜,“吃!”
“是,是……”张玉林乖乖地把钱放回到了自己的口袋里,也跟着江天养大口地吃了起来。
“你那个老邻居家离这里不远了吧?”江天养一边嚼着菜,一边问道。
“不远了,翻过前面那道岭就到了。”
杨淼坐在西单购物中心一楼的星巴克里,一杯冒着袅袅蒸气的蓝山放在面前,旁边的座位上放着她亲手DIY的小背包。
以杨淼父母给她的生活费和她自己在纽约打工的收入,哪怕是一次性买齐所有LV限量版的手袋都不成问题,但她是个处世很低调的女孩,并且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简约生活倡导者,所以她很多的服装和手袋都是自己亲手制作的。在那些服装和手袋上,她会用手针绣出花体的两个字母——“Y&G”,那是她和江天养的姓氏第一个开头字母。
今天的杨淼,一席淡蓝色的套裙,一头柔顺的长发,怎么看都显得楚楚动人。
坐在临座的一对情侣中的男孩不时地用眼睛向她这边快速地扫描,惹得那男孩的女友在桌子下面不停地踢他。
星巴克的门被推开,白小宁一阵风似的冲了进来。同杨淼比起来,她的打扮简直就像个假小子。一件厚厚的羽绒服,一条紧身的牛仔裤,一双洗得有些泛起白边的运动鞋,再加上大得惊人的双肩背包,特别是理成只有几厘米长的头发,使很多人误以为她是“颓废一族”,但是不管她怎么颓废,还是难以掩饰青春在她身上雕琢出来的美貌。
看到了向她打招呼的杨淼,白小宁夸张地向杨淼挥了挥手,来到桌子边。先是把背包放下,然后再把羽绒服脱了下来,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上下打量了杨淼一番后,白小宁大声地说:“妞,穿得这么少,就算你不冷,也不该坐在这里被人吃豆腐啊!”
说完,她向窗外努了一下嘴,示意杨淼往外看。杨淼转过脸来看到落地玻璃窗外面,刚好有两个路过的大男孩正贪婪地边走边回头看着她那修长并且只穿着丝袜的腿。
杨淼非但没有把腿收回去,相反还故意向玻璃窗边靠了靠,看着渐行渐远的两个男孩不无感慨地问白小宁:“像他们这个年纪的时候,你敢保证你不偷看班上的帅哥?”
白小宁满不在乎地点了点头,随后向刚才一直在偷看杨淼的那个临座男孩抛了个媚眼:“那时候是偷看,现在是偷!”
那个一直三心二意看着这边的男孩接到白小宁向自己抛的媚眼,一时慌了手脚,先是往自己身后看看,确定白小宁不是在和别人打招呼,随后又用手指了指自己的鼻子,用目光向白小宁求证。这下那男孩的女友实在看不下去了,抄起一杯咖啡浇了男孩一头,随后起身摔门而去。那男孩尴尬地呆在那里,不知该如何是好。
白小宁用手一指女孩的背影,大声朝那个呆若木鸡的男孩说:“你丫还不快去追啊!”
看着那个男孩匆忙地结账后一路小跑地追了出去,两人一起哈哈大笑起来。
笑够了,杨淼看着白小宁那张没有化妆的脸,唏嘘地说道:“咱们这个年纪,也就只剩下勾引勾引小男生的本事了。”
“什么啊?”白小宁很不服气,“大小姐,咱们才三十啊!不老啊!没听人说嘛,女人三十的时候是玫瑰,最妖艳,也最具有杀伤力。论气质,我们已经完全可以不把那些十七八岁的小丫头放在眼里;论身材,我们这个年龄段最具有女人特有的成熟曲线;论阅历,那些臭男人就是搬座金山也休想再把我们勾引到床上;论品位,我们最懂得如何把自己包装得恰到好处……”
“你都穿成这样了,还叫懂得包装啊!”杨淼端起咖啡品了一口。
“这你不懂了吧?”白小宁故意做出一副妩媚的样子,“我这叫沦落美!”
杨淼嘴里的咖啡一点没剩,全部喷到了桌子上和桌子对面椅子的包上。
“嘿!大姐,我这包再不值钱也是阿迪达斯的啊!”白小宁一边用纸巾擦着包,一边又跟着杨淼笑了起来。
“这次回来能呆几天?”闹了半天,白小宁先恢复了正常。
“过完年就走,我买了十五的机票。”
“这么快啊!”
“是啊,那边的公司正在恢复期。你知道,金融危机对美国的经济打击很大,很多大公司都先是拼命地裁员,那些被裁美国人都将从公司得到一笔巨额补偿金,这使得公司损失惨重。等到经济开始恢复,这些大公司需要重新雇用新人时,就开始大量招募移民或是刚刚到美国的新人,因为这些人的薪金低廉,再次出现裁员时可以不必像第一轮裁员那样支付巨额的补偿金。我的工作就是这么来的,完全是钻了美国人的空子,我不能不珍惜!”
“你还缺美国人给你开的那点工资啊?”白小宁白了杨淼一眼,“凭你父母的财力,在美国给你开一家公司都没问题,干什么要去受那份洋罪?”
杨淼笑了笑没说话。
白小宁停顿了一下说:“美女,找我什么事?”
杨淼没有马上回答,她把白小宁的手抓过来,双眼盯着白小宁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小妖精,帮我做一件事!”
白小宁有点紧张,但是转瞬间就平静下来:“干嘛啊!大姐,不是要把我拐美国去卖了吧?”
杨淼没有笑,她严肃地继续一字一顿地说:“帮我想想办法,我想让他跟我一起走!”
白小宁安静下来,回望着杨淼:“你怎么认为我能帮上这个忙?那头猪死犟死犟的,你和他谈过吗?”
杨淼点点头说:“我和他说这个想法已经说了一年多了,但是他始终说考虑考虑。我一个人在那边,实在是不放心他……”
“不放心他?”白小宁重复了一句,“不放心他什么啊?你还怕他在国内再认识了其他女人?”
杨淼使劲地摇了摇头:“你知道,他做的工作都是一些冒险的事情,别看他不说,但是我从他采访后写出来的稿件里都可以看出来,他总是在面对着这样或是那样的危险,给我的感觉他不是一个记者,倒像是一个警察。”
白小宁默默地点着头:“你说的倒是事实,他那几个新闻奖都是冒着风险拿回来的,就好像他是一个天生的冒险家。也许男人都是这样的吧,喜欢刺激,喜欢冒险。”
杨淼的眼睛里开始有些湿润了:“好几次,我在噩梦里醒来,梦到他出事了。
赶紧一个电话打过去,直到听到他的声音我才放心。说实话,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我有点受够了。”
“他是什么意见?除了考虑考虑他还说了些别的什么?”白小宁问。
“他曾经和我说过,干到40,等他40岁干不动了就不再干了。但是他40,我就36了,还要我再等6年,我办不到,我宁愿现在就找个老外嫁了自己!”
白小宁把自己的手从杨淼的手中抽了出来,使劲儿地打了一下杨淼的手:
“呸!呸!呸!说什么呢你!”
“你知道,我父母是根本不同意我和他在一起,我和我父母抗争了八年。八年啊!抗日战争都结束了,我这才让我的父母可以接纳他。”杨淼感慨地说,“但是直到去年,我突然发现,我和他之间已经失去了刚开始时的那种感觉。每次通电话都像例行公事一样,问一下对方的时间,再问一下天气,然后问在干什么呢,接下来就是保重、照顾好自己什么的。像刚开始那时候,一个电话从纽约的黑夜打到北京的黎明的事情已经好久没再出现过了……”
杨淼到现在依旧清晰地记得刚刚和江天养相恋的那段日子。那时国内的网速出奇的慢,两人之间只能依靠越洋电话来沟通。曾经有过多次,午夜睡不着的杨淼打电话给正在中午的江天养,两人一聊就能聊上十五六个小时,一直聊到纽约天亮又天黑、北京天黑又天亮。
还有几次,杨淼按捺不住自己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买张机票偷偷地潜回北京,在江天养的家里小住上几天之后,再赶紧买张机票飞到加拿大或是地球上其他某个角落,然后再给父母打电话,撒谎说自己正在旅行,所以好几天没有联络。
看着杨淼眼睛里的泪水,白小宁不由得心头一酸,她转身从包里拿出纸巾递了过去,然后假装生气地说:“他敢?要是让我知道了他有另外的女人,看老娘我怎么砸断他第三条腿!”
一句话说完,四周座位的人都用一种惊奇的目光投向这里,白小宁一吐舌头,把脸转向了窗外。
“小宁,你听说过七年之痒吧?我和他八年了,我们是不是已经到七年之痒的时候了?说实话,我好怕!”杨淼说着,眼里腾起一层水雾。
白小宁瞪大了眼睛:“你说什么呢?人家七年之痒说的是那些结婚了天天生活在一起的,你们俩天各一方的,一年见不了几面,痒什么啊?我看充其量就是皮炎!”
说完后,两人都呵呵笑了半天。
“不过你放心,你的意思我明白,你是希望他能和你去美国,也省得你一个人孤单,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