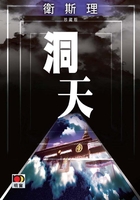突然,电话听筒里传来一声怒吼:“你们想逼死我啊?我不活了!”
紧接着,江天养看见就在服务区靠近洗手间一侧的一个电话亭边,几个男人正以半包围的形式围拢一个手拿电话的男子,包围圈越来越小,那男子正歇斯底里地冲着他们咆哮。
“妈的!”江天养情不自禁地咒骂了一句,一把挂上高速档位,车轮与地面摩擦出白烟的同时也发出了刺耳的噪声。
几个出来拦截的工作人员几乎就快要抓到张玉林的时候,他们同时听到了由远及近的发动机的声音和紧急刹车的声音,这使得他们惊呆在原地。一辆越野车飞一样地驶到电话亭边,副驾驶的车门砰地一下被打开,开车的中年男子冲着张玉林大喊了一声:“上车!”
张玉林最先缓过神来,一把丢掉电话,一个箭步冲上江天养的车,随后江天养加足油门向服务区的出口冲去。
一切就在几秒钟内完成,在场几乎所有的人都呆呆地站在那里,直到江天养的车驶上了高速公路,才有人回过神来,高声喊着:“赶紧开车追!”
另一个人无奈地回应着:“咱们这破面包车能追得上VVT涡轮增压的发动机吗?”
“那怎么办?那人是谁?”
“谁记下车号了吗?”
“我看到那车的前挡风玻璃上好像有个新闻采访的标志牌!”
“服务区有监控录像,赶紧去控制室……”
以160公里的速度开出大约20多分钟后,江天养往后视镜里看了半天确定没有人追上来,这才放慢了车速。
张玉林一直侧着身子向后张望着,从上车开始他的手就一直在颤抖。
“那些抓你的人都是谁?”江天养问道。
“有街道办和派出所的,还有几个我不认识,就是他们一直在监视着我。”
“怕你出来告状?”
“对,一旦我跑到省里或是北京,他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你怎么知道?”
“街道办的人告诉我的,他们求我千万别外出告状,要是我跑了,上面要追究他们责任的。”
江天养一边开车一边从口袋里拿出烟盒递到张玉林的面前,张玉林千恩万谢地从烟盒里拿出一支香烟,叼在嘴上后点燃,使劲儿地吸了一大口,这才长长地出了口气,情绪稍微平静下来。
“和我详细说说你弟弟的事情吧!”江天养把天窗开了一丝缝隙,在烟雾被猛烈的气流吸到车外的同时,一股寒冷的空气也充斥了车内。
张玉林的弟弟叫张金林,出生于1979年,中学毕业后没上高中,一直在家里务农。
张家老父亲在世的时候,家里还有十几亩旱田和六亩水田,虽然不多,但是让已经结婚的张玉林和尚未婚配的张金林兄弟衣食无忧还是绰绰有余的。
两年前,张家兄弟的耕地被乡里收了回去,不只他们一家,整个村子的耕地都被回收到乡里。两兄弟在拿到不足万元的补偿款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座现代化的工业园区在原本属于他们的耕地里像搭积木一样建设起来。
失去了土地的张玉林用多年的积蓄和那笔为数不多的补偿款在城关镇里购买了一个小院,随后他又借了一些钱给弟弟也购买了一处临街的平房,准备让弟弟就在那座房子中结婚,也算是完成了已经去世父母最大的心愿。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学徒后,张金林把自己的房子进行了简单的装修,开办了一个小小的家电维修铺,由于张金林为人勤奋,朴实本分,所以生意渐渐红火起来。
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张金林准备把小店整修一下扩大经营门面的时候,一张由乡政府和区动迁办联合签发的动迁令被贴到了他家对面的一堵墙上。
某个房地产开发商来到这里投资,而他看好的一片棚户区正好就包含了张金林的小店。这种事情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城市里屡见不鲜,但对于动迁办提出的每平方米500块钱的补偿方案,不止张金林,就连他周围的左邻右舍也都难以接受,毕竟这个补偿价格实在太低。
“我在给我弟弟买那套房子的时候,还是每平方米一千八买的,拆迁却只给五百,这还叫不叫人活了!”张玉林讲述到这里时,声音里充满了愤怒,“其实我打听了,开发商把补偿款定为每平米两千,但是余下那一千五百多被乡镇和区里以各种借口给克扣掉了……”
“你有证据吗?”江天养开着车,侧过脸来盯着张玉林,多年从业的经验告诉他,对于向他反映情况的当事人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必须得打个问号。
曾经有过一次,一伙失去土地的农民找到江天养的报社,告诉他自己的补偿款被政府给挪用。而当江天养找到那个地方的政府主管部门时,政府领导却一脸无奈地拿出有那些村民签字和朱红手印的领款单。原来,就是那些村民对于补偿金额不满意,所以才到处找媒体反映。那位领导告诉江天养,他已经是第六批被忽悠去的记者了。
“有!”张玉林没有丝毫犹豫,“乡里有一个干部就住在我弟弟家隔壁,他从单位复印出来开发商和乡镇签订的补偿方案,那上面有真实的数额,我弟弟就是因为看到这个材料才和来拆迁的人打起来的。”
三个多月前,动迁令上的最后期限到期。恰好就在那段日子里,外省发生了一名动迁户自焚死亡的惨剧,该事件的发生也促使多名专家学者建议国家修改拆迁条例,就在国务院开始进行调研时,一些基层的政府和开发商也加快了拆迁的进度,其目的就是要和国家即将出台的新拆迁条例抢时间。
当这些连宏观带微观的政策变化和专业术语从张玉林这样一个几乎没有受过什么高等教育的人嘴里说出来时,江天养丝毫没有感觉到惊奇。他知道,为了保护自己能够栖身的房产,已经有越来越多原本近似于法盲的人被逼成了法律专家。
张玉林想把抽剩下的烟头放在鞋底上拧灭,江天养打开了车窗,示意他把烟头直接丢出车外。
张玉林不好意思地讪笑一下,又接着开始回忆:“那天拆迁办动真格的了,开来了四台铲车,还有上百个穿着迷彩服头上戴着钢盔的人。”他的声音开始变得有些低沉,“我弟弟和动迁户里身强力壮的几个人站在第一排,不让铲车靠近,结果那些穿迷彩服的就动手打他们。混乱中也不知道谁打的,一个穿迷彩服的鼻子出血了,随后警察就来了……”
连同张金林在内的十几个动迁户被带到了派出所,就在他们被带走后,一整片的棚户区在铲车的轰鸣中成为了废墟。
当天晚上,其他十几个动手打架的当地人被家人保了回来,而由于张金林是后搬到这里的,加上张玉林手中一时拿不出钱来给那名被打伤的拆迁人员看病,所以张金林被关进了看守所。
几天后,张玉林拿着东拼西凑来的两千块钱到派出所给弟弟办理取保手续时,派出所的人才告诉他,张金林已经因扰乱公共秩序和轻微伤害被刑事拘留了。
在简单清理了弟弟被推倒的房子里的物品后,张玉林开始了艰难的诉讼之旅。
他先是找了一名法律工作者,向当地的公安局提出了诉讼,要求公安局立即释放他的弟弟。但是当地法院一听说是因为和拆迁的人打架被拘留的,压根就不给他立案。而那名法律工作者却不管这些,收到手里的两千元代理费一分钱也没退给张玉林。
随后,张玉林又代表弟弟向法院提起诉讼,控告开发商和动迁办野蛮拆迁。
这次法院干脆拿出了区里的一份文件,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由于动迁案件所涉及的问题众多,所以法院不得受理该类案件”。
就在此期间,不断有人给张玉林送信,给了他一个银行卡号和一个叫张大力的户名,让他去给他弟弟存一些钱,好让他弟弟在看守所里少遭一些罪,但是张玉林一时拿不出什么钱来,只能去看守所给存了一百块钱进去。
就在张玉林为弟弟的案件继续奔波的时候,也就是一个多月前,他接到了弟弟在看守所里死亡的噩耗。
“那天是派出所的和街道的人来送的信儿,我一听说当时就昏死过去。我就这么一个弟弟,老实、本分,连女人是个啥味儿都还不知道呢,就这么去了!”
说到这里,张玉林的眼泪落了下来。
江天养把储物箱打开,从里面拿出了一盒纸巾递给张玉林。张玉林伸手想拿,一看雪白的纸巾和自己那满是鼻涕和眼泪的手,不好意思地把手收了回去。
为了弄明白弟弟的死因,张玉林开始奔波于看守所、检察院和公安局之间,但是任他到处哭诉,哪怕是给人下跪,始终没有人告诉他张金林真正的死亡原因。
所有部门都几乎是统一了口径一样地告诉他:“急性心脏病发作死的!”
说到这里,张玉林近似于哀求一样地看着江天养说:“我敢对着太阳起誓,我弟弟绝对没有任何的毛病,他的身体壮得跟牛似的!”
“那就有人也敢对着太阳起誓,你弟弟绝对是死于心脏病!”江天养始终盯着前面的道路,“你说你弟弟不是心脏病死的,你有证据吗?你不一定有,但是人家可有,人家可以编造出一百份你弟弟有病的病历,毕竟你弟弟的尸体还在人家手里。”
江天养平日里什么书都看,甚至还看过一些关于中医的书籍。在中医的一些诊疗手段中,有一种方法就是先叫病人彻底的绝望,然后病人就会对医生的治疗言听计从,等于是把自己的生死完全托付给医生。
对于眼前的张玉林,江天养也想用这种方法,先是让张玉林彻底绝望,他才好完全按照自己的思路调查下去。否则,张玉林如果没有证据来佐证他的说法,那么江天养的这次H市之行恐怕就会无功而返。但是张玉林似乎并没有按照江天养的设计变得颓废下来,他使劲儿往衣服里面翻着,艰难地从最里侧的贴身内衣里拿出一个手机来,摆弄了半天后调出一张图片,递到江天养的面前说:“看了这个后,你还相信我弟弟是心脏病死的吗?”
手机里的图案是一具光着身子的尸体,整个尸体呈现出紫褐色,大大小小的伤疤遍布尸体的全身。在尸体一边,两名穿着白大褂的人正打开一个纸箱子,整个画面由于相素质量太低的缘故显得比较粗糙,颗粒也显得很大。
江天养接过手机,边开车边仔细地看着。良久之后他把手机还给了张玉林,问道:“照片上是你弟弟吗?”
“是的!”
“照片里的箱子是什么?”
“纸棺材,那两个穿白大褂的是收尸的。”
“你从哪里得到这张照片的?”
“我们原来村子里的一个邻居,地被占了后就通过关系到看守所里给人做饭打杂。这是他看到的我弟弟的尸体,就用他随身的手机拍摄的。”
“去哪里能找到你这个老邻居?”
“他已经被看守所给辞了,现在在哪儿我不清楚,不过我有他的电话号码,他好像就住在距离看守所不远的一个村子里。”
“那咱们就去找他,不过他为什么被辞了?”
“我这张照片是从他的手机里转过来的,我拿着这张照片到处告状,结果他们就知道了我手里有我弟弟尸体的照片,一追查就查到了,就把他辞了。”
“怎么能查到他呢?”
张玉林把手机再次递到了江天养的面前,这次江天养才看清,原来照片发送来源所显示的是一个手机的号码。
“你还会用彩信?”
“我哪里会?我是听我那个老邻居说完,又在他手机里看到照片后,才狠心买了个可以接收彩信的手机。”张玉林把手机里的照片发送到江天养的手机里之后,又把那个银行卡号也给了他,随后把手机小心翼翼地包好,重新放回到自己贴身内衣里。
“你是怎么找到你那个老邻居的?”
“我去看守所问我弟弟的死因,结果连门都进不去,我就在看守所门口扯出一条横幅,上面写着个大大的冤字,我就跪在那里,跪了整整两天。”张玉林的眼泪再次夺眶而出,“直到第二天天黑后,看守所的人都下了班,我那个老邻居才敢偷偷地走到我跟前,给我看了那张照片。他说收尸时他就在旁边,认出是我的弟弟,就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
“那他知道你弟弟是怎么死的吗?谁给打成这样的?”
“他说他只能在看守所的外围活动,监舍他进不去,所以太具体的不知道。
但是他告诉我,我弟弟死后,尸体是第二天抬到看守所外面的仓库里收殓的,还去了不少警察和当官的。他是被叫去帮着搬尸体来着,搬的时候才认出来是我弟弟。看守所里的人眼瞅着我弟弟满身的伤,却还非说是急性心脏病死的。他就让我出去上告,这天底下还是有说理的地方的。”
“对!这天底下还是有说理的地方的!”江天养点了点头,加了一脚油,提起了车速。
当张玉林被一个记者开车给劫走的消息传到刘国权的耳朵里时,他正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午睡,由于没人叫他,他一直睡到了下午两点半。桌子上的电话响了半天,他懒得接,直到自己的手机也响了起来,他才意识到可能是有急事。
来电话的是下面县里的公安局副局长翟建国,在电话里他简单地汇报了中午时在关外服务区事情发生的经过,当他汇报说张玉林是被一个来自北京的记者给劫走的时候,刘国权插话了。
“你怎么知道是北京的记者?”
“那台越野车前面放着新闻采访的牌子,并且弟兄们还记下了车辆牌照号码。”
“你们查了吗?”
“查了,我中午就叫咱们市里驻京办的人帮着查了一下。”
“什么结果?”
“驻京办的回信说那个牌照是登记在一个名叫江天养的人名下,是他的私家车。而这个江天养是《中国法制观察周报》的记者,我还在网络上搜了一下,找到了不少他写的文章。”
“该!”刘国权冲着电话吼了一声,“早就告诉过你们这些单位,一旦发生死亡的案件一定要先妥善安抚死者家属,防止发生不可预料的情况。你们也是满嘴答应着,说一定会处理好,处理好了怎么还弄出今天这一出?”
翟副局长一时语塞,拿着电话“这个……这个”了好半天。
“现在我问你,你给我说实话,那叫死者到底是怎么死的?”
“局里的调查报告上说是病死的。”翟副局长的声音开始小了下来。
“说实话,到底是怎么死的?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里和我忽悠!”
刘国权不耐烦了。
“打……打死的。”翟副局长终于在电话里吞吞吐吐地说。
刘国权考虑了半天,又问:“那看守所那边是怎么处理的?”
“县看守所拿了十万块钱,委托死者所在的街道和派出所给他的家属送去了。”
“我没问你钱,我问的是人怎么处理的?”
“人?”翟建国有些紧张,压低了声音说,“人,法医鉴定完之后人火化了。”
刘国权给气得直想摔手机,好容易压住火气才说:“听不明白我的话么?我问的是看守所里参与殴打的人怎么处理的?”
“哦,是这样,那小子所在的监舍被重新调整了,全部被分散开来关押到其他监舍里。其中有一个是判了一年刑留在看守所服刑的,已经到期了,出事没几天就放了。”
“管教呢?所领导呢?怎么处理的?”
“没……没处理。”电话里的声音更小了。
“为什么不处理?”刘国权终于压不住火了,对电话吼了起来,“对外可以糊弄人说是病死的,你们自己不知道人是怎么死的吗?为什么不处理责任人?”
“哦……是这样的。”翟副局长有些焦急,支支吾吾地说,“县看守所的高所长……”
“哪个高所长,说名字。”
“高天放,高所长。他是我们县局高局长的表哥,今年59了,一过完年就到点了……”
“什么到点不到点的?说清楚点。”
“就是一过完年就要退休了,如果这个事情被捅出来,不但不能正常退休,闹不好还要被追究责任。所以,局里的班子经过研究,就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