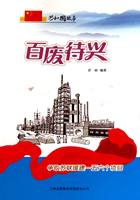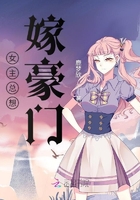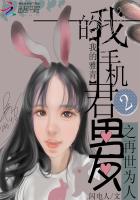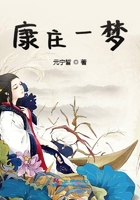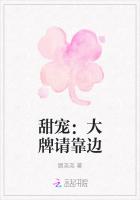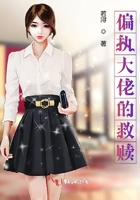在我的人民看来,这儿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神圣的。每一个山坡,每一条山谷,每一块平原和树林都由于一些在那早已消逝的岁月里的悲伤或愉快的事件,而变成了圣地。
——摘自美洲一位酋长的演说
1949年10月1日,一辆编号为“谢尔曼NO?237438W14”的美制坦克,隆隆驶过故宫门前,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分别乘坐小车跟在后面。他们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这年56岁的毛泽东用他的湖南腔普通话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整个天安门广场沸腾了。
同年12月,蒋介石怀着苦涩抑郁的心情,逃到了台湾岛。整整用了20多年的时间,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给蒋介石父子上了颇为沉痛而又刻骨铭心的一课,后来老蒋、特别是小蒋能够背靠美国,惨淡经营,着意发展经济,显然与败逃大陆的沉痛教训不无关系。
急风暴雨般的战争结束了。
从黄土高原、延安女大走来的女性们,一脸疲惫两肩征尘,有的身体里还带着弹片。她们分散在全国各地,大都脱下弹痕累累的军衣,换上工装或列宁服。透过袅袅飘散的硝烟,望着旭日初升的繁忙工地,这些饱经忧患、坚毅顽强的女性,脸上露出骄傲而欣悦的微笑。
中国女性的微笑有史以来第一次这样光芒四射!
中国女性有史以来第一次以群体形象,矗立于民族英雄的行列!
人民潮涌般在百业待兴的工地上集结。年轻的共和国渴望着,在新世纪的地平线上高昂起雄狮般的头颅。
而从延安走出来的革命女性是这个共和国的开拓者和中国新纪元的敲钟人,她们以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以自己的爱情、热血和眼泪,以“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巨大牺牲和“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英雄气概,挽着伤病累累的中华民族的臂膀,昂然走向新时代的大舞台。她们为中国在今天的和平崛起奠定了伟大的基石。
我们继续追寻着她们的足迹,那些沾着深厚黄土、灼热战尘的足迹,那些浸透热血和汗水的足迹。我们发现,延河水依然在她们的血脉中奔腾,延安魂依然在她们的胸中熊熊燃烧!
她们真是一代圣徒,一代无私奉献的民族斗士,一代彻底的理想主义者。我们想,无论在今后的任何时候,她们都应当是我们民族心中光芒四射的精神偶像,无论在今后任何时候,她们都不应当遭到哪怕是一丝一毫的亵渎!
陆红:不讲人道,还算什么共产党!
1946年冬,内战烈火已经燃遍全国,只有东北最远的重镇哈尔滨以及以它为中心的广大农村地区,由于蒋介石鞭长莫及,还处于共产党的掌握之下。
已近傍晚。东北大烟泡儿(暴风雪)刮得天地间一片白茫茫,坚硬的雪粒刮在脸上,像遭了猎枪的霰弹一样生疼。一个头戴狗皮帽子、身穿破旧的日本军用大衣的人影,正在茫茫雪野上艰难挣动,每走几步,身后的脚印就立刻被狂啸的暴风雪淹没。
不到近前看不出这是一个女人。
她就是陆红——延安女大学员,因在三八节集会中跳了个新鲜的瑶人舞而出了名。采访中,她笑着对我们说,假如没有革命没有延安,她今天可能就是个体态臃肿、手指套着金镏子的老太太吧。当初她跟着革命洪流进了延安,改名叫洪红。解放后,大陆山河一片红了,又改名叫陆红。
那个傍晚,她终于在风雪中挣扎着回到黑龙江依兰县城一间破旧的草房里,一屁股坐到火炉边的木墩上,摘下帽子,嘴里咝咝哈哈伸出双手烤火。没烤一会儿,又忙不迭地从炉灰里扒出几个烤土豆,狼吞虎咽地捧在手上啃,烫得直劲吸冷气。她饿坏了,这段时间她身子很弱,前几个月区里收缴流散在民间的枪,一个小战士不小心碰到一支枪的扳机,砰的一响,子弹从陆红小腹打进去,又从屁股打出来,差点儿一命归西。
没见过东北这么冷的天,像狗咬一样!她边吃边说。
今天转了几个屯子?土改队长王伯仁问。
两个,她说。动员老乡真是费劲,跟他们说共产党号召搞土改,给他们分田分地分财产,他们不敢要,说怕地主哪天打回来,要他们的脑袋。我说哪个地主敢回来反攻倒算,我们共产党就毙了他!
这时陆红的丈夫徐以新走进屋,他笑着插嘴说,这会儿你应当给老乡讲讲《共产党宣言)啊。
这是你干的事儿!陆红抢白他一句。三个人一起笑了。
徐以新(解放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少年时代投身革命,长征路上公开站出来反对张国焘韵分裂主义路线,被当作“反动分子”看押起来,其间两过雪山,三过草地。一次路遇敌人小股马队袭击,看押他的是刚参军的小农民兵,没打仗经验,一听枪响,吓得把枪丢了,一头钻进草丛里不敢动。徐以新抓起枪,眼珠子血红,和战友们迅疾投入战斗。马队被打跑了,那个农民听着没动静了,从草丛中钻出来,徐以新又恭恭敬敬地把枪交还给他说,咱俩以后就这样分工吧:你负责看管我,我负责打仗。
那小农民兵冷眼瞧瞧四周,小声说,再加上一条,我负责看管你,你负责教我打枪。
后来徐以新被派到苏联,学了一肚子马列理论和全套标准的交谊舞回来,在女大专讲《社会主义概论》,同时是业余的舞蹈教员。大家闺秀出身的陆红也是满场飞的舞蹈家,周末的联欢晚会上,两人搭伴跳舞,那潇洒妙曼的舞姿常引起满堂喝彩,两人后来就成了夫妻。陆红把徐以新管得很严,一天晚上,毛泽东和徐以新站在窑洞外面聊天,毛泽东顺手递给徐以新一支烟,说试试看,趁那位陆大小姐不在,做一回神仙罢。徐以新刚把烟点着,陆红不知从哪儿蹦出来的,上前一把把徐以新手里的烟抢下来,狠狠扔在地上踏灭。
毛泽东用手点点陆红,笑说:你真是匹野马!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向徐以新建议说,你已经是大秀才了,再到下边去增加些实践经验是很有益处的。于是,徐以新先行,已有两个孩子的陆红跟着别的队伍,两人在东北会合,徐以新当了依兰县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委,她则做了宣传部长。
吞下几个烤土豆,陆红的身子渐渐暖和过来,苍白的脸上也显出浅浅的润红。王伯仁郑重地说,陆红,我跟你说件事情。战后,依兰县有一批日本孤儿被扔下了,你愿不愿意收养一个女孩?
陆红知道,这些孩子来到中国或生在中国,都是日本侵吞和灭亡中国图谋中的一部分。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这个企图改变东北人种版图的图谋就开始实施。
1932年10月,第一批日本开拓团移民抵达佳木斯市。
1933年2月,第二批日本移民计493户到达桦川县。
1935年5月,日本拓务省制订“关于满洲农业移民的基本方案”,计划从1936年起,5年移民100万户,约500万人。其目的一方面是输出饥饿,减轻国内粮食供应压力,最终目标则是尽快使他们扶持起来的伪政权“满洲国”日本本土化。
1937年7月,第三批日本移民494户到达依兰县七虎力河右岸。以后每年都有大批移民运抵中国,安置在东北各地。
这批日本孤儿就是扎营在七虎力河畔的开拓团遣留下来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开拓团或者完全溃散,或者集体逃亡,或者集体自杀,大批日本孩子被父母扔下不管了。如何安置好这些日本遗孤的生活,成为刚刚成立的黑龙江省各县中共基层政权的一大难题。他们广泛动员党的干部们带头收养这些孩子。
陆红点头了。
王伯仁把片冈弘子带到陆红家。弘子那年14岁,圆圆的脸蛋,长得很壮实,穿一件更生布长衫,怯生生站在门边不敢动。天很冷,再加上有些紧张,她的嘴唇直抖。
炕烧得热热的,屋里弥漫着柴草的潮湿昧和玉米面粥的香味。
来,过来吃饭吧。陆红和颜悦色地招呼弘子,让她脱鞋上炕,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坐到矮矮的炕桌边。要是在日本投降以前,要是在自己家,弘子会大为惊讶的。在日本,在自己家,女人是不能与男人同桌吃饭的。而且她在开拓团小学读书时,听日本老师讲过中国“红胡子”(指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是怎样的凶恶,怎样的“青面獠牙”、“共产共妻”,见了日本小孩就杀。她也知道因为这场战争,中国和日本之间有着多么深的积怨和仇恨。抗战刚结束时,没有生活出路的她跑到当地一个地主家当女佣,听说八路要来了,弘子恐惧已极,不知会遭到怎样的毒打和蹂躏。没想到八路军来了,斗倒地主,反而把她解放出来,让她跟着工作队里当翻译。在朝夕相处的日日夜夜里,她发现八路军是一群大好人。这会儿,她又和“红胡子”县委书记的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了。弘子与陆红4岁多的大孩子一样待遇:每人一碗热气腾腾的玉米面粥,一个玉米面饼子。
陆红怀里抱着的小孩子刚1岁多,吃的也是玉米面粥。
吃吧吃吧,不够还有,把肚皮吃得圆圆的,陆红亲热地说。
片冈弘子跪坐在炕桌前,以日本人的习惯不住地向徐以新和陆红鞠躬。自“八一五”以后,这是她第一次浸润在如此温馨的家庭氛围之中。饭后,陆红一边给弘子缝补衣服。一边跟她聊天。弘子用流利的中国话说,她是9岁那年随家人来到中国的,父母都是地道的日本农民,在开拓团里生活很苦,母亲冻死了,父亲患伤寒病死了。两个哥哥刚成年就被关东军拉去当兵,至今生死不明。弟弟片冈彰夫流落乡间,以打短工维持生计,还有一个妹妹当了人家的童养媳。开拓团里的一些亲友,有的逃亡,有的自杀。弘子在一个地主家帮着干家务看孩子。直到八路军工作队来了,斗倒了地主,她被解放出来,可又无家可归了,幸亏工作组收留了她,她才有今天。
90年代初,笔者曾写过一篇有关日本遗孤的纪实文章。据了解,“八一五”日本投降之夜以及后来的两三天里,遍布东北偏僻乡村的日本移民,大多还不知道天皇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各地开拓团头头接到上级密令,以“效忠天皇”为名,立即开始了对本国移民的大屠杀。在东三省各地,开拓团以“联欢”、“庆祝”等各种名目,把一家家移民集合到一间大房子里。杯觥交错、欢歌笑语之间,或者引爆早已埋在地下的炸药,或者在酒菜里放毒,或者突然宣布日本已经投降的消息,威逼着要大家切腹自杀,数十万计的日本移民就这样在一夜之间死于非命,尸横遍野。
这是一桩尚未了结的公案。
对死于这场大屠杀的移民人数,中国方面没有做过统计,日本方面则对死因讳莫如深。一些官方资料及立在日本各地的死难者纪念碑,大都对死亡人数、包括每人的姓名做了详实登记,对死因则都含糊其辞地说这些人“殉难”于对华战争。直至现在,日本的年轻人很少知道,残害这些同胞的凶手与杀害数千万中国人的凶手是同一伙,是东条英机、冈村宁次这伙灭绝人性的日本战犯。而他们罪恶的灵位至今还供奉在日本靖国神社里,以供那些歪曲和无视历史真相的政客和军国主义余孽们瞻仰。
大屠杀之后,数以万计死里逃生、没有了爹娘的日本孩子遗留在中国大地上,成了孤儿……
自此,片冈弘子成了徐以新和陆红一家的成员,并跟他们一起享受供给制。吃得饱,穿得暖,日子过得比开拓团还滋润。弘子内心的创痛渐渐平复,而且有了舒心的笑。白天,陆红出去忙工作,弘子就帮她照料两个孩子。晚间稍有闲暇,陆红便教她读书写字,每天要求她学会8个汉字……
两年后,徐以新调佳木斯市任市委书记。家里忙着打点行装的时候,弘子心慌了,怕把她扔下。陆红笑着说:傻丫头,我们怎么能丢下你不管呢,以后你就当我妹妹吧,我叫陆红,你就叫陆霞,咱们就是亲姐妹了。
弘子紧紧抱住陆红,泪水滚滚而下。
在佳木斯,陆红把孩子送进托儿所,以便让片冈弘子进学校学习文化。五十年代徐以新和陆红调入北京,陆红又安排弘子进入工农速成中学学习。在那里,陆霞以一片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激和爱戴之心,先后加入共青团和党组织,后考入中国地质学院,毕业后分配到甘肃地质部门工作,并有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小家庭。
“文革”时,陆霞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偌大的中国几乎没有她可以安身立命的一块净土。中日建交后,1979年,得知早期返国的弟弟片冈彰夫已在日本成就了一番事业,陆霞和丈夫决定带着3个孩子返回日本定居。临行那天,对于家国亲人的思念,对第二故乡中国和中国姐姐陆红的依依惜别之情,像漩涡一样翻卷在心头,弘子是哭着登上飞机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听说中国开始大力纠正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并步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一直念念不忘徐以新和陆红养育之恩的陆霞毅然决定重返中国,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出力。弟弟片冈彰夫少年时饱经忧患,回国后靠卖血发愤读书,终成大业。他得知徐以新和陆红几十年如一日照料和培养弘子的事情后,深为感动。他说,当年日本把那么深重的灾难带给中国,没想到中国共产党人能如此人道地对待他的姐姐,真是恩重如山啊!
陆霞对我们说,她一家及所有日本亲友都深深地感念徐以新和陆红的养育之恩。徐以新和陆红不仅把她培育成一个对社会和大众有用的人,而且在几十年的共同生活里,他们还自身的高风亮节教会她应当如何做人,她虽然称陆红为“姐姐”,但在心目中,她一向把陆红视为自己最亲爱的慈母。
陆霞激动地说,她是从这两位老共产党人的身上,认识到中国的伟大的。后来弘子在日本的亲友们怎么感谢徐老和陆大姐,他们都坚辞不受。1980年,片冈彰夫见徐以新一家还在看一台小黑白电视,便送老两口一台彩色电视,可陆大姐转手就把彩电送给外交部幼儿园了。那以后,我们就把对徐、陆两口子的感激之情,转化为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支持。弟弟片冈彰夫尽自己一切所能,还带动了不少亲友,帮助中国发展经济。在北京、陕西、福建、四川及深圳等地,都有他的投资。他是新时期最早进入中国的日商之一。
1994年12月30日,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徐以新溘然长逝,享年83岁。片冈彰夫代表全家拍来一封长长的唁电,电文中说:“徐以新是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杰出的国际主义、人道主义战士。本人及家人深受先生的恩惠,忆昔日慈父恩师般的抚育、教诲,至今历历在目,终生不忘……”后来片冈彰夫专程来到陆红家,与陆霞等含泪肃立在徐以新遗像前,双手合十,深深鞠躬,以表哀思,并祝愿日中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李文放:痴女与奇书
1947年春,悄悄来到全国第一个解放的大城市哈尔滨。
道里区有名的大市场“八杂市儿”里,人来人往,摩肩擦踵,高高低低的叫卖声响成一片。在这里,柴米油盐酱醋茶,乃至东南西北中的小百货、五行八作的日用品,一应俱全,琳琅满目。现在它已经消失了,变成正儿八经的大百货商店和油光水滑的菜市场,可老哈尔滨人谈起那个品类丰富、价格低廉的“八杂市儿”,还是很有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