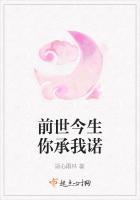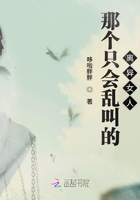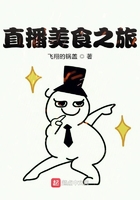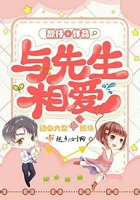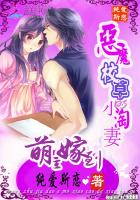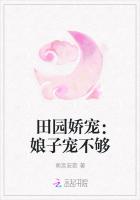刘涑自抗大女生队毕业后,在山西省灵丘县开展敌后斗争,任县妇救会主任。有一天,武工队获得消息,日伪军马上要来驻地清剿,路程只隔两个村庄了,必须马上转移。当武工队员们把群众扶老携幼地带到山林中时,一位村妇发现自己的6岁女儿喜兰子没有跟上队伍,顿时急得哭了起来。刘涑说,二嫂不要着急,我回去给你找。
乡亲们一听都吓坏了,说不能去,太危险了,说不定鬼子这时候已经进村了。刘涑说,孩子太小,绝不能让她落在鬼子手里!说着,她在腰间系了一条麻绳,匆匆跑下山去。
进了村,刘涑直奔二嫂家,没有!
转来转去,终于在路边草堆处发现已经睡着的喜兰子,脏兮兮的小脸上全是泪水,显然她因为找不见妈妈,哭着哭着睡着了。这时村里狗叫声响成一片,看样子鬼子已经进村了,刘涑背起喜兰子就跑,可身后一片杂乱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当她气喘吁吁、慌里慌张背着孩子刚刚跑进山林里时,被一群虎狼般的日伪军追上了。
“八格牙路,小小的女子,这样的快跑!”十几把枪口和刺刀齐刷刷把刘涑围了起来,“说,往哪里跑?”
这时刘涑反而沉静下来,她放下背上的喜兰子,擦擦额角的汗水,把孩子护在膝前,低首不语。
“快说,不说死了死了的有!”一个鬼子逼上前,啪地一个重重的耳光扇过来,刘涑踉跄了几步,又站稳了。喜兰子吓得哇哇哭起来。
刘涑对孩子说:“喜兰子,不要哭!他们是坏人,日本鬼子,专门杀人放火,欺负咱们中国人!”
鬼子听出一点意思,狞笑着说:“你的大大的坏了,你向小孩子说皇军的坏话是不是?”他下令要几个伪军上前把刘涑绑到树上,轮番用皮带抽她,抽一阵就追问:“八路在哪里?你往哪里跑?”
刘涑咬紧牙关,一声不吭。狂舞的皮带中,衣服破碎了,露出的肌肤鲜血淋漓。一直在一旁悲哭的喜兰子突然疯了一样扑上来抱住刘涑的腿,哭喊着“不打姑姑!不打姑姑!”
噗地,一个鬼子把刺刀直捅进喜兰子后背,然后猛力一挑,把喜兰子挑飞到一旁,孩子大叫一声,在地上打了几个滚儿,死了。
愤怒的刘涑大喊:“你们这帮狗强盗,杀人的豺狼!血债一定要你们的血来还!”
鬼子的几把刺刀同时深深捅进刘涑的胸膛!
刘涑最后留给历史的不是歌声,而是一声怒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她的生命终止在19岁。她永远是19岁。
墓碑与基石
我们无法一一细述延安女大的战士们在战争年代的悲壮经历。牺牲了的,每座墓碑下都是一部史诗。活着的,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共和国的基石。
去延安前,在北平、天津把日本人炸得人仰马翻的蒙古族姑娘乌兰,像海鸥一样渴望着暴风雨中的飞翔。女大毕业后,她找到张闻天,坚决要求回到大草原参加抗战。在那里,她成了一个贵族家的牧羊女,白天赶着羊群,嘹亮而悲壮的歌声响彻天地。夜晚,贵族家安睡了。乌兰作为秘密交通员,悄悄跨上骏马,飞驰于风暴雪狂的草原,为地下党组织递送情报。不久,通过地下党员克力更(后成为她的终生伴侣)的关系,她又打入国民党新编第三师,在师政治部代主任云时雨(即乌兰夫)的领导下做宣传工作。新三师虽然是国民党的武装,但实际在中国共产党的掌握之中。他们到处建农救会、妇女会,组织民兵武装,使整个鄂尔多斯草原呈现出一片团结抗日的兴旺景象。
蒋介石对此早有察觉,严令新三师调往甘肃整训,并密嘱师长白海峰寻机把云时雨等共党分子秘密处决。形势危急,中共中央决定,所有身份已经暴露的共产党员立即撤离,乌兰与克力更结伴回到延安。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9月,乌兰把不足两岁的儿子阿斯楞交给延安第二保育院,再返热辽地区前线,出任内蒙人民自卫军第十一支队政委。这支骑兵队伍纵横驰骋于广阔的草原山野,乌兰作为我军第一个女骑兵政委,双手打枪,能征惯战,时而一身戎装,时而身着飘飞的蒙古族长袍,特别在腾格里营子一战中,她率队生擒罪大恶极的匪首“小白龙”,“双枪红司令”的名声在内蒙大地广为传播。
不过,不要以为乌兰是一个粗野的“赳赳武夫”式的女性。克力更对我们谈起妻子时,一往情深。他说,实际上乌兰是非常温柔的女性,她平时说话声音轻柔细慢,走路步履轻捷,上身不动,只是双脚迅速移动,像一阵轻风从湖面掠过。她特别爱美,战争年代无论怎样艰难紧张,她一直保留并十分爱惜那根乌黑油亮的大辫子。哪怕突然奉命出征,她纵身上马,双腿夹住马肚子,任马如飞奔驰,她却能稳稳端坐马背,两手麻利地编好辫子。延安女性留辫子的不多,刚入女大时,同学们批评乌兰留辫子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你说你的,乌兰照样留着,干起活来把辫子往头上一盘,样样抢在头里,时间长了,大家也就不说什么了。
乌兰爱起来也是如火如荼,柔情绻缱。延安的夜晚,吕璜和同学们出来巡夜,常见乌兰和克力更坐在延安河边上紧紧拥抱接吻,直至深夜。她们有些看不惯,背后悄悄说,同学中那么多谈恋爱的,顶数乌兰最粘乎。可在克力更眼里,乌兰是最甜美、最可爱的姑娘了。
陶端予(生前为教育部初等教育司司长)自女大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宣传部当机要秘书。1943年冬。22岁的陶端予向支部书记王若飞提出,想到乡下去做些实际工作,她自愿来到延安北郊的杨家湾,一个人白手起家,为贫苦农民创办起第一所小学。
农民不放娃出来念书,她就挨家挨户帮着修纺车。感情近了,农民把她当自家人,娃们就放心地交给她了。没有教材,她就自编自写,都是农民生活中有用的知识。她还编了许多歌谣,几十年后学生们还记得。没有经费,她就下地种田,卖了收获也就有了经费。她还带领孩子在全村大搞卫生,教老乡多洗澡,教老太太捉了虱子不要放在嘴里吃。杨家湾大变样了。她的办学经验被总结出来,毛泽东兴奋地批示给《新华日报》:“全文发表,一个字也不要改。”
陶端予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的特等劳模。她惶惑地说,抗战前线的将士们流血牺牲,我在后方做的这些算什么呀。
40年后,当了教育部司长的陶端予重访杨家湾小学,据《延安报》报道,那里的老乡亲见她如见亲人,啊呀,那个激动人心的场面,简直令人无法用语言形容。
老太太杨桂香迎上去,两人搂抱在一起泣不成声。杨桂香说,你怎么一走就再也不回来了,可把我想坏了!
陶端予擦着眼泪说,那年你送我走时,编了一个歌,边走边哭边唱,“杨家湾向阳川,来着容易走着难……”现在我还记着哩。
另一位老太太说,那年你走,我还编了个信天游,“崖畔上开花不扎人,什么人留下个人想人?”你记着吗?
陶端予说,记得,记得!
那时的青春和生命像火焰一样炽烈,像水晶一样透明,中国共产党同人民群众有着鱼水般的亲情,老百姓记得,老共产党人也记得。
邓寿雨(原为冶金部钢铁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容貌端庄,谈吐文雅,年轻时是个很秀气的姑娘。父亲是热血汉子,曾与汪精卫一起谋划行刺摄政王,事败后他潜逃家乡福州,后来到国民党南京政府海军部混了一个上尉文职。邓寿雨生在北京,现在还是一口标准的北京腔。
“七七”事变后,海军部撤到湖南岳阳,时为中学生的邓寿雨跟着父亲到了岳阳。抗日救亡大潮中,她急了,向父亲大喊,小日本打咱们中国,海军不下海,怎么还跑到山上来了!
父亲一脸的无奈,只有长叹。邓寿雨像一团烈火般投入街头救亡宣传活动,可国民党县党部又限制她们。年少气盛的邓寿雨火了,不干了,找八路军抗日去!
1938年夏,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邓寿雨跟家里谎称到“西北联大”念书去,便坐上一条帆船出发了。海军部里一个青年职员叫何玳,长邓寿雨6岁,常跟邓寿雨一起演剧搞宣传,这次也跟着走了。船刚离岸,17岁的邓寿雨突然呜呜哭起来。何玳问她怎么了?她就是哭,不说。同行人都以为她舍不得离开父母,其实是邓寿雨忽然想到,何玳和她一起失踪,家里家外会以为她和何玳私奔了,那名声多不好啊。
这个何玳后来果然爱上她,不屈不挠地追了她好多年。在邓寿雨与丈夫姚少诗(生前为冶金部教育司司长)已经有了恋爱关系以后,何玳还是恋恋不舍,又写信又送日记。邓寿雨只好写信给他说,她的态度和决定是不能改变的。何玳痛苦不堪,把邓寿雨的照片撕得粉碎寄还给她。后来何玳跟着四野,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最后牺牲于抗美援朝前线。作为曾经同甘共苦的战友,邓寿雨很怀念他。50年代末,邓寿雨利用公出机会,专门到沈阳烈士灵堂寻找何玳的骨灰,以寄托哀思,可惜没找到。面对蓝天大地苍松翠柏,忆起当年纯洁而真挚的战友情谊,邓寿雨怆然泪下。
解放战争时期,邓寿雨到了东北。四平保卫战枪声甫落,陶铸便带着秘书姚少诗、邓寿雨等十几人开进去接收。战斗打得十分残酷,满城废墟,遍地血迹斑斑的尸体都是一丝不挂,衣服都被饥寒交迫的老百姓扒光了,邓寿雨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如此惨不忍睹的景象。1947年秋,她到黑龙江省依安县任郊区区委书记兼区长。回忆起这段生活,邓寿雨说,旧社会的贫富差异令人无法想象,贫苦农民家的大姑娘穿不上裤子,可东北的地主真是有钱啊。大概也就因为这个,加上土改初期我们的政策比较左,东北穷苦百姓斗起地主来特别激烈,吊起来打的,点天灯烧死的,逼得一些地主富农,甚至还有中农跳河跳井和上吊自杀了。
在依安县有个土地主,攒了一辈子钱,不买官,不搞工商业,收了钱就埋到地下。开始农会不讲政策,又打又斗,还把猫塞进他的裤档里抓咬。邓寿雨发现了此事,坚决加以制止。过后深入到地主家的长工中间做工作,打消他们怕地主秋后算帐的顾虑。最后,在长工的帮助下,终于在地主家一间破仓房的地底下,挖出整整三大缸银元和三百多根金条,围观的人眼睛都花了。那天晚上非常紧张,为避免老百姓一哄而上,把钱财抢了,邓寿雨把县大队调来负责安全。起出浮财后,立即让县银行接收。斗了地主老财,接着就给老百姓开仓放粮,分田分地分骡子分马,老百姓跳着脚喊“共产党万岁”!
后来,邓寿雨又南下辽西当区长,当地有个远近闻名的女土匪头子,绰号“花蝴蝶”,头发梳成许多小辫,再盘在头顶上。她能双手使枪,百发百中,侧身骑马,奔跑时能在马上滚下翻上。她的势力也很大,有机枪、迫击炮,还有十几辆胶皮轱辘健马大车。不知为什么她特别恨男人,贴身护卫都是女匪,男匪只能干些粗拉活儿。听说县里来了个共党女区长,“花蝴蝶”很不服气,还叫号要和邓寿雨“会会”。可惜邓寿雨不久就南下了,没与这个“花蝴蝶”交上手。一年以后“花蝴蝶”被剿灭。
孟于记得,女大毕业后,她参加了华北文工团,赴前线演出《白毛女》时,每天晚上演出两场,给战士带来极大激励。演员们晚上坚持演戏,白天就上炮火连天的战场帮助抢运伤员。孟于亲眼看到,为了防弹,攻城的战士顶着桌子,桌子上绑着三四层棉被,用水浇透,就这样呐喊着往上冲。孟于蹲在战壕里看着,眼泪哗哗往下淌。一场战斗打下来,百十人的连队只剩下30几人。
孟于说,战场上流血牺牲是大量的,活下来的英雄是极少数,因此在后来的历程中,她常常想,自己能活下来,命就是白拣的,是从烈士堆里爬出来的,工作时就总有一股不要命的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