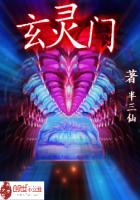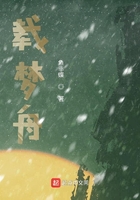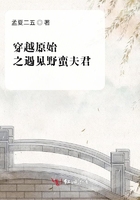灾难还是降临了。1930年6月的一天,突然从南面山岗冲来黑压压的一帮民团,随着杂乱的枪声,他们冲进村来,到处烧杀抢夺。廖冰的父亲出来阻拦,一个兵痞抡起枪托把他从桥上打落水中,小廖冰尖叫一声,和哥嫂跳到水中去救父亲。接着,廖家的中药铺被点燃了,母亲和邻居们慌乱而徒劳地用瓢舀水救火,药铺还是在烈焰中轰然倒塌了。兵荒马乱,豺狼横行,生活没了着落,13岁的廖冰怀着满腔仇恨,跟着父亲和三哥逃难到新加坡,在码头上与先前逃到这里的大哥相见,一家人百感交集,潸然泪下。
20世纪30年代,新加坡还是英国的殖民地,那里居住着很多华侨,他们的子弟大多被送到侨民学校学习,廖冰也在那里就读。虽然身在异国,但故土的风雨变故无时无刻不牵动着她的心。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廖冰和广大华侨青年走上街头,高喊口号,反对日本的侵华恶行,并募集捐款来赈济祖国东北难民。但英国当局却出动军警大肆抓捕上街游行示威的学生,小学没毕业的廖冰也被关了一些日子。
不久,大哥给她订了一门亲事,那是一个家资佢万的富贵人家,婆家见廖冰娇小玲珑、温文尔雅的样子,很是喜欢,答应先供她上学,中学毕业后再成婚,然后再送她去英国留学……可这不是廖冰想要的生活啊!心怀国难家仇的她不甘心像木偶一样被别人牵着走,考入新加坡南洋女子中学以后,廖冰终日苦苦思索,希望能找到一条求妇女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光明之路。自己的一方天地。随着豆蔻年华的到来,快要毕业的廖冰已出落得清秀端庄,气质优雅。但婚期也一天天地逼近了,怎么办?就这样结婚,做一个甘于平庸生活的贤妻良母吗……她辗转反侧,久久难以入眠。
最后,她终下决心——逃婚!
中学毕业后,廖冰借回国看望父母之机,偷偷跑到厦门,在一位许姓同学的帮助下进入一所机绣学校学习。但是,婚约还没解除,这件事一直是廖冰的心病,思考再三,她决定重返新加坡,豁出去,做一场反对封建、解除婚约的斗争。那些日子,她又是绝食又是上吊,经过好多次坚决的抗争直至走上法庭,婆家人终同意解除婚约解除,并登报声明。
一直压在廖冰心头的桎梏终于打碎了,她像挣脱出樊笼的小鸟,开始了自由的飞翔。1936年秋,19岁的廖冰来到马来亚,在一所学校教书。业余时间,她常在报刊上发表一些散文杂文,谈国难家仇、妇女解放、封建压迫等一些时政问题,由此与《中华晨报》的总编辑王炎之成了好朋友,后来她参加了马来亚文化协会工作并当选为妇女部长。在马来亚文化协会,廖冰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如《西行漫记》、《两万五千里长征记》等等,由此她知道了共产党、毛泽东,知道了工农红军和红色延安……她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我一定要去延安,去革命,去抗日!很快,她与一批也想奔赴延安参加抗战的华侨青年集结起来了。消息传开,社会各界群情振奋,为这批抗日青年捐献了大批金钱物资,有侨胞向廖冰赠诗云:“翘首望中原,敌忾重如山。杀敌酬壮志,誓让木兰先。”
行期将近,曾经计划同行的几位热血青年,在热血冷却之后,或因家庭阻拦,或因爱人难舍,或怕不习惯北方水土等种种原因,都声言“暂时不走了”,最后只剩下一个廖冰。一个女孩要远涉重洋回国参加抗战,该是怎样的艰难和危险啊,但她抱定“壮士一去不复还”的誓死决心,毅然登船启程。临行前,王炎之交给她三封介绍信,分别写给香港办事处的廖承志以及延安的陈伯达和艾思奇。
别了,南洋!当轮船离开新加坡码头时,廖冰举目眺望,感慨万千。这里有自己多少难忘的记忆,而今日一去,路途迢迢,万水千山,等待自己的又将是什么?身后海浪滔滔,前方烟波浩浩,廖冰心潮起伏,热泪滚滚,她心中不禁吟起那首《告别南洋》:“再会吧,南洋!你海波绿,海云长,你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我们民族的血汗,洒遍了这几百个荒凉的岛上……”
7月间,下旬,廖冰经由香港、广州乘车北上。当时武汉告急,“保卫大武汉”的标语到处可见,火车的各个车厢乃至过道、洗漱间都挤满了人,还有很多奉命北上保卫武汉的士兵。车上的气氛很紧张,仿佛战争的气息已经渗入了每个人的神经,廖冰也不由得担心自己一人独行北上,究竟能否安全到达延安。正想着,突然刺耳的警报声响了起来,火车猛然刹住,惊慌的人们高喊,快跑啊!小鬼子扔炸弹啦!叫声、骂声、哭喊声和警报声冲撞着人们的耳膜,旅客们慌乱地跳出车厢,横七竖八地卧倒在铁路两边的稻田里,惊恐地看着天上盘旋的飞机。就这样,一路上炸炸停停,到处都是尸体,血淋淋的现实不仅没有使廖冰望而却步,反而更加坚定了她慷慨赴难的决心。
车行路上,廖冰发现自己座位的前后左右坐着好些年轻人,他们三五成群,窃窃私语,还不时地打量着自己。
突然,一个人走过来问,您去哪里?
廖冰心里有些忐忑地说,去西安。
干什么去?
廖冰说,去永安堂。这是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特意交待的,从新加坡回来的华侨,一律说是永安堂的职员。廖冰一下有些紧张起来,该不会被敌人盯梢儿了吧?
对方好像看透了廖冰的心事,笑了笑,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是去延安的!你大概也是吧?旁边一个同伴还亮出了给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信。哇,廖冰高兴得要跳起来了,在如此严酷的局势下见到志同道合的同龄人,真让人喜出望外。大家立时成了好朋友,说笑声响彻整个车厢。
火车徐徐驶进西安车站,站台上到处是戒备森严的军警,出站的人要挨个搜身,廖冰的心一下收紧了。轮到她被搜身和翻箱检查时,那个警察从她的箱底翻出一本《西行漫记》。廖冰想,这下完了,肯定要被抓了。那个警察随便翻翻书,然后一把她推倒在地上,恶狠狠地吼了一声“滚”,又顺手甩过她的箱子,箱里的东西乱七八糟撒了一地。廖冰不敢言声,挣扎着爬起来,把东西胡乱塞进箱子,赶紧随人群拥出车站。她一边匆匆出站,心里一边暗自庆幸,那个警察狗屁不是,居然没发现她带了一本犯禁的书。可她到住处整理东西时,发现那本《西行漫记》奇怪地不见了。
有趣的是,这本扉页上题名“廖冰清(廖冰的原名)同志留念”的《西行漫记》,第二年却戏剧性地摆在延安中山图书馆里。同伴们分析,那个检查她行装的警察肯定是自己的同志。
在从西安到延安的路上,廖冰还穿着漂亮的西式白底浅花连衣裙,脚蹬半高跟皮鞋,这身南洋小姐的打扮,在一望无际的八百里秦川高原上好不显眼!
行军第一天,廖冰还兴高采烈地跑前跑后,大家都夸她是“坚强的南洋小姐”。可第二天就不行了,脚上起了泡,两腿发硬,举步维艰。同行的伙伴们逼她骑上毛驴,可她根本不会骑,硬是从驴背上溜溜地摔下来好几回,大家又好笑又着急,于是牵驴的牵驴,搀扶的搀扶,让这位“南洋小姐”倍感温暖和幸福。
到延安后,充满“共产”思想的廖冰对自己的行李作了一次彻底清理。她把自己带来的大笔华侨捐款,自己保存多年、亲手绣织的祖国山河和飞鸟画幅,以及小座钟、手表、金戒指等等各种细软首饰,全部捐给公家。看周围的同学们没有手绢,她就拿出一条裙子一裁十几块,分给大家用。
这里的生活与南洋相比,真是难以想象的艰辛,廖冰在南洋家里一天要洗两次澡,在延安却要十几个人共用一盆水洗脸;吃饭了,用桶盛来的小米饭竟然常常裹着苍蝇,让她难以下咽;冬天盖被子,只有棉絮没被罩,第二天起来棉絮毛毛粘满身……到延安前,廖冰根本不知道虱子是何物,很好奇,身上生了虱子以后,她竟抓了几只,放在信封里寄给母亲,母亲看到信封里的虱子,流了很多泪。
战争也是契机
妇女是人类之母。每个人、每个民族的启蒙教育都是从老祖母的故事和母亲的摇篮曲开始的。妇女的素质、觉悟和解放程度,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并对这个民族的未来产生极大的影响。在人类文明史上,在封建时代的漫漫长夜里,中国女性所受到的压迫与摧残最为惨烈。举世独有的缠足,遍布中国大地的贞节牌坊,全套的“三从四德”封建礼教,这一切都是血淋淋的明证。
活着等于死,战也是死,何不奋起抗争,换一种活法儿呢。于是,五千年来,中华文明所熔铸的爱国心与凝聚力像地火岩浆般喷突出来,让中国的历史遍布起义者造反者抗争者的足迹与鲜血。特别在抗日战争中,无数仁人志士揭竿而起,千百万热血儿女挺身而出,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整个中国从沉梦中醒来了。
在这场空前壮烈的抗日救亡的大潮中,千百万中国女性以出入意料的果敢,掀起一场追求民族解放和自我解放的伟大风暴,其果敢程度悲壮程度甚至出乎毛泽东们的意料。除开前面所描写的那些女性的故事,在历史的记忆中,还有更多的令人难以忘怀的花花朵朵的女孩,跨过死亡的栏栅,潮水般向延安涌来了。
多少兄弟姐妹、老少儿孙是肩并肩手拉手投入抗战的。
夏似萍(生前为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副主任)
夏似萍的兄弟姐妹一共4位,全部到了延安。
抗战爆发后,正在上海读书的夏似萍放弃学业,只身一人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参加抗战。她听说二弟已经到了延安,想到家里还有两个弟妹,便匆匆赶回家,跟父亲说,要把弟妹都带到延安参加抗日队伍去。父亲大发雷霆:你都给领走,只剩我和你妈在家,谁来照顾我们?那天晚上,孤灯残月,万籁俱寂,夏似萍瞧着衰老多病的爹娘,也觉得自己想把弟妹都带走的念头有些冒失,战乱之际,生活的艰难是难以想象的,老人身边确实需要有人照颐。夏似萍决定,还是自已走罢。灯下,她一边给父母缝补衣服,一边聊着她跑出去这一段所目睹的一切。东北人民流离失所、住街头睡窝棚的苦难,京津的沦陷,上海的血战……
第二天早晨,她打点行装准备走了。父亲突然说,你把弟妹领走吧,大敌当前,还是救国要紧啊。夏似萍的心猛地颤抖了,她一把拉过弟妹,跪倒在父亲母亲面前,一家人泣不成声。夏似萍流着泪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父母大人含辛茹苦把我们养大,我们一定牢记父母的养育之恩,等抗战胜利后,回来再孝敬老人吧!
父亲又拿出一百元钱交给似萍说,剩我们老两口虽然寂寞,但总比一辈子当亡国奴强多了。直到姐弟三人走出好远,泪眼中,还能见到父母那瘦弱的身影和缓缓摇动的手臂。
王紫菲(原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党委书记,著名摄影家吴印成的夫人)
王紫菲身材颀长,温文尔雅,有大家闺秀的风范,说起话来温柔轻缓,怎样慷慨激昂的事情听来都像娓娓道来。
她的父亲是贵州省国民党政府的教育厅厅长,家里生活优裕,她又是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的高才生,整日歌呀舞呀,过着无忧无虑的学生生活。“七七”事变后,广州屡遭日机轰炸,书读不成了,王紫菲只好回到贵阳家中。国难当头,百姓涂炭,然而她在家中看到的却是上层社会的麻木与豪奢腐败,这样的日子她一天也过不下去,愁苦郁闷了许多天,她终于下定决心,离家投奔延安。
那时,她不知道表弟是地下党,便与表弟及表弟的一个同学相约,说去武汉找国民政府,还从母亲那儿骗出二百块大洋。路上,又遇到她的两个女同学。5人结伴到了武汉,晚上住在一个旅店,白天却鬼鬼祟祟各自活动,你躲着我,我背着你,王紫非说去“找同学”,表弟说“找朋友”,同学说“找亲戚”。结果在八路军办事处,姐弟俩和3个同学,5个人又撞到一起,这才发现目标是共同的。手足之情又添了战友之情,5个年轻人你捶我我打你,拥抱着笑个不停。王紫菲回忆说,去西安乘的是那种闷罐火车,挤得像沙丁鱼罐头,还常遭遇日机的轰炸,走走停停。她是个女孩子,解手不方便,又不敢下车,怕火车突然开走,一路上不敢吃不敢喝,可把她难为死了。
赵英(原纺织工业部机关党委书记)
赵英一家投身抗战的更多。
她父亲赵家元在上海开了一片生意颇为兴隆的店,平日老成持重,寡言少语,看样子好像对政治毫无兴趣,一心做自己的生意。赵英说父亲,“你真是个老好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你怎么什么都不关心呢?”父亲依然只是憨厚地笑笑,不语。赵英在学校里积极参加学潮,秘密进行各种救亡活动,都是瞒着父亲的。上海沦陷后,她决定去延安,偷偷把衣服等日用品放到同学家里,一切都准备好了,那天晚上向父亲告别,她只说要去参加抗战,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没想到父亲什么也没问,只是关切地要她把路上用的东西都备齐,嘱咐“路上要多加小心”,又拿出一些钱给她,赵英感动得哭了。
直到解放后,赵英才知道父亲的“庐山真面目”。1950年10月19日,上海《解放日报》以“模范军属赵家元”为题,对其父做了这样的报道:赵家元先生出于一片爱国热忱,“自抗战开始到目前为止,共引导全家子侄亲友三十八人参军”,“他开设的店铺和在沪的家居,无形中就成了沦陷区和解放区一个联络转运站”,“他不但帮助和掩护地下工作,同时他自己也曾从事这个伟大的工作,为新四军运送了大量无线电器材等。”“赵家元先生曾被敌特监禁了三个多月,正如他所说:我们同解放区有着血肉的关系,敌人的这些迫害怎能吓倒我们呢!”
赵英笑着对我们说,“那时我在敌后根据地,对父亲的秘密活动一无所知,还以为父亲是个光知道做生意的冬烘先生呢。”
阎明诗(原鞍山市农机厂干部)与高玲(原名阎明英,原南京市科委副主任)
姐妹俩来自解放前在党内很有名的“阎家店”即阎宝航一家,“阎家店”培育了一大家子革命党。在我们采访女大同学时,几乎所有人都向我们推荐阎明诗,说写延安女大一定不要遗漏了阎明诗,她被革命改造得最彻底,简直是一位虔诚的圣徒。
在鞍山,我们见到阎明诗时,她已经坐在轮椅上了。
20世纪初,辽宁省海城县一个村落。书声朗朗的乡塾,一个衣衫破旧的农家男孩经常伏在窗外偷听先生授课。先生发现后,沉着脸把那男孩叫进来,问他为什么这样做?男孩说,他喜欢读书,可因为家穷,无法供他念书。先生感动了,随便出了几道考题要男孩回答,男孩竟对答如流,比坐在课堂上的有钱人家的孩子学得还好。先生惊叹不已,连称“孺子可教也”。于是说服男孩的父亲,以不收费为条件,允许这个“老四”入乡塾读书。这个男孩就是阎明诗的父亲阎宝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