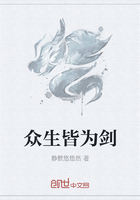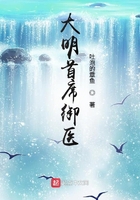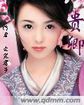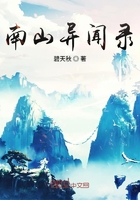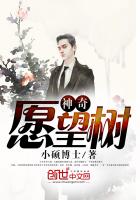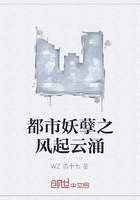张琴秋大姐见万曼琳哭了,心痛地把她拉进怀里,安慰她说,小鬼,你的情况康克清大姐都跟我说了,还特别嘱咐我们要好好关心和照顾你的生活和学习。我们都是革命同志,也都是你的亲人……要勇敢起来,向你哥哥学习,做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
乔凌:“只要不挨打就行!”
乔凌(原武汉床单总厂领导)只知道自己的生日——1923年1月4日,那是上海一家养生堂(当时由外国人开办的慈善机构)给她记录下来的,但她一直不知道自己的生身父母姓甚名谁。显然因为家境过于贫苦,父母养不活她,把她送进了养生堂。小乔凌在养生堂长到两三岁时,上海市郊一位姓乔的爷爷花了三块大洋把她买回了家。
乔家其实也过着清寒的生活,乔爷爷是个烧茶水的,开个小小的茶馆,早起晚睡的很辛苦,街坊邻居遇有红白喜事,他就去脚前脚后地帮忙,从中赚几个铜角子。乔爷爷有一个成年儿子,经常在汉口和上海之间跑买卖,风里雨里奔波忙碌了几年,不仅没赚着钱,反而欠了一屁股债,只好远走高飞躲避债主,一连几年音讯皆无。幸而他已经娶妻生子,算是延续了乔家香火,乔爷爷看儿子已经没啥指望,就早早地为孙子买回一个童养媳,并为她取了名字叫乔凌。
从乔凌记事时候开始,她的记忆中就充满了毒打、欺辱和眼泪,没有一丝丝童年的快乐。从小小的5岁起,乔凌就开始在家里学纺纱,从早到晚,手脚不能停,累得腰酸腿痛,还要收拾家务,洗一家人的衣服,稍有不满,爷爷就会给她一顿暴骂和痛打,还说“棍棒底下出孝子”,有时打处小乔凌屁股肿得老高,晚上睡觉时不敢沾床。7岁时,爷爷不让乔凌在家“白吃饭”,把她送到市郊一个地主家帮着伺弄庄稼,烈日之下,风里雨里,小乔凌像个小长工忙在田间地头,只有汗水,没有玩伴。有一次干活时突然天降暴雨,小乔凌急忙跑到附近一个瓜棚里躲雨,刚巧地主家的小儿子也在那里,那个地主崽子比乔凌大不了几岁,却心生歹意,恶狠狠朝小乔凌扑过来,把她按倒在地。小乔凌已经干了好几年力气活,身上有了些劲道,于是拼命反抗,反而把地主崽子推翻在瓜棚角落,弄了一身泥水。地主崽子恼羞成怒,掏出一把刀子猛地向乔凌刺来,乔凌背转身一躲,刀锋刺进她的后背,乔凌逃出瓜棚,一路飞奔,流出的鲜血把裤管都染红了,而身后,传来地主崽子狂傲的笑声……
背上的伤口,成了苦难生活留在她身上的第一道伤疤。
乔凌10岁时,家里突然发生大变故,半个月之内,乔爷爷和乔奶奶相继去世,家里只剩下养母、乔凌和她的“小丈夫”。有人把事情传告给在汉口躲债的养父,一个漆黑的夜晚,养父突然出现在家里,因为怕债主找上门来,养父白天不敢出门,整天小心翼翼,走路都怕声音重了,全家人一直生活在恐怖的气氛之中。不久,养父带上儿子和乔凌,又悄悄逃出上海,潜入汉口。已经破产的养父没本钱做生意,只好把儿子送去学钳工,把乔凌送到申新纱厂当童工。乔凌被分配到细纱车间,这项劳动要求眼快、手快、脚快,做工质量要求高。车间是两班倒,12小时一个班,小小的年纪,一个班做下来,累得全身骨头仿佛散了架,走路两腿发抖,身子直打晃。回到家里,还要挺着身子烧火做饭,洗衣服,真忙到深夜才可上床睡觉。凌晨3时又得赶紧起床,做好一家的早饭,5时之前再赶到工厂,开始12小时的繁重劳动……
刚刚10岁的孩子,怎么挺得住这样的劳累!有一次因为特别疲劳,眼皮沉重得怎么也睁不开,小乔凌像个机器人似的,只是下意识地在机器之间奔跑着,分理着细密的纱线,终于她挺不住了,意识朦胧之间,细纱终于“开花”了(细纱一处断了就会断一大片,拧成一团如同开花),这时一个凶恶的工头吼叫着跑过来,一把揪住小乔凌的头发,抄起一根尖利的钢管就往乔凌头上扎,嘴里叫着“看你还困不困!”额角上流下汩汩的鲜血,染红了她的脖颈和衣襟。因为没钱治疗,伤口发了炎,整整3个月后才完全愈合,额上却留下永远的伤痕。
这是苦难生活留给她的第二个伤疤。
1934年,申新纱厂失火,主要车间几乎全被烧毁了,工厂只好宣布倒闭破产。失业在家的乔凌又成了“白吃饭”的,天天挨打受骂,过着非人的生活。与其在家当受气包,不如出去找工做。一天大清早,12岁的乔凌偷偷从家里溜出去,跑到汉口第一纱厂找工做,一个40多岁的工头答应给她介绍工作,却把她哄骗到郊外一处农村,卖给一家农民当童养媳。几天之后,养父找到了她,花钱把她赎回家。一时家门,气急的养父用绳子把她的手脚死死捆住,然后用皮鞭没头没脑地猛抽,嘴里叫骂着,死丫头,看你还跑不跑!
这场毒打,在小乔凌身上又留下几道伤疤!
几个月后,申新纱厂恢复了生产,乔凌又回到那里继续做工。1938年,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申新纱厂也出现了中共地下党的活动。这时已经在工厂住宿的乔凌有了一些人身自由,在工厂业余学习文化的活动中很活跃。一天,那位叫毛真的文化教员找到乔凌——他本来是按照蒋委员长的要求,到工厂来开展“新生活运动”的,其实是中共地下党员。毛真问乔凌,小鬼愿不愿意离开家,到一个新地方去学文化?
乔凌说,当然愿意!你说吧,去哪里?
毛真说,那地方你想做工就有工做,想读书就有书读……
乔凌一听,高兴极了,读书是她梦牵魂绕的奢望啊!不过这位毛先生是不是骗人的,世界上真有这样的好地方吗?在黑暗的旧中国,乔凌挨打的记忆太深太痛了,她脱口问道,那里挨不挨打?
毛真笑着说,那里怎么会挨打?在那里人人平等!
乔凌立马说,只要不挨打,我去!
几天后,毛真和另外几位姐妹一起,从各自的家里偷跑出来,由毛真带队,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报到,然后坐上脏乎乎的运煤车,北上西安。在从西安步行到延安的路上,带队的邓队长为大家做动员,说,延安的条件非常艰苦,大家一定要做好吃苦耐劳、流血牺牲的思想准备!
激动万分的乔凌脱口说道:只要不挨打就行了,大家哄地笑起来。
伍良素:跟随百名壮士奔延安
1935年初,一支红军队伍浩浩荡荡开进贵州遵义市,正是在这里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我党我军的领导地位,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而深入到遵义高坪乡的一支红军队伍,也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一位女性的一生。
伍良素(原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副行长)的家是高坪乡的大户,她的祖父是前清秀才,父亲和大伯做盐业生意,家境富裕,日子安稳。遵义一带有钱有势的人听说红军快到了,早早就关门歇业,跑到外地躲避。伍良素的父亲和大伯虽然躲了,但母亲宋玉兰为照看家业,没走。
十几位红军战士住进伍家,他们不仅没有没收伍家财产,还热心地帮母亲出售食盐。伍良素亲眼看到,红军战士们每天挑水、扫院子,和妈妈一同煮饭、洗衣服,在乡里不欺压老百姓,不调戏妇女,买卖公平,损坏东西照价赔偿,这一切都给伍良素留下深刻印象。红军第二次经过遵义时,有一个红军战士受伤未能跟上队伍,跑到伍家躲藏,母亲二话未说,就把他收留下来。母亲给他上药,缠绷带,又换上伍家帮工的旧衣,到傍晚时,母亲让战士挑着煤篮子,亲自带他从小路出城去追赶红军队伍,避开了白军的追杀。母亲的大义之举吓坏了父亲,父亲大骂母亲,怎么可以干这种“满门抄斩”的事情!母亲镇静地说,我不明白什么世事道理,人家红军帮过咱,咱就得帮人家!
红军的行为一直深深影响着伍良素。1939年春,在遍及全国、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伍良素与遵义女子中学的同学杜奇结伴离家,共同踏上奔赴延安的征途。她们的第一站是重庆,然后徒步转移到成都。成都是大后方,进步学生和革命青年比较集中,中共在这里的活动相当活跃。一到成都,伍良素就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群力社”,很快又秘密入党。她与大批青年同学走上街头,积极参加宣传、游行、募捐,大唱救亡歌曲,到医院慰问被日冠飞机炸杀的群众。她和同学们的热血在胸中沸腾,她和同学们的激情在街头激荡……
1939年10月,伍良素在成都结识了《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光未然,当光未然得知伍良素想去延安的心愿后,便告诉她和同学黄颖说,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创办了“民族革命大学”,派人入川招生。这里的热血儿女们群起响应,呵气成云,我们党决定趁这个机会,把大批需要撤退和要求去前方的党员和青年骨干送到前方去,这样既可保存干部力量,又可增强前方抗战力量。
伍良素和黄颖立即报了名。
1939年12月8日,参加“民大”的学员按军事组织编成一个大队,下设四个中队,徒步向第二战区出发了。队伍告别成都时,全市各界举行了盛大欢送会。
这支队伍上路走了没几天,伍良素脚上就起了大泡,而且发了炎,站立都很困难,简直痛苦不堪。正是隆冬严寒季节,队伍从四川到陕西,要翻巴山,越秦岭。队伍一路奋勇前行,一边向民众宣传抗日,自称是“小长征”。途中,有一天忽然来了13个男女青年。一问,他们都是来自海外和广东的爱国青年,满怀赤子之心来到重庆找国民党政府,要求去前线抗日,想不到竟无人理睬。听说这支学生军之后,他们在后面悄悄跟了数天,经观察证实这是真正去抗日的队伍,便要求加入。双方热烈拥抱,群情激奋,这13人被大家誉为“十三勇士”。
队伍行进途中,得知阎锡山背信弃义,公然发动了反共的“十二月事变”,仅“民大”学生就牺牲了数十人,二战区的新军(中共领导的部队)与旧军(顽固派领导的部队)正打得不可开交。这支“民大”学生队伍义愤填膺,决意改变路线,不去给阎锡山“壮门面”了。几位领导者都是地下党员,经报请党组织同意后,他们一边与阎锡山派来的接收人牛队长等人斗智斗勇,假意周旋,一边秘密准备转道奔赴延安。
一天深夜,牛队长被灌得酩酊大醉,队伍悄悄集结起来,领导人王怀安站在队前,神情严峻地征求大家意见:同志们,闫锡山现在反共了,我们是到反动黑暗的地方去,还是到进步光明的延安去?
大家群情激奋,振臂高呼,去延安,跟着共产党抗战到底!
当夜,这支近二百人的青年队伍于洛川突然转道奔向延安。党中央派冯文彬、徐一新、柯仲平、韩天石等人到三十里堡迎接这支年轻的队伍,欢呼声、口号声在山谷间久久回荡……
从1939年12月8日自成都出发,到1940年2月2日胜利到达延安,这支150多人的队伍徒步行军57天,行程3000多里,大家浑身上下衣裤鞋袜都破烂不堪,还长了虱子,好像一群流浪者,但到了梦想已久的革命圣地,每个人都情绪高昂,歌声不断……
最后还有一个小插曲。不久后,阎锡山向毛泽东发电抗议,称共产党劫走了他的学生,要求把人送回。毛泽东笑着说。共产党是从不抓壮丁的,这次我也不开先例。他要人把电报送给大家,说去者欢送,留者欢迎,由学生自己决定去留。
数天后,150多人联合签名的致阎锡山的公开信在《新中华报》上刊出,信中申明大义,称“因为你们开倒车,我们青年不得不离开你们。阎先生如能改弦更张,坚持抗日,我们会回到先生身边的。”
阎锡山再无反应。
廖冰:南洋小姐跨海抗日
身材娇小玲珑,谈吐轻缓从容,一副金丝边眼镜,尽管已是夕阳暮年,但内在优雅而文静的气质是你迎面就能感觉到的,这就是廖冰(原中国科学院机关党委副书记),谈到当年,她笑着对我们说,我是穿着高跟鞋从南洋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
1917年,廖冰生于广东省大埔县平原乡的一个医生之家。在她的少女时代,大革命如烈火怒潮,席卷整个广东省,中共在大埔县建立了革命武装和苏维埃政权,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许多村镇成立了工会、农会、妇女协会等组织。革命的浪潮也波及到廖家所在的平原乡,平原公学成为革命者最为活跃的地方,那里的老师也受到新思潮影响,带领学生四出宣传进步思想,还排演了表现苏联革命成功的白话戏剧,演员都装扮成俄国人模样,各乡各村的老百姓何曾见过这么新鲜时尚、洋里洋气的演出?人山人海地围着看。
廖家人世代学医,家风忠厚正直、乐施好善,深得村民的尊重和爱戴。廖冰的大哥廖优健是平原公学的教师,一向热心进步活动,革命者连半天先生是他的结拜弟兄。这样,在廖家的药铺里,常有平原公学的老师和革命者来喝茶聊天,研究革命斗争。就在这经意和不经意之间,廖冰常听到一些慷慨激昂的革命言论,什么“阶级斗争”啊,“压迫剥削”啊,“西方列强”啊,虽然这些词汇对于少女廖冰来说还有些费解,但她记住了男女要平等、男人不能打女人、女人也能和男人一样去上学……
9岁那年,廖冰眼见表弟进了学堂,便也哭闹着要去念书,在大哥和连半天先生的支持下,她成了平原乡有史以来第一个进学堂念书的女孩,而且回回考试全班第一,还从一年级一下跳到了三年级。才女的名声立刻传遍了全村,廖冰竟然成了学习的榜样,很多人家受廖冰的启发,都送自己的女儿上学了。
1927年春,正是北伐战争胜利发展、工农运动风起云涌、国民革命进入高潮之际,老师每天都给学生们介绍和讲解国内局势和每天各地发生的事情,放学的归途中,孩子们还在老师的带领下高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奋斗,齐奋斗……”然而,白色恐怖却裹挟着血雨腥风突袭而来。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大开杀戒。很快,平原公学被查封,连半天等许多革命者被迫转移,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被捕被杀,廖冰的一位参加农村暴动的堂兄也未能幸免。她亲眼看到一批批青年被捆绑着从自己家门前的大路上走过,在死亡面前,他们毫无惧色,个个昂着头,大义凛然,一路高呼口号:“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土豪劣绅!”“中国共产党万岁!”
廖冰的心灵被如此惨烈的场景猛烈地撞击着,崇敬、恐惧、无奈、仇恨、难过、思索,久久地交织在一起。
父母和哥哥常在家关起门来大骂国民党当局,盼着红军早日胜利。小廖冰就坐在床边,竖着耳朵听他们谈话。一个狂风呼啸的深夜,廖冰发现大哥悄悄回来了。他告诉母亲,自己前几天被抓了起来,在押解途中他设法贿赂了押送的大兵才逃了回来。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大哥决定逃往南洋。慌乱中,母亲从柜子里取出一些银元交给他,什么也来不及说,大哥就消失在无边的夜色中了。从那天起,恐怖的气氛笼罩了小廖冰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