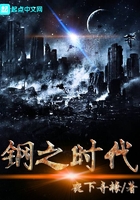“想要的话,一会儿再继续,现在还是先吃些东西吧。要不然今夜……饿了就刹了风景了。”燕邪放开青染,暧昧地轻笑道。接着声音微微扬起:“让你们把饭菜端来这里,没听到吗?”
男子俊美妖异,女子清冷美丽,这香艳如花的一幕早已令传膳的几人看得几乎鼻血狂流,失了神智。忽听燕邪声音响起,蓦地清醒过来,面红耳赤地将桌案搬至软榻前,手忙脚乱摆好了饭菜,施礼之后匆匆倒退而去。
见几人离去,燕邪微微一笑,提箸夹起一块茄骜,送至青染嘴边:“来,尝尝看,这个味道很不错。”
“已经没有人了,还有演戏的必要吗?”青染推开那已经卸了劲道的手臂,站起身看着燕邪,冷笑道。方才那冰冷的一吻,没有情欲,没有需索,瞬间便让她猜到了他的心思。
筷子顿了一下,燕邪没有反驳青染的话,慢慢将茄骜放入口中,细嚼慢咽之后,也缓缓站直身子,居高临下地看着她。随后伸手擒住她的下颚,桃花眼牢牢锁住她的双眸。
青染被迫仰头看着燕邪,看他眼中瞬间闪过的种种心思。正在思忖该如何应对他接下来的言语,燕邪已经松开手重新坐下,接着方才的动作,慢条斯理姿势优雅地继续用膳。
燕邪这样的反应,令青染颇为意外,怔怔地看着他,一时间竟不知道该如何举动。
“不坐下吃饭,等我喂你不成?”见青染迟迟不动,燕邪淡淡开口。语气中不见了方才的轻佻,多了几分疏离和冷漠。
然而,这冷漠不耐的口吻,却令青染暗暗松了口气。直觉认为,这样的口气,才是这个男人的真实性格。虽然不知道他为何要刻意做出方才那般举动,但是比起来,她宁愿和现在这个冷漠的燕邪共处一室。
青染斜斜地坐在桌子一角,尽量远离燕邪。端起碗,饭菜的香味传来,青染这才发觉自己早已是饥肠辘辘。
看着青染坐下,燕邪拿起一只空碗,随意夹了几筷菜肴放入碗中,将其放到青染面前:“这是你的,其余的不准动。”
刚刚提起的筷子停在了半空,青染看着眼前堆得乱七八糟的一碗菜,顿时没了胃口。这哪里是给人吃饭的样子?分明是在喂猫猫狗狗。
看也不看眼前狼藉的碗,青染将米饭端起,大口吃着。
一餐饭,总算是“安安静静”地吃完了。
晚膳用罢,侍从们入内将碗盘撤下,帐帘再次挑开,两个粗壮的侍从抬着一只红木浴桶进来,在里面注满温水之后,施礼退出,将帐帘从外面掖得严严实实,隔去了秋夜的凉意,也隔出了一方静寂的空间。
燕邪懒懒起身,脱去松散的外袍,正欲跨进木桶,忽地想起什么似的,转头看向青染邪邪笑道:“要不要来帮我擦背?或者……干脆一起洗好了。”
见燕邪起身脱衣,青染早已经背转身子。她虽然在现代生活了六年时间,又在幽雅阁做了数月歌姬,却依然没有勇气直视男人的裸体。对于燕邪戏谑的语气,青染只做充耳不闻。
身后水声响起,显然燕邪已经开始沐浴。尴尬之后,青染索性就地坐下,倚靠在帐篷一角,合眼假寐。
看着缩在角落里的纤细身影,燕邪唇边笑意更浓。每次见到这个倔强的女子,他就忍不住想要逗弄一番。这种乐趣,比驯服一匹烈马,或是俘获一只雄鹰更加有趣,更加具有挑战性。
何况,这个女子于他,不只是一个把玩消遣的宠物。他的计划,也需要她的协助。比起架上那些刻意做旧的书来说,一个活生生的女人更有说服力。只是,他还需要一个合适的契机来说服这个软硬不吃的女人,好好配合。
不过今晚,还是让她好好睡吧……看着青染沉睡的容颜,燕邪眉头忽然不自知地皱了起来。几月未见,她愈发消瘦了。虽然沉静依旧,但是眼角眉梢间蕴藏的伤怀却更加深沉。细细想来,自从在山林茅屋中相识之后,数次谋面,都从未见她笑过。那纤细的身子里,到底隐藏了多少悲伤和哀戚?
就像此刻,虽然她身在梦中,但那深锁的眉头和眼角渗出的泪显示着她睡得并不安稳。那无意识抽动的双肩,每一下瑟缩,都让燕邪心烦意乱。索性转过身子背对着她,却还是按捺不住回过身来。几次三番地折腾了许久,燕邪最后终于抵受不住,猛地坐起身来。
游戏还没有开始,她若病了,岂不是少了许多乐趣?终于为自己的反常找到了理由,燕邪拿起薄毯,想要将伏在羊毛地毯上和衣而眠的青染抱起。
尽管动作极其轻柔,但在他的手触及到她身体的那一刻,青染还是蓦然惊醒。
看着不知何时站在身前的燕邪,青染一惊,霍地坐起身来。谁知动作太过剧烈,一时间眼冒金星,险些栽倒。
没料到青染竟然会突然醒来,燕邪伸出的手愕然停在半空。本就因为自己今夜反常的行为而烦躁的燕邪,在看到青染那仿佛见鬼一般的举动之后,更加羞恼。
冷哼一声站起身来,燕邪大步走回软榻,重重躺下再也不动。
乍醒的青染初时还有些莫名其妙,待晕眩的感觉退去之后,立刻感觉到了身上传来的柔软触感。
将薄毯向上拉起,盖住自己单薄的身子,上面的温暖带给了青染莫名安心的感觉。除了母亲,这还是第一次有人为她盖上被子。
想起莫溪,青染只觉心头酸痛,垂头将脸埋进毯子里,将无声的哽咽和奔涌的泪水一并掩去。
虽然平日里她都表现得冷清漠然,坚强而镇定,可是又有谁知道,午夜梦回之时,她有多少次从梦中哭醒?母亲惨死的一幕,紫衣决绝的信函,韩霁遥离去的背影,还有林涯行踪的渺茫。一桩桩一件件,走马灯一般在零碎的梦里穿插纠缠,伴着她的泪直到天明。
方才,本来只想打个盹,却不期然地再次陷入了悲戚的梦境。从痛苦中蓦然惊醒,便看到了背光而立的燕邪。身上的毯子带着属于他的味道,披在她的身上。第一次,青染觉得眼前这个邪魅的男子不再阴森,不再危险,他眼中那转瞬即逝的情感,是……心疼吗?
怎么可能?一定是自己睡迷糊,看花眼了。青染迅速否定了这个可笑的想法,见燕邪并无他意,紧张的心情这才渐渐放松下来。
将身子蜷缩进薄毯之中,青染慢慢躺下,只留给燕邪一个单薄的背影。
“谢谢。”不知过了多久,就在燕邪以为青染睡着了的时候,她轻不可闻的声音悠悠响起,像是清晨的雾般朦胧轻微,很快便消失在静寂的帐篷之中,恍如错觉一般。
然而,就是这轻得不能再轻的一声谢谢,却在燕邪心里荡起了密密的涟漪。烦躁的心奇迹般地安静下来,看着角落里蜷缩的人儿,燕邪轻轻弯起唇角,发自内心清浅而温柔地笑了。闭上眼,仿佛还是可以看到她身上那跳跃的蜡烛的光晕,橘黄色的影子,无声无息地映入了记忆的深处……
天明时分,燕邪缓缓睁开眼睛,顺着窗隙中明亮的光线,将视线停留在那依然酣睡的人儿脸上。平日里鸡鸣则起的他,竟然也会睡到这个时候。而让他破例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女人。她均匀香甜的呼吸,胜过最好的催眠药物,令习惯性地戒备着别人,拒绝任何人靠近的他无端地安心和沉醉。一如那个山洞中的夜晚,他睡得也是如此安稳踏实。
将这个玩物留在身边,果然是个正确的选择。
似是感觉到了那炙热的注视,熟睡中的青染黛眉微皱,素手扬起抚上额际,蝶翼般的长睫颤动着,露出那明媚的双眸。片刻迷蒙之后,很快便清亮如水。
“你乖乖留在这里,不许乱跑。”见青染醒来,燕邪漠然开口,随手拿起架上的衣袍,大步离去。
“九殿下今日起得好早。”军营中一处空地,摆放着矮桌躺椅,秦绍白悠闲地靠在躺椅上,向着燕邪温文笑道。
“先生有话直说吧,这样阴阳怪气的,实在有损你的形象。”秦绍白之于燕邪,幼年时亦父亦师,燕邪渐渐长大之后,又像是忘年之交的好友。言语间自在随意,没了和旁人相处时那习惯性的伪装。
“听说九殿下费尽手段将魏国太子妃掳了回来。”秦绍白依然是那副不紧不慢的样子,手捋胡须眯眼看着燕邪,“不知此事是真是假?”
“是,她现在就在我营帐之内。”燕邪毫不犹豫,爽快承认。
“那不知九殿下有何打算?”秦绍白继续追问道,“不要忘了,按规矩这敌国皇族不论是谁捉到,都必须交给统帅带回南燕国,由皇上发落。你这样私下藏匿,会惹来麻烦的。”
“谁说我要私自藏匿?如此暴殄天物之事,我怎么会去做?”燕邪自斟了一盏香茗,看着朝阳映照在其中的橙红的倒影,笑得意味深长,“就像这盏中旭日,虽在我的手中,却也要让众人欣赏才是。若是无人知晓,我斟这杯茶又有何意义?”
秦绍白坐起身子,抬起手至半空,恰好挡住了那柔美的倒影,口中轻笑:“只怕到时可不止你一人手中有茶。而这倒影的心,终究还是在天上。”
“一个玩物而已,心在哪里又有何妨?”燕邪笑得云淡风轻,不以为意。
秦绍白没有回答,视线淡淡扫过燕邪,复又躺回到椅子上,闭目养神。直到燕邪手中的茶盏渐空之时,方才从唇间吐出几个字来:“当局者迷。”
至晌午,燕肃、燕黄纷纷归营。三军会齐,马不停蹄班师回朝。
浩荡大军长蛇一般从旷野中穿行而过,蜿蜒看不到头尾。燕肃在前领军坐镇,燕黄在后监军收尾,燕恒与燕邪二人则策马在中来回巡视,以防有变故发生。
这样的差事,无聊至极,乏味得令燕恒昏昏欲睡。他是一个直来直往的性子,豪爽快意。若是让他横刀立马征战沙场,那自是不在话下,可是让他干这巡逻的差事,却是要了他的命。不过一个时辰,他便已经按捺不住,离了职守的岗位,策马来到燕邪身边,并肩而行。
“啊……”大大打了一个哈欠,燕恒抓抓脑袋,向燕邪抱怨道:“这慢慢悠悠的,几时才能回去?要是依我的脾气,立刻急行跑步前进,有掉队的就打二十军棍,保证三天之内就到了南燕国边境。”
“三皇兄这火爆性子实在应该收敛一下了。”燕邪端坐在马上,看着燕恒笑道,“父皇都说了你多少回了,还是不知改改。”论才能,燕恒并不亚于燕肃、燕黄二人,只是这急躁的性情遮掩了他的才华,使得多数人都觉得燕恒只是一个有勇无谋的莽夫。
“自小就这性子,改不了了。”燕恒撇撇嘴,百无聊赖地四处张望,忽地看见一物,好奇地问道:“哎,我说九弟,那是你的马车?”
燕邪顺着燕恒的视线望去,点头道:“嗯。”
南燕国皇子皆以苍狼为图腾,只是样式各有不同,依个人喜好来定。燕肃便选了藐视天下的傲立于峰,燕恒则选择了草原驰骋的自由奔放,燕黄的苍狼图腾对月长嚎野心勃勃,而燕邪的则是一只休憩于林的悠闲睡狼。前三人的苍狼图腾皆是全身雪白,显示着苍狼中最高贵的血统,唯有燕邪的卧狼遍体漆黑,带着夜的阴鸷与神秘。
据说这乃是朝中数位众臣联名向燕留远提的建议,说是九殿下大典之日惹来雷击图腾圣碑,所以自然不可再以白色苍狼为徽,以免再次惹来天灾。燕留远当即点头,所以便有了这与众不同的徽印,毫不留情地时刻提醒着燕邪那不祥之人的身份。
“我说九弟,你那车里是什么东西?”燕恒把视线从卧狼图腾上移开,落在了赶车人的身上。那个面色冷峻的侍卫他有印象,似乎是叫残影,乃是燕邪亲随,而身边坐着的那个玉树临风青衫长髯的中年男子则是燕邪的老师秦绍白。
这二人坐着的马车上,到底会载着什么珍贵东西?
“在魏国遇到的一个女子。”燕邪淡淡道。
就是这简单的一句话,却差点儿把燕恒吓得跌下马来。手忙脚乱重新坐稳,他瞪大眼睛看向燕邪:“你说什么?”
他是不是听错了?那个向来厌恶女人接近,只因为被碰了一下衣服就把美貌歌姬踢飞的燕邪,竟然会让女人坐上带有他徽印的马车?这个玩笑开得有点儿大了吧?
“九……九弟啊。”燕恒额角抽动,试探着问,“这女子莫不是仙女下凡?”是哪家的大家闺秀有如此魅力,让眼高于顶的南燕国九殿下动了心?
“是一个歌姬,已经嫁人了。”又是一句令燕恒五雷轰顶的淡淡回答,燕邪说着,视线也落在车厢上,桃花眼中柔情似水,“我准备回去后便行了仪式,娶她为妃。”
看着燕邪温柔的模样,燕恒似乎听到了自己下颚脱臼的声音。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一物降一物?风华绝世、俊逸如仙的燕邪,最终竟会把心落在一个青楼出身的已婚女子身上。若不是听他本人说,打死燕恒也无法相信。
看看卧狼徽印的马车,再想想那日酒楼的情景,燕恒忽然有了仰天长叹的冲动。真是世事无常啊。
燕邪不动声色地将燕恒的反应看在眼底,面色未变,唯有眼中迅速闪过一抹算计。对,就是这样的反应,与他的设想完全吻合。接下来,只要按照计划一步步走下去就行了。
入夜,大军就地驻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