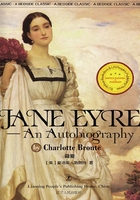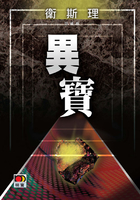小冯姑娘是队上的资料员,她个子不高,胖胖的,走道儿哼着歌儿,手里还晃动着一串铜的、铝的钥匙,“哗铃哗铃”地摇。乍看上去,她和中学生没什么两样。
小冯姑娘每天的工作,就是把全队各井、站上送来的产油、产气、注水量的数字汇总起来,抄一份给大队好再汇报,抄一份给队长晚上开会时好批评人。剩下的事情,就是分分报纸、送信、听电话,实在没有事情可干了,就把队部的那台一打开就“滋啦啦”乱响乱跳的破黑白电视打开,白天看,晚上看,总也看不够。
我初到羊儿洼油田的时候,与小冯姑娘住隔壁。
同样是隔眼不隔耳的板房,可我的板房西面,是三间空荡荡的库房,饿红了眼的耗子们,大白天都在里边追杀惨叫,怪碜人的!隔墙的东面,虽说住着小冯姑娘,可她,整天不在房间里。
每天,我只能在吃饭时候,听到小冯姑娘“哗铃哗铃”摇着手中的钥匙,哼着:“泉水叮咚,泉水叮咚!”或是什么更好听的歌儿回来拿碗。除此之外,一整天,我再也听不到她任何响动。
有几回,我闷在屋里看书,听她“哗铃哗铃”唱着歌儿走来,真想放下手中的书本,同她搭搭话儿。可她,从我门前经过时,胸脯挺得高高的,趾高气扬的样子,睬都不睬我。
这日黄昏,下雨。
我独自坐在窗前,凝视着窗外的“沙沙”漂落的雨丝,又联想起学院里男生、女生们在一起读书学习的情景,不由自主地涌起了一阵阵骚动的心潮。恰在这时,门外突然响起一串“扑吃扑吃”的踩水声,我知道是小冯姑娘回来了。
刹那间,我没等她把房门打开,就大声地隔墙问过话去:“几点啦,小冯?”
我这样问她,她好像知道我要干什么,一边抖着雨衣上的雨水,一边告诉我:“还差十分钟。”
指开饭时间。
“给我带两个馒头好吗?我没有雨衣。”
她脆生生地回答我两个字:“好的!”
转天,又是开饭时间,她便主动隔墙呼唤我:
“大学生,开饭喽!”
我坐在桌前,好像一直在等待这个声音。但我听到她第一声呼唤时,并没有急着回应她。这时刻,她便会再喊一声:“开饭喽,大学生!”
听到她甜甜的喊声,我多数时候是拿起碗同她一道儿走。有时,我拿着饭票,门口堵她:“给我带两馒头?”
“谁给你带两馒头!?”她这样说着,冲我一撅嘴儿,做个鬼脸,那只胖胖的小手,如同小燕子捉食似的,一下子把我手中的饭票捉去。
回头来,她不但给我带来馒头,还用她那小巧的饭盒盖儿,给我带来一份我爱吃的菜。
日子久了,我们彼此更熟悉起来。有时,她从队部回来路过我门口,看我正在埋头看书,便轻轻地猫着腰,绕到我身后,猛一跺脚,脆脆生地喊一声:“嗨!”故意吓我一跳。常常是逗得我笑,她也笑。
这天晚饭后,停电。
我们坐在门口说了一会儿话,两人一起到房后的河堤上散步。期间,我给她讲了很多她不知道的知识,还给她背诵了普希金的一首爱情诗《赠娜塔利亚》。
一时间,不知她是在用心记我的话,还是在思索什么更奇妙的问题,低着头走在我的身边,一句话也不讲。
印象中,那晚的月亮,映在淙淙流淌的溪水里,很美!路过一处河水打弯的地方,她突然停下脚步,压低嗓音,喊我:“大学生!”
我一愣,觉得她声音有些异样,忙唤她:“小冯?”
一语未了,她转身靠到我的怀里,头顶着我的下额,轻轻地问我:“羊儿洼,好吗?”
我似乎意识到了什么,猛推她一把,唤道:“小冯!”她连退三、四步,差点跌个后仰翻,我的心随着一揪!可她,到底还是吃力地站住了。
“你!”她紧咬着粉唇,好像不认识我似的,静静地盯着我。突然,“哇”地哭出声来,转身,独自前头跑去。我跟在她后面连喊几声:“小冯,小冯!”她头都没回。
当晚,我回去时,她已关灯躺下了。
半夜里,我听到她“呜呜”地哭泣。
此后几日,小冯姑娘总是躲着我。有几回我故意同她走个碰面,可她睬都不睬我。我心里很难过!想到我来羊儿洼这几个月,与我接触最多的就是小冯姑娘,她是我在羊儿洼唯一的亲人。平日里,帮我带饭、洗碗,有时,还悄悄地把我床上的单子扯下去洗。但我,万没料到我们会是这样的结局。
这天夜里,也就是我接到调令,要离开羊儿洼的头一天深夜,我木木几几地唤醒了她。
没料到,她冷冷地问我:“什么事,半夜三更的?”
我说:“我要走了!”
“要走了!”她一把拽亮电灯。隔墙问我:“不是说实习一年吗,怎么现在就要走了?”
我说:“是厂部决定的。”
之后,我听她摸摸索索地穿上衣服,拉开房门。待我也开门让她进屋时,她却站在我的门口不进来。
她问我:“是不是因为俺?”
我说是厂部决定的。
可她,还是说怪她!鼻子一酸,泪水“扑扑”地滚下来。
可巧,那天后半夜,羊儿洼落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小冯姑娘没等到天明儿,便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步行到十几里外一个叫曹家乌的小镇上,专程为我买来一个日记本。
令我吃惊的是,那本子送给我时,扉页已被她撕去,但从字痕中,可以看出她在扉页上写过什么。原认为她是写错了什么字,不好意思让我看到,而就手撕去了。没想到,上路的那一刻,我去找她道别,发现她撕掉的那张扉页,正压在她桌上的玻璃板底下,上面端端正正地写道:
留下的是我的
送走的也是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