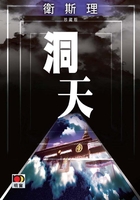歌舞举办得十分隆重,百十名歌女在王府的戏楼里载歌载舞。王府几百人定定地围住观看,现在上场的是一名很滑稽的小丑,小丑灵巧地在舞女们身前身后穿梭着,闪展腾挪,脚步轻灵得如长了翅膀。能看出此人的功夫极好。不时有人轻声喝彩,在这里是没有人大声喧哗的。
丁月华看到白玉堂身上背的那只包袱,笑道:“你不能解下来吗?”
白玉堂笑道:“不能。这里边装的是某大人的前程,白玉堂一刻也不敢疏忽。”
丁月华又问道:“白玉堂,你如何到了这里?”白玉堂盯着丁月华,突然长叹一声:“丁姑娘,我不曾想过你就是展昭夫人。”他不再说,远远望着坐有襄阳王身边的钟涛,他心里有些乱。一串哨子响在空中划过,他仰头一看,见几只鸽子从头上飞过,鸽子一般晚上是不飞出的,除非是训练有素的鸽子,他心念一动。
丁月华苦笑:“前番不曾以真情告知,还望海涵。”
白玉堂问:“不知丁姑娘何时到京城与展护卫完婚?”丁月华笑了:“这要问你了,你不是还要与展昭较量吗?如果有了死伤,我怕是要另择婆家了呢。”
白玉堂粲然一笑:“丁姑娘莫要误会,我与展昭并无仇恨,如果不是当今圣上赐下的‘御玉堂决不会与展护卫有什么过节的。”
丁月华问:“这一个名字果真那样重要吗?白玉堂点点头:“是的。”
丁月华长叹一声:“你何苦要与展昭两败俱伤呢?玉堂兄,我敬你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却不想你心胸如此狭窄。”白玉堂微微一笑,并不答话。
丁月华突然不再说话,她的目光在灯光下显得十分忧郁。她呆呆地看着白玉堂,目光中一种热力弥散出来。
白玉堂感觉自己心里一阵急跳,他当然有些明白丁月华的目光。他把持了一下自己,笑道:“今天晚上的歌舞真好啊!”丁月华怔了一下:“哦,真是很好。”她微微朝白玉堂笑着。两个人再也无话,呆呆地看着歌舞。
白玉堂禁不住侧目看了一下丁月华落在双肩上的那浓密乌黑的头发,真像一匹黑色的绸缎。丁月华的微笑,使她的容貌更加美丽如仙,白玉堂有些把持不定了。他感觉自己心中的血在突突奔涌。
丁月华笑道:“你何不在襄阳府盘留几日?”他笑道:“我邀了一个人在陷空岛见面,我要急着回去了。”他心中突然闪出一个杂念,他想起了东京城里的颜査散。他委实有些担心了。
丁月华一怔,笑道:“玉堂兄,这歌舞真是闷气,我们何不到城外的山上去看看。”
白玉堂笑道:“我正有此意。如此秋高气爽,正是游山的时节,只是这夜晚,你我孤男寡女……”
丁月华笑了:“你这人还真是迂啊。”就起身离座出去了。白玉堂笑笑,也起身跟了出去。
襄阳王府傍山而建,从北门出去,走不了几步就上山了。闪闪的星空广阔地展开了,四野在星空中显得辽远。山上是昏暗的,这昏暗的夜色使他们愈加亲近了。二人走了几步,丁月华脚下一滑,身子就靠在了白玉堂的身上。她的胸部起伏着,她凝望着昏暗的田野出神,暗夜里快意的气氛围绕着她,她很想对白玉堂说些什么,可她什么也不说。白玉堂也没有推开她,任她倚靠在自己的肩上,闻着她身上那种醉人心魄的气息。
远处的山谷中传来亲切的淙淙水声,远处有些如豆的灯火闪动。于是,大地和天空被这些如豆的灯火截然分开了。山脚下有萤火虫扑上山来,白玉堂心情很乱,他一时生发出一个念头,他很想在这么一个静静的晚上,和自己爱着的这么一个姑娘坐上一夜。
突然丁月华笑了起来,白玉堂被她笑得愣了。丁月华跳起来,向山下跑去,她的笑声像一串清脆的响铃向山下跳去了,白玉堂听得美妙如仙,他欲跟下山去,而就在这一刻,他突然清醒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感觉击中了他,他转身朝相反的方向去了。那是刚刚在襄阳王府里他看到的一群鸽子飞去的方向。
但是他刚刚跑了几步,忽然听到丁月华的呼救声,声音尖厉。白玉堂忍不住,转身向呼救声跑去,当他跑到山洼处,见丁月华被人绑在了树上。几个蒙面人正在剥丁月华的衣服。白玉堂大喝一声,就纵身过去,几个蒙面人就与白玉堂交上了手。几个回合过去,那几个蒙面人处在了下风,其中一个打了一声口哨,夺路而走,余下的也跟着飞奔去了。
白玉堂感觉身后有些不适,但他来不及多想,纵身过去解救丁月华,他心头却是一亮,突然明白了许多事情。他嘴上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忙把丁月华身上的绳子解开。丁月华一下子扑进了他的怀里。爽朗的月光下,白玉堂看到了丁月华粉颈处露出的内衣一角。
此时的白玉堂心中已经清醒如初。
月亮像一个银盘。
白玉堂知道自己可能落进了一个别人事先设好的圈套里了。他有些明白,这几天发生的一切,是有人在背后安排好了的。
他现在已经无奈,看看背后那个包楸,并无异样。但是白玉堂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结果。
割袍断义
颜査散已经被关了五天。
他被关在开封府的牢狱里。雨墨住在开封府外的一家客栈里,每天来开封府要求探望主人,开封府却是不让雨墨见颜査散。
颜查散没有想到皇上宣他进宫只是为了诱捕他。五天前,他进了东京,皇上却没有见他,他被安排在开封府的后院住了三天,再一天,开封府召他上堂。当他走上开封府的大堂时,几个粗壮的武士已经准备好了枷锁。颜查散皱眉,他认为自己掉进一个圈套中去了。他根本没有见到皇上,就直接被关起来了。
今天一早,颜査散被张龙几个带到了开封府上。包拯已经威严地坐在了大堂上。包拯请颜査散在堂下坐了。
包拯叹口气:“颜先生,我包拯今天奉命审讯你,只要问你对大名王、太原王、河间王被害一事是否知情?如若知情,还望你从实招来。”
颜查散道:“包大人,此事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是要见皇上有话要讲。”说罢,他埋下头,闷闷不语。
包拯想了想,对颜查散道:“颜先生,你说你在济南王那里任职,但我遍查济南王属下的名册,并不见你的名字。这是怎么一回事情?”
颜查散仍然不说话。
公孙策走过来,跟包拯耳语几句,包拯点点头。包拯对颜查散道:“我看你神色恍惚,你还是先在开封府里休息几日,过几天我们再讲。”
颜查散点头,起身告辞。包拯望着颜查散走出大堂,心里一阵慨然。从心里讲,他并不认为颜查散有什么错,可是皇上认定被济南王收罗的人物都是有谋反嫌疑。从心里讲,包拯宁愿相信襄阳王心怀不轨,而济南王却是一个安分守己的王爷啊。而公孙策所讲,他不可将颜査散交付圣上。公孙策似有难言之隐,包拯也感觉这其中的文章太多。
包拯心里想着,此时欧阳春和展昭应该在什么地方呢?他正在想着,突然张龙慌慌地进来报道:“相爷,吴公公他……”包拯忙道:“他一定是来传旨了,我迎旨。”张龙叫道:“相爷,不是传旨。吴公公暴死在门前了。”包拯大吃一惊:“什么?”他跌跌撞撞地奔出府去。开封府门前,吴明倒毙在台阶上,后背上有一支‘金镖,正好击中心脏。公孙策跟出来,皱紧眉头,低声说一句:“好厉害的身手。”
吴明临死前竟在台阶上写了一句不明不白的话:廿期已到。
公孙策看着这四个字,思索着这四个字的含意。张龙、赵虎一干人正在街上四下追去,但是哪里还有凶手的踪迹。
空空荡荡的大街上,连行人也躲得一干二净了。包拯眉头紧皱,他知道事情越来越复杂了。
就在白玉堂大闹开封府的五天之后,展昭和卢方等人仍在陷空岛等白玉堂。天光已经临近正午,湖边的树林外立着的陷空岛的旗杆,影子正在一点点地缩短。众人的心也在一寸寸地缩紧,他们担心白玉堂不会来,他们实在搞不清白玉堂还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展照苦笑道:“我们几个真个是呆,我们怎么要相信白玉堂这等人物,他说下午在这里见面,实在是耍笑我们了。”
忽听到一声大笑:“众位莫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白某来了。”
众人转身去看,树林里闪出了白玉堂。太阳当空,旗杆的影子正在缩尽。展昭和欧阳春、卢方等人围住了白玉堂。白玉堂看着面前的这几个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心中陡然有些悲伤,刚刚几日,这些人竟会联手来围捕他了。这里边还有与他有过八拜之交的卢方、韩彰、徐庆、蒋平。
白玉堂笑道:“几位既然都来了,一定是准备合力出手拿住白玉堂。只是还要让我先与姓展的动过手,较出一个高低上下。”卢方叹气道:“五弟,你何必负气!本该跟我们一同去开封府见包相爷。”
白玉堂并不理卢方,他只对展昭笑道:“姓展的,这一场麻烦皆因你我而起,你我之间今日就一定要做个了断,我也好领教一下南侠的武功。”
展昭摇头:“万一我失手,江湖上便要少了一条好汉,岂不是遗恨千古?”
白玉堂仰天大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御猫’不必如此,白玉堂死在‘御猫’剑下,也不枉我江湖一场。拔剑吧。”
展昭冷笑:“白玉堂,你大闹开封府,搅闹紫禁城,已经是十恶不赦。你如此狂妄,还晓得自己几斤几两吗?识相些的快快交出相印,在包大人那里你还有些活路。”
白玉堂一声冷笑:“人生在世,若晓得自己几斤几两重,岂不是活得太无趣了吗?人生的乐趣或者就在这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重。休得再说,你若赢了我,我自会交出相印。‘御猫’,拔剑吧。”
展昭不再说,就拔出剑来。剑光杀气立刻布满了四周。白玉堂微微一笑,伸手拔出刀来。刀光闪动,和展昭的剑气搅在了一起,众人被逼得后退几步。
展昭也不禁盯住了白玉堂的刀。这似乎是一口极普通的刀,刀光闪动着淡青色,光芒并不十分强烈,却使空气多了许多肃杀。白玉堂微微笑着,他是不是已经对这一仗充满了胜利的信心?
展昭当然不会相信自己失败,他自出人江湖以来,还没有败在谁的手里。当年他与欧阳春比剑,也只是打了一个平手。他不相信白玉堂会在欧阳春之上。展昭的瞳孔已经在紧缩。刀与剑的光芒在跃动。
白玉堂的刀气突然暴涨,纵横一片,似卷起了漫天的青云。展昭立刻飘起,如青云般飘起。实在不好形容展昭这身姿的飘动,如一段美妙无比的乐曲,没有一点生硬。白玉堂的刀当然落空。
白玉堂称赞一声:“果然好功夫。”又是一刀挥出。这一挥时,已经有了至少三个以上的变化。刀意萧疏,刀式似乎行云流水般滑动。几乎没有一点点杀气,是极温和的刀法,明眼人看出,这刀法中藏有无限杀机。
展昭的脸色陡然变了,他的剑暴烈地刺出。当当作响,是刀剑相接的声音。好烈的剑,好猛的刀。
此时,突然听到有人大喝一声。
众人一愣,只见卢方疾风般拔出刀来,横刀拦在了展昭和白玉堂的中间。
展昭和白玉堂不得不向外跳开。
卢方的劲装已经被白玉堂和展昭的刀剑之气,撕裂了几道口子,有碎布飘落下来。
白玉堂看着卢方,毫无表情。
卢方收起刀,凄然一笑:“贤弟,果真不能不打吗?”
白玉堂摇头道:“怕是不行。”
湖面上的风渐渐变得硬了起来,呼呼地吹着。树林里打着尖厉的口哨。有几只野兔窜出来,慌慌地没进了草丛。
卢方叹口气:“我等奉旨到此,还望贤弟交出相印,让我等带回开封府结案。这样于你于大家都有好处。”
白玉堂摇头:“不行。我跟展昭现在还没有决出输赢,不能就这样把相印交回去,如果你们一定要我交回,你们可以一起动手,把我白玉堂剁为肉酱,再将相印带走,也不失之为上策。”蒋平脸色变了:“贤弟,你不得违抗圣旨啊。”白玉堂冷笑:“我从不认得什么圣旨。”徐庆怒道:“白老五,你休得逞顽。”
张龙怒道:“白玉堂,你不得无礼,卢护卫也算得对你仁至义尽,你若逞匹夫之勇,便将你也拿下。”
白玉堂哼了一声:“你有什么本领?你不过是开封府的一只走狗,在上原桥的酒店里我已经领教过了,酒囊饭袋而已。”
张龙被揭了短,勃然大怒,粗重的眉毛拧成了疙瘩:“你这匹夫还口硬,是你放走了那花……”
卢方拦住张龙,皱眉看着白玉堂:“贤弟,你今日果然不肯给我一个脸面。”
白玉堂笑了:“只是你们不肯给我一个脸面。”
忽听得湖面上有人大喊,众人转眼去看,见一叶小舟正如飞般驶来,不及到岸,舟上的人已经跳上岛来,众人看的清楚,正是赵虎。赵虎气喘吁吁跑来,厉声喊道:“莫要再打!”他在展昭耳边细语了几句,展昭脸色登时变了。
赵虎对欧阳春、丁兆惠、卢方也细语几句。欧阳春、丁兆惠面露憾然的神色。
白玉堂一旁嘿嘿冷笑。
卢方叹道:“玉堂弟,我们今日放过你,下次不可如此。”白玉堂笑道:“如此谢过了。”说罢,挥刀割下白袍,大声说道:“卢护卫、韩护卫、徐护卫、蒋护卫,今日我与姓展的一战不算完结,但我与你们的情分便是断了,日后相遇,我等视为路人,你们便公事公办,不必再尴尬。”他手一扬,一片白袍随风了。
卢方心里一悚,凄然叫道:“贤弟……”
白玉堂摇头:“割袍断义,你们已经没有我这个贤弟了。”说罢,转身去了。
阳光灿灿,白玉堂像一只白色的鸟儿,浴一身金光,飞进了树林。
卢方、韩彰、蒋平面露凄然之色。
徐庆骂道:“卢大哥,莫要伤感,这等人物,绝交了也好。我只是不解,今天如何要放过他呢?”欧阳春道:“或者包大人另有所想。”
展昭道:“此事越来越机巧,我真是不知道应该如何办了。”赵虎道:“包大人告诉大家,白玉堂已经托人将相印交回。”众人如坠五里雾。白玉堂何时将相印交回的?赵虎又道:“包大人传圣上旨意,即日要蒋平进宫听命。”徐庆喜道:“这可好了,四弟进宫去,美女侍奉,好酒享用,真是美事啊。赵虎兄弟,是否也有老徐一份啊。”
赵虎笑道:“你怕是没有这个福气哩。”
蒋平笑道:“徐三哥,几时我做得累了,便推荐你进宫便是。”
徐庆认真起来:“四弟,此话不可食言。”白玉堂又一次进了东京城。他已经知道了颜查散被开封府关押的消息。
但是偌大一个开封府,他不知道颜查散关在哪里。他先在一个客栈住下了,他心情很坏,不能不说他与陷空岛四鼠的断袍绝义对他的伤害很大,他不理解,为什么朝廷给这四个人封一个职位,这人情便是断了。白玉堂喝过几杯闷酒,便自躺下了。刚刚睡着,他忽然听到窗外有细微的响动,他翻身坐宁,刀已经拿到手中。
白玉堂低声笑道:“窗外是哪路朋友,为何不进来说话?”门外嘻嘻笑了。白玉堂一惊,他已经知道来人是谁了。门一推,丁月华进来了,她身后跟着雨墨。白玉堂愣道:“月华姑娘,你如何在这里?”丁月华道:“玉堂兄,你若是寻找关押颜先生的地处,请随我去。”
“你如何知道?”
“这你不必细问。”
白玉堂纳闷道:“丁姑娘,你如何要帮我?我可是展昭的敌人。”
丁月华脸上一红:“你随我去便是了。“说罢,她回身对雨墨道,“你去鱼儿巷后面等我们。”雨墨点点头去了。白玉堂和丁月华悄然出了客栈。
二人直奔了一条胡同。白玉堂心想,若不是丁月华领他来,他是无论如何也不知道这个地方的。二人在一座高墙外停下,就听到有两个巡夜的差人走过来。丁月华待两个差人走近,突然从暗影里跃出,挥剑砍翻了两个差人。白玉堂看到,惊讶了一下,猛然一愣。丁月华悄声说:“进去之后,堂后的房子就是关押颜先生的地方,你放心进去,我在外边接应便是了,只是你要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