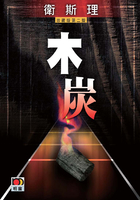铁子眼睛一亮:“那就跟他要钱嘛。”
“那狗日的耍死狗,说他也是个打工的,兜里一分钱也没有,穷得跟叫花子一样。”
“这话哄鬼鬼都不信。”
“我也这么看。你去一趟吧,我看他怕你,你能降住他。”
这时舒芳开口道:“你们一有麻烦事就来找铁子,好像他是如来佛似的。”
老蔫笑道:“铁子就是本事大么。我想找你,可你能办得了这事么?”
一句话把舒芳噎住了。铁子一攥拳头:“走,去工地看看。”
杨玉环本想劝铁子别趟这个浑水,可想到上次为此铁子和她闹翻了,把到口边的话又咽回了肚里,改口说:“你们动动脑子,把拖欠的工钱要回来就好,千万别动手。”
铁子点点头,对老蔫说:“咱们走吧。”
老蔫冲杨玉环一拱手:“谢谢你的酒菜。”
铁子和老蔫来到工地,工地早已停工,一切机械都成了铁疙瘩,六七十个民工懒洋洋的坐在工棚前晒太阳,神情木然。
是时已是下午两点多钟,工地才开午饭。只听杜兴旺吆喝了一声:“开饭喽!”民工们闻声拿着碗筷蜂拥到厨窗前,杜兴旺手执饭勺依次打饭。铁子他们走到近前细看,只见民工碗里,盛着多半碗清汤,飘着能数得清的几根面条和几片菜叶,不见一滴油星。他忍不住问一个认识的民工:“根娃,你们就吃这个?”
叫根娃的民工是个二十刚出头的小伙,他咧着嘴,快要哭的样子:“好我的哥哩,就这一天才给吃两顿。”
这时杜兴旺听到铁子的声音,从厨房探出头来:“铁子哥,到明日格就连这都吃不上了,断顿了,你快帮大伙想想办法。”
民工们都围过来,跟铁子和老蔫七嘴八舌地诉苦。铁子忽然看见根娃身后站着一个孩子,上前问道:“你叫啥名?”
“毛蛋。”
“多大了?”
“十五,吃十六的饭了。”毛蛋长得黑瘦,看上去只有十三四岁,一双眼珠子很黑,骨碌骨碌地转,很是活泛。
铁子说:“你这么大点就出来打工,爹妈就能舍得?”
毛蛋垂下了眼皮,不吭声了。根娃说毛蛋是他侄儿,是他带出来的。铁子肚里来了气,问他:“毛蛋是你的亲侄儿?”
“亲的,一点假都没掺。”
“那你咋就带他出来打工?他还是个娃娃呀!”
根娃哭丧着脸说:“我哥得了胃癌,年前殁了。我嫂子带着小侄儿改嫁了,拉下的三万多元债荒落在了我的头上,我上有老下有小,你说让我咋办呀?”
毛蛋抬起头来:“叔,不怨我二爸,是我自个要来工地的。我爹在世时说,男长十二夺父志。我都十五了,啥活都能干。”
根娃说:“也没让他干啥重活,就是解解水泥袋开开卷扬机。”
铁子默然了。他抚摸着毛蛋的头,好半天,又问:“一天给你多少工钱?”
“十五块。”
“来了几个月?”
“两个月零八天。”
“给你开了多少工钱?”
毛蛋摇头:“一分钱都没给。”
这时一个年过六旬的老汉说:“我来了四个多月,也没拿到一分工钱。来时带了八十元钱早就花光了,家里一家老小眼巴巴等着我拿钱回家过年哩……”说着抱头痛哭。
民工们眼圈都红了。
铁子的脸色变得铁青,牙咬得格格响,转脸问老蔫:“姓林的呢?”
老蔫一指西边的工棚:“刘永昌还在那里跟他磨牙哩。”
铁子疾步朝工棚走去。到了近前,隔窗瞧见刘永昌正在慷慨激昂地讲什么。他们驻了足,侧耳聆听。他们都想听听刘永昌给林头讲些啥。
“你先人是农民吧?”刘永昌在大声质问。
“是农民。”林头回答。
“你知道啥叫农民?”
林头嘟哝说:“农民就是种田的。”
刘永昌训斥道:“不全对,农民的全部定义是:直接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还有,户籍制度中所规定的农民。中国农民都有哪些特点?不知道了吧,我来告诉你。中国农民有以下几个特点:一,从人口数量上来看,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群体;二,从质量上来看,文盲半文盲的数量仍很大;三,从经济地位上看,农民依然起着对社会经济的支撑作用;四,从农民的生活状况来看,农民的生活水平虽然有了显着的提高,但相对水平有所下降……”
老蔫低声道:“永昌给姓林的上政治课哩。”
铁子给他了个眼色,示意他不要吱声,往下听。
刘永昌讲到兴头处,站起了身,一边打着手势,一边侃侃而谈;“中国农民在历史上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关于中国农民的历史地位主要有三种论述。一是民本论。最早见于《尚书》,民惟邦本,本固邦中。就是说民是国本,农民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国家才能稳定发展。第二种观点是依靠论。《汉书》中说,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不管哪朝哪代的统治者都应以老百姓的利益为最高利益,而老百姓以食为天,必须吃饱肚子。中国是农业大国,老百姓者,农民也。你是农民的后人,不给他们发工资,让他们饿肚子,这个问题十分严重。如果不给你饭吃,你能答应么?水可载舟,亦能覆舟。这话你明白么?你手下有六七十号民工,每个民工往少的说,每天给你创造三十块钱的财富,你一天获利两千元左右。一月六万还要多,一年就是七十多万。农民工养肥了你,可你还不知足,黑着心亏农民工,亏你先人也还是农民哩!告诉你,你不要把人逼急了,兔子急了也要咬人。农民工能把你养肥,也能吃了你的骨头!”
铁子听到这里,暗暗叫好。刘永昌不愧是个社会嘴,不知从哪里趸来了这番说词,贩卖给姓林的,可谓恰到好处。但姓林的是个要钱不要脸的主,装傻卖苶,根本没听进耳朵去。他恼怒起来,推门而入,只见林头圪蹴在脚地,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刘永昌可能说干了嘴,正端着杯子大口喝水。从门口卷进的朔风使他们禁不住打了个寒颤。他们几乎同时转过头来,待看清来人时,脸上表情迥异。
“铁子,你来了!我给他上上政治课,好让他开开窍。”刘永昌脸上乐开了花,似乎在绝境中看到了救星。林头却害牙疼似的吸着气,脸上的愁容更是乌云密布。
老蔫说:“你是给牛弹琴哩,白费了半天唾沫。”
铁子走过去,一把抓住林头的衣领,把他拎了起来:“你的良心叫狗吃了!”
林头可怜巴巴地哀求:“你手下留情,请听我说……”
铁子松开了手,林头揉着脖子,喘了口气。铁子的厉害他早就领教过,此时他看见铁子不由得打了个尿战,一张脸皱成了苦瓜:“老板把钱卷跑了,我能有啥办法。他还欠着我十八万哩……”大嘴一咧,呜呜地哭开了。
铁子踢了他屁股一脚:“别跟我来这一套,用尿水子糊弄人!”
林头的哭嚎声更大了:“好我的爷哩,我糊弄谁也不敢糊弄你。我这会死的心都有了。”
“那你咋不去死!”铁子怒不可遏;“你出去看看,民工们吃的是啥?”
“好歹他们还有口吃的,我两天啥都没吃一口。我只是个带工的,说难听点是人家老板手下的一条狗,老板跑了,你们不能拿我当替罪羊呀。”林头说着又嚎开了。
铁子把探询的目光投向刘永昌。刘永昌说:“这两天我把他圈在这里,啥都没给他吃,叫他也尝尝饿肚子的滋味。”
老蔫说:“把这熊早就该饿一饿了。”
林头哀求道:“好歹给我吃一口吧,我装了一肚子凉水,快撑不住了。”
“你等着,我去叫杜兴旺给你提桶涮锅水来。”刘永昌给铁子和老蔫示个眼色,三个人相跟着出了工棚。
铁子问刘永昌:“你看姓林的是装死狗,还是真的是个精鸡(穷光蛋)?”
“他哭得鼻一把泪一把的象是死了亲娘老子,大骂老板骗了他,看样子不象装死狗。你说,谁有头发愿装秃子?这两天我把狗日的也整惨了,他要真格有钱就不可能去受这个罪。除非他把钱看的比命还要紧。”
铁子说:“这事就难办了。不怕他为富不仁,就怕他兜里真的没钆(钱)。”
刘永昌说:“谁说不是呢。我就是没辙了,才让老蔫请你来帮忙。你说这事该咋办?”
铁子双肘抱在胸前,咬着嘴唇,半天不语。老蔫忍不住说:“咱给姓林的再来点硬的,把螺丝再紧一紧,我就不信从骨头里榨不出几两油来!”
铁子说:“现在他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咱把他打死,还得给他偿命。这么饿着他也不是办法,咱得另想法子。”
刘永昌忙问:“想个啥法子?”
“据我所知,姓林的包工也有八九不离十个年头了,我就不信他手中没钱。”
“我摸过他的底,工地的机械大多都是他的,可那些铁疙瘩一时半时又换不成钱。”刘永昌递给铁子、老蔫一根烟。
三人都大口抽着烟,一筹莫展。
忽然,杜兴旺急匆匆地走过来,身后跟着一个中年民工。
“铁子哥!”杜兴旺压低声音说:“有个新情况,不知对你们有没有用。”
“啥情况?”
“有个紫薇花园小区,你们知道么?”
铁子不知道这个小区,扭头看刘永昌。刘永昌说:“我知道,有啥情况?”
“林头常去那里,还是让满囤叔给你说吧。”杜兴旺把中年汉子推到了前面。
满囤说:“我有个侄子在紫薇花园当保安,我去过那里两三次,都看到过林头。”
老蔫嘟哝道:“这是个啥情况?你能去那里他就不能去那里?”
满囤涨红着脸说:“不是这话,我估计那里有他的住处。”
铁子说:“你是说姓林的家在那达?”
“我不敢肯定。”
铁子略一思忖,说:“这话你没对别人说吧?”
“没有。”
“那就不要再对其他人说。你们先忙去吧。”
满囤和杜兴旺走了。没走几步,他们又回来了。满囤说:“还有个情况我差点忘了。”
“啥情况?”铁子问。
“我侄子说,有一回他看见老板和林头在一起,林头把老板叫舅哩。”
刘永昌咬牙骂道:“狗日的给咱上眼药哩。”
铁子以拳击掌:“事情这就好办了。”
刘永昌和老蔫都瞪着眼睛看着他,不知怎么就好办了。铁子压低声音说了一番话,刘永昌咧开嘴笑了:“你把姓林的底给咱摸清,剩下的事就交给我。他给咱耍赖,我也给他耍一回赖。比试一下,看谁的道行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