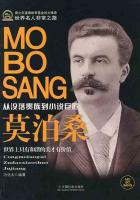也是冤家路窄。当鲁宾斯坦和卡拉进入英国使馆的贵宾大厅时,猛然见到艾密尔·莫林纳斯基父女俩。真是大出意料之外,鲁宾斯坦的“一颗心几乎停滞不动了”。大使夫妇按照罗马习俗,像欢迎一对老朋友到来似的把鲁宾斯坦和卡拉公主分别介绍给了各位来宾,还倍加恭维赞美。艾密尔·莫林纳斯基倒是热诚地跟钢琴家握了握手,妮拉却猛地车转身子,别过脸去,弄得鲁宾斯坦无地自容。那天晚上,鲁宾斯坦自始至终都不太理睬卡拉,但却几乎是逼着妮拉随他走到墙壁的一角。她一脸冰霜,柳眉倒竖地怒视着对方,好容易才从牙齿缝里挤出了一句话:“我跟你没啥好说的。”鲁宾斯坦低声下气,曲意逢迎,再三再四地恳求:“你一定得听我说。明天下午我会去看望你,向你解释一切。你没有什么可以责怪我的。”妮拉朝对方报以怨恨的一笑,但表示第二天可以会见他。不多时,她就跟自己的父亲离去了。因为那晚的上宾是卡拉,所以他不能早退,只能眼睁睁地瞧着伊人远去。返回旅馆时,鲁宾斯坦受到了卡拉的百般嘲弄。卡拉把妮拉蔑称为“小黄毛丫头”、“德国妞儿”。
第二天下午,鲁宾斯坦怀着一颗猛跳的心,叩开了歌剧院近旁的莫林纳斯基的家门,见妮拉孤零零地呆坐在角落里,一声不吭。鲁宾斯坦于是把自己与卡拉之间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个明明白白,最后补充道:“你不难看出,这根本算不上什么爱情了。都好久没有往来,这次在巴黎我又见到了她。我告诉她我爱上了你,要跟你结婚。”经过反复解释,总算换取到了妮拉一丝儿宽慰的笑靥。最后妮拉说话了:
“我怎么能够信任你?人人都对我说你是个见女人就爱的人,我又怎么能够相信你对我的爱呢?还有人说你对女人从来就不真诚,你对人总爱宣扬你准备打一辈子光棍。对这一切我倒可以不去理会,只要你给我写封信也好嘛。像你这种名声的男人,叫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孩子怎么去等呀?”
鲁宾斯坦听了她的这一席话,自然心怀愧疚,惶惑不安。于是,他倾诉了自己的过去和在柏林的那段苦难的岁月,以及无条件地热爱人生的体验最终,博取了妮拉的同情。接着,他又信誓旦旦地表示她是自己“惟一要娶的女人”,为了能使她“过上应有的舒适生活”,所以特地请求她“务必等”他,“千万不要丢弃”他。妮拉不动声色地听着,最后说话了:
“有一位年轻的钢琴家梅西斯洛·孟兹,他也想跟我结婚。他爱我爱得发了狂,爱得死去活来,天天送鲜花,写情书。为了跟我在一起,他连去日本巡回演出的机会也放弃了。我把我爱上你的事告诉了他,当然也如实地表达了不相信你说的要娶我全是一片真心。”
鲁宾斯坦听了大为震惊,坚持要她不能“嫁给一个”她所“不爱的人”。他并且决定次日下午再来看她,因为当天晚上他还有演奏会。
那天晚上的演出“可说是一团糟”,鲁宾斯坦仅是走过场地把全部节目奏完了事,毫无感情注入可言。卡妮·帕拉汀妮公主面无表情地与她在罗马时就十分熟悉的穆勒大使夫妇坐在一起,而妮拉则跟她邻座的女友们窃窃私语,没去注意听台上的演奏。
次日下午,鲁宾斯坦去看望妮拉,气氛也不太顺畅。他再次恳求妮拉等他,还告知了他1929年再去南美的演奏计划,说道:“这趟归来后,我相信就可以结婚了。”鲁宾斯坦此时此刻使出了浑身的解数,讲尽了甜言蜜语,最终使女孩子回心转意,允诺等待。
此后,鲁宾斯坦与卡拉公主一前一后地离开华沙:卡拉独自去了罗马尼亚,鲁宾斯坦则是在她走后的第二天才搭乘火车去布加勒斯特。
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的那场音乐会结束之后,鲁宾斯坦和卡拉一道乘车去雅典。在雅典预演和正式演出的间隙,他们还一道游览了雅典神殿。
接着,他们又一道去了下一站演出地亚历山大港和开罗。在演出的间隙,他们雇了一名向导去游览金字塔。当天晚上,他们俩在下榻地牧羊人大饭店进餐时,与两个来开罗做生意的法国朋友不期而遇。趁卡拉离席的当儿,这两人建议钢琴家去开罗著名的“红灯区”观光溜达。这时,鲁宾斯坦承认自己那“好奇的个性又占了上风”,于是便欣然同往,却坚决不同意带卡拉去。卡拉一时勃然大怒,摔门而走。
在“红灯区”,鲁宾斯坦看到的尽是一些“丑陋不堪的妓女”,表演的也是“最不堪入目的淫秽动作”,令这位钢琴家“一心作呕”。卡拉虽不知情,但对不让她来却耿耿于怀,恨恨不已。两个男女在去布林帝西的船上互不说话。到达该地后,他们也只冷冷地握了一下手,便分道而行:她搭头一班火车去了罗马,鲁宾斯坦则返回了巴黎。
这时的鲁宾斯坦,已对昔日的情人卡拉·帕拉汀妮公主厌恨已极,难以再忍让了。
3情海起波澜
鲁宾斯坦回到巴黎蒙玛特利区拉威南路15号寓所,收到法兰西奥交来的一大捆信件,看到华玛赖特为他安排的法国演出,密契尔安排的英国沿海小城的一些音乐会,桂萨达邀请他去西班牙各地巡回演出,以及意大利圣塔西西里亚等地的演出等。
马不停蹄的巡回演奏对鲁宾斯坦来说,已变成了一种例行公事和自觉行动了。他从恋上妮拉开始,一心只想改变过去那挥金如土的奢侈习惯,诸如购买鲜花送给邀请他晚宴的女主人,添置昂贵的时装和动辄乘坐高价计程车等。他要勤俭节约,改掉大手大脚的毛病,多存一点钱备用。
这时的鲁宾斯坦已变得更多了点人情味,能够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了:他觉得自己的条件并不够理想,比妮拉大上22岁,已是属于父辈的人了;加上本身又不富有,事业上的成就也很有限,还住在巴黎蒙玛特利区的一幢极普通的小木屋里。而从妮拉那一方面来说,追求她的那位情敌、钢琴家梅西斯洛·孟兹倒是“有足够的资格娶妮拉为妻。他可以提供她所需要的一切,而且也只比她大几岁”。论条件,这位孟兹钢琴家也是波兰人,他在鲁宾斯坦发誓永不再去美国的那年到达了纽约。“他在那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当时就使我既羡慕又嫉妒。他在技巧上的日臻成熟,加上肯下苦功,没多久就展现了事业上的辉煌前途,而且无忧无虑。”联系到自己的行为,鲁宾斯坦也自感愧疚,难怪妮拉会生气了,因为她“看见自己要嫁的男人竟跟一个美女一起来到华沙,两个人的情史又早就传开了,加上华沙人又都喜欢说长道短……”
想到这些,鲁宾斯坦就更是缺乏给妮拉写信的勇气,但内心又盼望着她能给自己写信,表示愿意等待,那就太好了。可是,妮拉就硬是没来信,这反倒增强了鲁宾斯坦的决心:一定要把这位姑娘娶到手;一定要搞好西班牙、意大利和南美等地的巡回演出,多赚一点钱来告慰心上人,她绝不会嫁给一个叫花子的。
决心下定,鲁宾斯坦就制定了开源节流计划:1929年去南美阿根廷和巴西等地巡回演奏三个月,同时履行在欧洲各国的演出合约;此外,他还到霍斯曼大道上一家阿根廷的代理银行——大西洋银行开了个存款户头。他从此开始有计划地俭省起来,力争多节约一些钱财。
阔别四年之后,鲁宾斯坦于1928年秋又踏上了巴西的土地。他在里约热内卢、圣保罗、萨尔瓦多、伯尔南布科和其他一些小城市进行了巡回演出。
在里约热内卢,鲁宾斯坦又见到了希托·魏拉—罗伯斯。在巴黎居留多年之后,这位一度穷困潦倒的作曲家,已经以世界著名的巴西音乐大师的名气回到了祖国。他在当时政府的资助下,创办了巴西音乐学院。饮水思源,缘木思本。这位乐坛的后起之秀特以院长的名义,颁赠给鲁宾斯坦以荣誉院士学位。在盛大的颁赠证书的仪式上,魏拉—罗伯斯致以热情的讲话,鲁宾斯坦则用葡萄牙语向他答谢。
在巡回演出到伯尔南布科城,鲁宾斯坦一天坐在咖啡馆中看当地的报纸,突然看到他早年在柏林、华沙两地境遇潦倒时的挚友佛德立克·哈曼死在他的指挥台上。
在结束巴西的演出之后,鲁宾斯坦在里约热内卢的一家银行存下了一大笔钱。
鲁宾斯坦到达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时,立即跟经纪人佛兰西斯哥·茹易兹联系,要求他增加演出次数,提高演出酬金,这个条件大都被接受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蒙得维的亚西城市提供了他计划储蓄的大部分金额。鲁宾斯坦的目标是100万法郎,他认为这笔存款足以使他未来的爱妻过上舒适的生活了。
为此,鲁宾斯坦在每场演出之前,都要勤加练习,力争把演奏会演好。总的说来,这位钢琴家并没有愧对听众,但他的心却不是放在所演奏的乐曲上,而是放在可赚的钱上。这是鲁宾斯坦一生中音乐不是他生命脉搏的惟一特殊时期。每场演出之后,他都要清点赚到的酬金,仔细估算与既定目标的差距。而与此同时,钢琴家在生活上也俭省多了:一日三餐都在小馆子里吃,只偶尔去大饭店改善一下伙食;通常音乐会之后的晚宴也婉言谢绝,宁愿在自己客房里随便吃点儿东西。
在阿根廷首都,有两则不幸消息使鲁宾斯坦悲痛万分:一是关怀自己像儿子般的故总统遗霜曼纽·昆塔纳老夫人去世,享年83岁;二是殷勤好客的米奎·马丁尼斯先生业已破产。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鲁宾斯坦还欣赏了新成立的首都交响乐团的演出,客座指挥为葛利格·费特博格。休息时,鲁宾斯坦去后台看望这位老朋友。费特博格笑着对鲁宾斯坦说:“我要告诉你一则消息,妮拉·莫林纳斯基已经在华沙跟梅西斯洛·孟兹结婚了。我相信你一定会乐意知道的。”
鲁宾斯坦乍闻心上人已经结婚,恍如晴天一霹雳。他当即决定搭下一班海轮返回巴黎。
“妮拉终于结婚了”。这一可怕的意念,始终萦回在鲁宾斯坦的脑际,成为挥之不去的浓重阴影。
“情海失意,赌场丧志”。回到巴黎后,鲁宾斯坦的精神世界似已崩溃,他于是放纵自己,一心醉倒在“赌”字上。当时巴黎附近的杜维尔、白雅丽茨和康城,都是鲁宾斯坦最喜欢去赌博的地方。
谁知出师不利,两场下来,鲁宾斯坦在杜维尔的豪赌竟以输掉50万法郎而告终。他似乎觉得,“这也可以算是送给妮拉的结婚赠礼了。”
1929年整个乐季,鲁宾斯坦继续去各地巡回演出和忙于录制唱片。
墨西哥是这次首站演出地点。自从1919年连创26场音乐会的高纪录后,这里的听众仍然忘不了他。10年期间,这座墨西哥市的发展变化得很快,宽敞的马路上耸立起了石笋般的高楼大厦。听众多半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富有的外籍人士,他们都是到这个石油和矿产资源极端丰富的国家来淘金的。接着,他又去墨西哥的两个新兴工业城市蒙特雷和普韦布拉演出。随后再去哈瓦那演出了两场。
回到巴黎后,鲁宾斯坦已变得心情开朗了许多,平日看戏、练琴,可忙呢。在巴黎期间,他认识了“大人之声”唱片公司的主管海斯·傅立德·盖斯博格,后者让鲁宾斯坦在该公司的录音室里录制了一首肖邦的《船歌》,效果特佳。当海斯将录好的唱片放出时,鲁宾斯坦竟感动得泪水盈眶,因为这正是他孜孜以求的演奏效果。从此,他便开始了一段新的生命——巡回公演与录音室录制唱片相互交叉进行。他在特设的录音室内那孕育着丰富灵感的演奏,已由转盘凝固成永恒的乐声。这样,鲁宾斯坦便同盖斯博格签下了一纸为期五年的合同。
1929年6月,鲁宾斯坦为好友保罗·高占斯基夫妇到达巴黎而举办了一次有七八十人参加的“百美毕备”的露天盛会,除美酒佳肴外,还另加余兴节目,包括表演魔术、玩杂技、乐队伴舞等。宾客之多,盛会之隆,是巴黎艺术界中鲜有的一次,来客中包括名演员布德夫妇、作家尚·柯克图、波兰驻法大使安纳多·穆尔斯坦等等。杜桂大饭店的五人乐队将他们最擅长的孤步、华尔兹、探戈和当时法国最流行的沙瓦舞曲全都抖了出来,一时围观的人好多好多。晚会一直闹到凌晨7时。“这一晚,的确是挥金如土的鲁宾斯坦生活中的一次高潮”。
1929年下半年,鲁宾斯坦有四件事值得一提:
一是友人渥拉德密尔·霍洛维次和贾沙·海费兹先后来到巴黎。鲁宾斯坦后来写道:“霍洛维次表现的方式是毫不犹豫地接受我的款待,而海费兹则热切地接受我提供给他那享受人生的经验。不过两人都以美元为标准,在事业上并不把我放在眼里。”与此同时,鲁宾斯坦也发表了对这两位名噪一时的大明星的看法:“而我却从来都没有妒羡过他们事业上的成就,我认为海费兹是当时受之无愧的最伟大的小提琴家,虽说他的演奏从未感动过我的心;而霍洛维次虽然是第一流的钢琴家,却显然不是一位伟大的音乐家。”在这里,鲁宾斯坦表达了对同时代著名的乐坛同仁那颇具分量的评价。
二是鲁宾斯坦和海费兹参加了由巴黎美术学院举办的一年一度的“古代艺术之夜舞会”。舞会是在举办拳击赛或其他体育活动的巨大华格兰馆中举行,巴黎的全部模特儿、画家和雕刻家都受到邀请并出席了盛会。请看这位“及时行乐”的鲁宾斯坦的两段精彩描绘:
“庞大的馆内挤得水泄不通。中央有一个圆型舞台。许多模特儿美女穿着蝉翼薄衫,裸露出赤条条的胴体。乐队不停地演奏狐步、华尔兹和沙瓦,闹得震天价响。其实毫无意义,因为那一对对的男男女女全然不顾羞耻地紧搂紧贴在一起,根本不去理会舞曲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