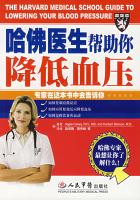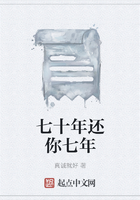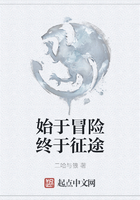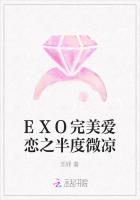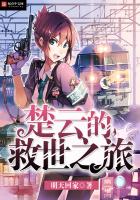老太太说完后继续坐着,而邓的后面却跟着一大批人马,直奔万年寺去了。老太太就觉得这个人不是一般人,就跟着大队人马到了万年寺,“游人”们带着小孩子在喊“邓爷爷好”。老太太知道了是邓小平后,赶紧走近了要给这位大人物磕头,几乎就快要半跪了,旁边中央警卫局的孙勇马上就扶住了老太太。邓小平见状用他那浓浓的四川话说了句“又不是要拜菩萨”。这句话意味深长,尤其是经历了“文革”中的造神运动之后。下跪的时候我也拍了,但是这张底片找不到了。只一天,当天晚上我也归队了,他们也走了。
照片右边的高个子是警卫,邓背后露出半个头的是四川省委书记谭启龙,后面是301医院的护士。整个画面非常自然,绝无摆布痕迹。这幅照片在1978年1980年的全国优秀新闻摄影比赛中获了银奖。
在四川广安的邓小平陈列馆里挂着这幅照片,旁边就是照片中邓穿过的那件白衬衫。澳门的马万祺的儿子马有恒最喜欢这张照片。1984年,邓80大寿时,马有恒要去见邓,给他祝寿。跟我说要送给邓这幅照片看,要我给他放大成24寸,还要请邓签名。我说那好啊,也给我签一份啊。就这样,我放了两张照片,邓也签了两张,一幅在马有恒那里,一幅在我这里。我拍了那么多邓小平照片,只有这张是邓签过名的。
这也是“文革”后杨绍明第一次给邓小平拍照,也是他连续(“文革”前就拍过)拍摄邓小平12年的开篇之作。
说说《邓小平在北戴河》这幅照片。
在深圳市的深南大道上,高高地矗立着一块巨大的广告牌,上面是邓小平语录,一侧是邓小平的巨幅画像。这是国内较早树立邓小平像的城市。多年来,深圳市的市民们每年在节假日时就来到这里,献花拍照,缅怀这位伟人给深圳带来的发展机会。在许多关于邓小平的画册和报刊中,都不难见到这幅照片,它的使用率是如此之高,实在难以统计。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幅照片的作者就是杨绍明。
我是1989年8月22日邓的生日时在北戴河拍的。这两幅使用率极高的照片都是1989年拍的,而这一年也是中国社会的多事之秋。夏天,中国领导人喜欢到北戴河避暑,我们家也去。有一天,我到了第五浴场,更衣室外有栏杆,下面就是海。这是个特殊的地方:“文革”前我曾经在这里给毛主席照过相。那次下雨后有彩虹,很漂亮。我就跟主席说要给他照相,主席说好啊,听你指挥。我就把主席请到这个地方,我那时年轻,自己很紧张,说出来却是“毛伯伯,请您轻松点啊”。结果主席说,我很轻松啊。就在他啊的时候我拍了下来。这张照片后来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用了一个中心夹页,但可惜我现在找不到这张照片了。现在要在这个地方给邓小平拍照,我心里就很开心。那时正好是邓的85大寿,我已经拍过他好几次过生日了。这次说好先照相,后游泳。他有个特点,过生日时特别好说话,子女或工作人员们有什么要求一般都能答应,照个相啦,题个字啦什么的。这次我说您穿得好点吧。他向来对服装不太讲究,而且自从建国以后就没穿过西装,无论多么大的场合,都是中山装。邓楠说:老爷子自在点,把两个指头放在栏杆上……他一放,大家就说真好看。在一家人的导演下,老爷子露出了笑容,我也就拍下了这一瞬间,而且只有一张。从画面上看,他的两个手指在栏杆上,衣服上的叠印很清晰。
说来也巧,另一幅经典照片也是在1989年拍摄的。这就是邓小平的这幅头像。一道轮廓光勾勒出他的脸形,刚刚理过的头发很整齐,暖暖的色调像一幅油画肖像,把邓小平的和善、沧桑和睿智都表现了出来。各种媒体包括许多邮品中都可以看到这幅照片的影子。中央电视台在《百年小平》的电视文献片头上用的就是这幅照片,旁边是邓的名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在一些邮票上,如澳门回归小型张,也是用的这张照片。
那是1989年11月。这一年是中国的多事之秋:六四事件,苏联的戈尔巴乔夫访华,邓小平选定江泽民为接班人……也是这一年,朝鲜领袖金日成秘密访华。中方接待规格之高为近年来少有:邓小平、杨尚昆、江泽民、李鹏等亲赴北京站迎接,邓小平甚至到车厢里迎接。这两个老朋友、铁杆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我的闪光灯也在频频地发亮。
第二天,俩人会谈,没有其他领导人参加,一个小时后休息。钓鱼台18号楼是“总统楼”,光线好极了,他们可能是谈得开心了,金日成到另一边休息,邓小平在靠近窗户的走廊上和别人在说话,表情特好,正是11点左右,我就快速用长镜头拍了下来,只此一张!
这张照片当年发在《中国摄影》上,后来用得就多了。着名的荷兰世界新闻摄影比赛组委会要出一本40周年纪念专辑,就用了这张作品,而且是惟一的中国作品。后来还做成了绢绣,一共就两份,一份在宋庆龄基金会保留,另一份在我这儿。拍这样的照片并非易事。按常规就拍会谈的,握手的,但这些往往大家都能拍到。而人物情绪高潮往往在一些不太正式的场合里出现,这时你要没准备就不行。我后来养成的习惯是,只要这个事件没结束,我就不收机器。有一次,邓小平见戈尔巴乔夫时,本来结束了,我也像大家一样开始收机器,突然有人猛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回头一看是我认识的一个警卫,他说:“你看又握手了!”我没有完全收拾好相机,还有一台在手上,跑过去就闪了一张,结果很成功,取名《第二次握手》,暗喻中苏关系的恢复。因为熟悉,我的“摄影耳目”挺多,他们经常帮助我。
邓小平同志逝世,我们感到非常悲痛,但我们那时远在海南,没能参加邓的追悼会。但那幅遗像是我拍的,当时我也不知道,后来看到媒体上登出后我才知道,是从我拍的一张新闻照片里剪裁出来的。据说印了几千万张,虽然那不是一张理想的肖像。
邓小平是伟人,也是普通人。虽然有了外孙,他也希望有个孙子,在他两儿三女中,邓朴方在“文革”中致残,1985年二儿子邓质方正好在美国生了个儿子。这下老爷子高兴了,在杨绍明拍摄的许多精彩照片里常有这个孙子“小弟”的影子,仅《退下来以后的邓小平》这组四张照片里就有小弟(大名是卓棣)的两张,足见老人家的关爱程度。
我一直奇怪为什么这样好的照片只得了三等奖呢?原来这里还有政治。“荷赛”一直和中国属于不同的意识形态。那一届得一等奖的照片是罗马教皇的,在西方他有着不可替代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二等奖是英国铁娘子撒切尔生活的照片,那年的评委主席是英国人。这组照片送去评选时是198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时间不长,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态度还没有完全改变,这个时候,邓小平代表的中国已经在国际社会中地位逐渐上升,西方社会不得不接受这个崛起的巨人。邓的照片在国际顶级新闻摄影比赛中获奖,本身就说明了问题,至于得几等奖,倒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杨绍明1942年生于延安,12岁时,父亲教他学习照相,在中南海里长大的他就从此以摄影的方式与伟人们开始对话。
我一开始学照相就是拍人物,先拍我父母,然后就拍中南海里的其他领导人。当时中南海有个摄影科,都是新华社摄影部中央新闻组的记者。像侯波,我一有空就向他们请教。高中以后有些照片就拍得不错了,和摄影科的人一起拍,拍完了,他们一看,哎,这张不错啊,给我们“留资”吧,就拿去了。后来新华社来北京四中招摄影记者。我很想报名,但父亲说,你现在还小,文化基础还没打好。你看李讷(毛泽东女儿)就上了北大历史系,你也要考进去。一定要到大学里接受高等教育,摄影将来再学也不晚。我也就听了父母的话,1961年考入北大历史系。我在高中时,就已经留下了领导人的很多生动瞬间,读大学时,可以算得上“准新华社摄影记者”了。上个世纪50年代初邓小平回中央工作后,因为和我父亲都是四川老乡,就经常串门,一起吃川菜,看电影什么的。我趁机拍了不少他的照片,有时候他们家合影,也叫我过去拍。到1966年“文革”开始,我已经在中南海拍了12年。“文革”刚开始,我父亲就被打倒了。江青、康生带领“文革小组”到北大动员学生起来造反。康生挑拨说:中央刚刚打倒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杨尚昆就是你们同学杨绍明的爸爸。我就站在台下,康生一说这句话,我顿时就被学生围起来了……1968年,我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被送到张家口4627部队农场种稻子,整整干了两年。因为身心受到极严重的摧残,1975年,我妈妈李伯钊偏瘫。中央专案组在请示周总理后,同意让我回到父母身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父亲恢复工作,我也得到平反,到新华社广东分社做摄影记者,终于圆了自己的梦。
杨绍明后来进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组任副组长。这个职务有利于他深入对邓的研究,室领导很支持他的工作,因为照片是研究一个人物的重要资料。后来他拿出很大的精力投入到中国摄影界的工作,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连续三届)、世界华人摄影学会会长、当代摄影学会主席。他还是社会活动家,历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副会长、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会长助理、中华慈善总会名誉副会长等,现任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
多年来他活跃在国内国际上各种摄影活动中,搞大型摄影活动,获奖、办展、讲座、出书、搞“民间外交”,为中国摄影走向世界、世界摄影走进中国牵线搭桥,殚精竭虑,无私奉献。1989年邓小平同志专门为杨绍明题的字“无私奉献”,如今还挂在他家的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