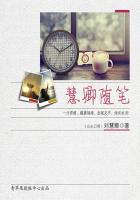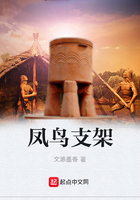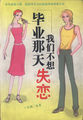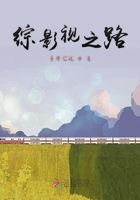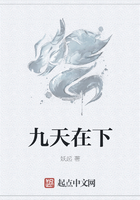是啊,不是共产党引领着华西人走上社会主义,使得华西日富一日,经济强劲地增长,别说“敬老奖”了,能不能过上温饱日子恐怕还很难说哩!三十七万元呀,一次奖质,奖给一家,华西愣是掏得出。我不知在中国,甚或世界,有哪一个地方,有此实力。即便有实力,能否做到?徜徉在华西星罗棋布的景点,我禁不住发出感慨。其实,触景生情,想说的还很多,而吴仁宝亲自为百岁老人程珍妹祝寿,老人直系亲属每人获奖金一万元,三十七人共获奖金三十七万元多,我不再赘言。那就说说华西人的衣食住行,华西人的口袋吧!先来交个底,二〇〇五年华西销售额达三百亿,三百亿是什么概念?一个村庄一年的经济总量大抵接近我国西部的一个省。人均年收入超八千美元。华西村民资产最少的人家有一百万,最多的人家有一千多万。家家有汽车,从捷达、富康、赛欧到奥迪、奔驰、宝马,少者一家一辆,多者一家四辆。户户住进四百五十至六百平方米的欧式别墅。几乎每个家庭都有数码相机、摄像机、液晶电视、等离子电视、电脑、高档红木家具、意大利真皮沙发,中央空调在华西也是屡见不鲜,城里人有的他们都有,城里人没有的,他们也有,国内游、出国游再不稀奇,只要时间安排得过来,手续办好,随时可以出行,纵情祖国山水,饱览世界风光。别的地方办不到的,华西人能办到。为舍?华西人盆满钵满口袋满。
文章中的数字,在般人看来都是枯燥的,可我在上面罗列的数字却是确凿的事实,不带虚头,没有水分,经得起任何人的检验。这里,我要引用我的一位省城朋友的话。他在听了我对华西的介绍后沉吟有晌,说哥们儿,你知道,我最讨厌文学作品中摆弄数字,读它不啻是一种折磨,可是,刚才听了你说出的数字,开始,我有点怀疑,可话从你嘴里说出来,而你又是调査得来的,我不能不信,在我看来,这哪里是一串数字,委实是一行行最美的诗,一幅幅最美的画。”为了印证我的说法,在此,我还可以说一说自己的一次亲身经历:
来到华西的第二天,我应邀住进了村民的家,这是一幢面积六百平方米的欧式别墅,属村里第五代建筑,二〇〇三年建成使用的。同年建成,面积在五百至六百平方米的欧式别墅一共四十幢,二〇〇四年又建了八幢。据说,还会有新的别墅,一幢幢向东延伸,这在华西,算作高档住宅小区。
将红色欧尚直接开进别墅底层的车库。我被引入客厅,客厅的宽敞,装潢的豪华令我惊异,除了面积较城市五星级宾馆的大堂稍小,那种豪迈的气势展露无遗。落座后,我们彼此通报了情况,聊了一阵,主人领我参观起来。别墅有三层,一楼是客厅、车库、大小餐厅,二楼有三间卧室一个书房,三楼有两个卧室,一个棋牌室,一个储藏室。整幢别墅,卫生间就有五个(一楼一个、二楼三个、三楼一个而餐厅、棋牌室、车库,均不在六百平方之内。主人告诉我,入住之前,装潢是村里办的,房款(含装潢)花了一百八十万。这又一次让我惊异。我初步匡算了一下,如此大的面积(含装潢)倘若在城里,至少也得五百万,如在一类地区或许要花七百万巨款才能拿下。而让我第三次惊异的是别墅的主人竟是大学毕业才一年的一对小夫妻。交谈中得知,两人读的是名牌大学的电子系,男的专业是信息,女的专业是声学,同系不同专业,相识、相知、相恋。华西是女的故乡,而男的家却远在湖南娄底,是女的将男的“带回”华西的。男的在华西钢厂工作。
“专业对口,能学以致用,”男孩性格内向,纳纳地说,“有施展的天地,我自然会不断地提升自己。”女的呢?电子声学,在华西用不上,改行在集团公司做会计。
“可惜吗?”我问。
“不,如今是个多元的时代,从事什么职业有多种选择。何况,在大学所学的公共课,作为知识储备,在这里也有用。”说着她莞尔一笑,“会计专业三门课我已通过两门,另一门也快考了,资格证书即将到手,在华西,有我的用武之地。”这是个文静的姑娘,她的话透露出对家乡的由衷热爱。
“你们才工作一年,怎能买得起这幢别墅呢?”我又问。
“靠父母支持,从父亲存在村里的股金中扣。”她半是骄傲半是羞涩地笑了笑,“这是暂时的,我们会自力更生,创造自己的新生活。”瞧,这话说得多好,我真心地为这小两口祝福。
夜晚,我留宿在二楼的一个卧室,窗外是呼晡的寒风,室内却温暧如舂。我知道像这样的别墅,在华西中心村多数村民都住上了,口的父母就住在另外一幢欧式别墅,备有两辆轿车。
就在我离开华西的前一天,告诉我,她的公婆已从娄底迁来华西,跟他们生活在一块。“平时,我上下班是专车接送。我有一辆电瓶车,也骑。他爸妈来了,我将电瓶车给了两位老人。打算最近再买一辆轿车,图个方便。”这就是说,夫妻二人一人一辆。而这在华西已相当普遍。
我不惮麻烦地写了」的故事,读者从中大抵会知道华西村里的富裕程度了吧!华西的社会主义,走的是一条“建村”、“建厂”、“建城”持续发展的道路。
“人民幸福就是社会主义”,吴仁宝的话,道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也是共产党执政的出发点和归结点。它比一些政治家、学者阐述的社会主义概念更能为老百姓所接受、所拥戴。其实,早在十年前,华西村民即已用事实诠释了社会主义的内涵,并用最通俗的语言将其概括为“八有八不”。
“八有”是:
(―)小有教:孩了从幼托到中学全部免费上学,考取大学则有奖励。
(二)老有靠:男五十五岁、女五十岁后,人人都有六匕百元的退休养老金。
(三)房有包:所有村民的住房全都由村里(集体分配。
(四)病有报:大病小病费用全部报销。
(五)物有商:村民购物足不出村,大小商场、超市一应俱全,货物应有尽有。
(六)玩有场:闭路电视、影剧院、公园,设备齐全,尽可享用。
(七)餐有饮:各类档次的饭店餐厅遍布全村,村里为每位村民每年提供三千元的补贴,村民不用自己掏钱,便享口福。
华西农民购买的新轿车。
(八)行有车:村里为每个家庭配置一至二辆轿车,捷达、富康、赛欧,任你享用。
“八不”是:
(一)吃粮不用挑:村里公务人员送粮上门,一家不落。
(二)吃水不用吊:户户用上自来水。
(三)煮饭不用草:煤气管道家家享用。
(四)便桶不用倒:抽水洁具每家必备。
(五)洗澡不用烧:热水管道通往家家户户。
(六)通讯不用跑:户户有电话(全国第一个电话村)。
(七)冷热不用愁:所有村民夏有空调,冬有暧气。
(八)雨天不用淋:万米长廊将全村住宅联为一体。
回过头来看,这切,只不过是小康。而今,华西已达中康,正在奔大康。
吴仁宝马不卸鞍,人不歇脚,高擎着社会主义的大旗,一直走在广大干群的前头。华西的社会主义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华西已成为一处强磁场,吸引着来自国内外的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参观者,给人们以警示,以启迪,以鼓舞。这样的社会主义留给他们什么印象呢?在华西,我看到许多外国朋友的参观感言。这里,我想引用几条,且听他们是怎样说的。
“到这里来参观,确实很荣幸。如果华西能给我一幢房子,马上就来安家,到这里做一个村民。一位刚果将军,二〇〇三年十月“这巳不再是一个乡村,而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了!”(中、日、韩地方政府交流大会考察团村民家中陈设一景,外国友人参观华西,由此可见华西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通过各国的通社传播、幅射到世界各地,从国家政要到一般民众的一名日本成员,二〇〇三年十一月)
“我是从一九七六年开始研究中国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二十五年,华西不仅创造了很多奇迹,而且还有很多感人的故事。美国研究中国的权威专家蓝普敦,二〇〇四年二月)“我也想做华西人,希望在来世。”(英国8汉:广播公司着名主持人罗宾,二〇〇五年三月“我走过很多国家和地方,也见到一些富裕的村庄,但是从来没有看到有哪一个村庄能像华西村这样达到共同富裕的。
对华西也都耳熟能详。难怪韩国前后几任总理听说吴仁宝、吴协东、吴协恩到韩访问,指定要见他们,并且赞赏有加。
金钟泌说:“华西村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了不起,不简单!(一九九九年九月)
李汉东说:“中国华西,大名鼎鼎,很有影响呀!”(二〇〇〇年九月)高健说:华西村,不愧为‘天下第一村’。二〇〇四年四月无需再引述什么,社会主义在华西巳是钢浇铁铸一般。朋友,你也去看看吧!艰苦卓绝创业路五十年,华西创造了一个奇迹,书写了一个神话。然而,它并非一职而就。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充满了曲折与坎坷。吴仁宝的能耐和伟大在于他始终锲而不舍,百折不回,带领乡亲们以他们的勤劳、勇敢和智慧建成了一个令世人瞩目的“乡村的都市”。
华西人走过的道路,乃是一部奋争史和创业史。让我们开启尘封的记忆,翻阅历史的篇章,看看他们是怎样走过来的。
像吴仁宝这样的老一辈农民,可以说,每个人都有一部辛酸的血泪史,他们在生活的底层,过着没有尊严没有温饱的卑微、屈辱、贫困的日子。
吴仁宝原本有个大家庭,父母生育了七个儿子,可是,除他和弟弟兴宝存活,龙宝送给人家外,有四个弟弟死于非命。自小他就在贫病交加的岁月中艰难跋涉,他上山砍柴,下河捕鱼,稚嫩的肩膀挑起生活的重担,想借此来减轻父母的家庭负荷。后来,他又做起小本生意,卖咸菜、豆腐干、萝卜干,贩布、贩鸡、贩红糖……先是在四乡八集进货、兜售,后来,居然跑进周边的城市,远至上海,但家底太薄,又因物价飞涨,在经济危机大潮的裹挟下,他无力支撑,终于两手空空回到家乡,为生活所迫,给富户当起了长工,面朝黄土背朝天,起早摸黑。春华秋实,可他得到的工钱竟填不饱肚皮。
受压迫被剥削的经济地位,使他心有不甘,渴望翻身,渴望有朝一日能拥有自己的土地。“一唱雄鸡天下白”,解放了,他的夙愿很快得到了实现,翻了身,入了党,成了土地的主人,继而当了互助组长,初级社长,高级社长,可以理直气壮地在华西这块土地上施展拳脚了。可是,摆在面前的现实是人均只有几分能耕作的土地。那又是怎样的土地呢?“高的像斗笠顶,低的像浴锅塘”,流传下来的民谣,在贫疮的土地上唱着一曲咏叹调:
高田岗,高田岗,半月不雨苗枯黄。
低田塘,低田塘,一场大雨白茫茫。
旱灾水灾无法抗,农民见了心发慌。
一九六一年,已是人民公社时代,吴仁宝担任华西大队党支部书记,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面貌并没有多大变化。当时,全大队人口六百六十七人,土地面积八百四十五亩,粮食亩产六百八十一斤,集体积累一千七百六十四元,人均分配五十三元,欠债一万五千元。(我们把这些数字一笔不漏地记下来,是告诉人们当年华西的家底,是想给二〇〇五年销售三百亿元,固定资产四十多亿元,人均收入八千美元提供一个参照系数。)而村容村貌又是怎样呢?大队所属十二个自然村,泥垛墙,茅草棚,东倒西歪;羊肠小路,泥泞土路,七拐八折,坎坎坷坷。田块更是七高八低,高低落差竟有一丈二尺……而村民还有无房户,栖息在屋檐下、草垛旁,有的秋后流落他乡,乞讨度日……这就是袓先留下的财富。贫穷的重担沉甸甸地压在我们年轻的党支部书记肩上。那时候,吴仁宝经常独自一人在田头场边、家前屋后转悠,时不时与干部、社员商量,如何才能改变这一穷二白的面貌。政治上翻身已十多个年头,可是,倘若经济上不能翻身,就不是真正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吴仁宝访农家翻身。而眼前最紧迫的是解决温饱。怎么办?
“平整土地,改造山河。”支委中有人精神抖擞地说,“我们有的是力气,人定胜天。”“话是不错,这事迟早得做。”吴仁宝说,“光凭一身力气是不行的,得有钱。拿眼前来说,正逢三年自然灾害,一个个面黄肌瘦,走路都打晃晃,连推磨的力气都没有,还谈得上平整土地?再说,即便勉强上马,钉钯、铁锹、铁镐这些工具靠啥买,不还是要钱嘛!”“对啊!”支委们豁然开朗,不约而同地应道。
而生财之道又在哪里?怎样让社员们从耗时费力的推磨中解脱出来?从华西窘困的实际出发又能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