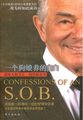《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如此沉重晦暗、粗粝荒寒,处处可见现实生存的残酷与艰难,但又如此诗意优美温情,两种截然相反的观感同时呈现在面前,给人奇异的感受。几乎跳跃在字里行间的温暖与诗意就像漏在树叶缝隙的黄昏的阳光,虽然有些乏力,却仍是撩动人心的。
最关键的因素是塑造了“我”这个细腻、温情、感觉敏锐、诗意盎然的抒情主体形象。小说中的“我”不仅是故事的倾听者,审视者,也是一个讲述者。“我”对魔术师的深情眷恋使“我”沉浸在自己的悲哀里,几乎“我”所见所闻的每一件事情每一种物体都能勾起我的泪水和绵长的思念。相识相知相恋到诀别的过程时断时续地绵延在作品的叙述中。看到寿衣店的花圈联想到魔术师的葬礼上,自己把花圈全都清理出去,因为“有我为他守灵就足够了,我是他唯一的花朵,而他是这朵花唯一的欣赏者。”如此美丽轻灵而又蕴藉凄伤的句子将小说点染得十分诗意。但这些思念并不泛滥,克制而理性。这是小说最打动人心的笔墨。“我”始终在与自我心灵对话,也在与外面的世界对话。小说因为“我”的讲述和倾听而呈现对话性、开放性和多重阐释性。用巴赫金的理论概括为复调的诗学,作者有意让“我”这个陌生人来观察、倾听乌塘无处不在的苦难。
小说中周二夫妻彼此关爱,他们代表了平凡夫妻的温情,他们共同操持着一个平凡但温馨的家,也将爱施诸他人,认孤僻的蒋三生为干儿子,总把他带在身边,对发疯时的蒋百嫂百般劝慰,周二嫂还将那个瘸腿人领回家中,为的是让他睡个好觉,吃顿热饭。还有遭遇母丧父残的云领。同样是小小年龄就经历了人世间至为惨烈的痛苦,他把对母亲的全部思念和爱都寄予在那盏小小的河灯上,正是他带着我在清溪完成了宗教仪式般的祭奠……这些爱和温暖是有超越意义的,它们代表了迟子建一个信念,那就是爱和美一定会战胜恶,人类需要彼此取暖,彼此关爱。小说结尾,“我”随云领去清溪放河灯,在那条似乎与天河接通的小溪上,以一种圣洁的近乎宗教般的仪式完成了对小说中所有魂灵的超度。临睡前出现了超现实的一幕,一只蓝色蝴蝶翩跹而至,绕指起舞,留给读者一点温情的安慰。
死亡并不能斩断生者与逝者之间的联系,无处不在的思念,奄奄一息仍等待主人归来的义犬,有曲无词的哀歌,陈绍纯的魔幻经历,大病一场后会唱哀歌,被强迫吃下记载民歌的纸屑后记住了所有曲调却忘记了歌词,他一唱歌连花猫也会流泪,而我在他的歌声中看见了魔术师。人们对于频繁矿难的理解是阎王爷发怒,亦真亦幻,碧落黄泉与人间联系在一起。写实与神幻联系在一起。
有论者称迟子建这类写作为“别样的底层写作”,是说迟子建作品在描写弱势群体的生存困境,将冷峻当年的事实推向小说叙事的前台,但她仍然在追寻着苦难中人性的光亮。这就使迟子建的底层叙事超越了当前底层写作的“苦难焦虑症”,而获得了独特的审美价值,那就是悲凉中的温情。飞翔在空中凝视这些凡夫庸妇的生活时,迟子建是饱含着悲悯和爱的。
就连陈绍纯的丧歌在“我”听来:“他的歌声一起来,我觉得画店仿佛升起了一轮月亮,刹那间充满了光明。那温柔的悲凉之音如投射到晚秋水面上的月亮,丝丝缕缕都洋溢着深情。”在他的歌声中,“我”如愿以偿看见了魔术师。这是非常温暖的一笔。还有蒋百嫂表面上的放浪和躲在画店外面听歌的眼泪,她的黑夜一样的秘密和巨大的寒凉包裹的生活,都透着对温暖的渴望。还有开旅店的周二嫂,她会出于同情把一个将死的瘸腿人领到家里,为的是让他睡个好觉,吃点热饭菜。而“我”小酒店醉酒时,店主也会送来温暖的话语:“世上没有趟不过去的河,遇事想开点。”
诗意还表现在作品的结构。死亡并不能斩断生者与逝者之间的联系,无处不在的思念,奄奄一息仍等待主人归来的义犬,有曲无词的哀歌,陈绍纯的魔幻经历,大病一场后会唱哀歌,被强迫吃下记载民歌的纸屑后记住了所有曲调却忘记了歌词,他一唱歌连花猫也会流泪,而我在他的歌声中看见了魔术师。人们对于频繁矿难的理解是阎王爷发怒,亦真亦幻,碧落黄泉与人间联系在一起。写实与神幻联系在一起。
迟子建的文字充满诗性和戏剧张力,能把个人悲剧和社会时代紧密结合。同时,更为难得可贵的是,她在苦难中蕴藏了温暖。跳跃在字里行间的温暖与诗意就像漏在树叶缝隙的黄昏的阳光,虽然有些乏力,却仍是撩动人心的。最牵动人心的当然是“我”对魔术师的深情追忆,无论走到哪里,看见什么都会使我想起昔日生活的点点滴滴,情不自禁,拂之还来。但这些思念并不泛滥,克制而理性。
小说中有一个细节被所有论者所忽视,但笔者认为此中大有机锋。“我”在听完陈绍纯的民歌后忆起往昔,在异乡的街头泪流满面。紧接着“我”到歌厅听到了一首温情的《陋巷之春》:“人间有天堂,天堂在陋巷,春光无偏私,布满了温暖网。树上有小鸟,小鸟在歌唱。唱出赞美诗,赞美春浩荡。邻家有少女,当窗晒衣裳,喜气上眉梢,不久要做新娘。春色在陋巷,春天的花朵处处香。我们要鼓掌,欢迎这好春光。”
作家把这首歌全文录了下来,让我觉得有些奇怪,如果仅仅表示温暖的话,有些小题大做的嫌疑。那么是不是另有深意呢?歌词中天堂在陋巷,而现实生活里的乌塘小巷中处处藏着苦难和悲伤,蒋百嫂的悲剧前赴后继,实际上说是地狱并不夸张。歌词中的少女喜气洋洋要做新娘,而现实中那些新娘要么很快做了寡妇,要么兴高采烈地拿着赔偿金走人。小说就写了一个嫁死引发的血案,矿工刘井发发现妻子是来嫁死的,手提利斧砍倒了媒人,自己进了监狱。人心的荒寒直接导致了血淋淋的现实。这样来看这首歌只能让人浑身寒凉,感受现实的荒谬和巨大的反讽。这样作家在貌似不经意间采用了平行叙事的手法,歌曲代表已逝的美好,反衬出现实中精神的荒凉。
小说结尾,“我”随云领去清溪放河灯,在那条似乎与天河接通的小溪上,以一种圣洁的近乎宗教般的仪式完成了对小说中所有魂灵的超度。临睡前出现了超现实的一幕,一只蓝色蝴蝶翩跹而至,绕指起舞,留给读者一点温情的安慰。《亲亲土豆》《踏着月光的行板》《相约怡潇阁》固然写出了贫贱夫妻的艰难,欲望时代情的萎缩,但也以秦山临终前送给妻子的旗袍,王锐夫妻相错火车的一眼,写出了人生的温暖。
从叙事特点上来说,也有点巴赫金小说理论中“对话性”与复调结构的特点。只不过这里的对话是心灵与心灵的对话,是作者与叙述者,作者与读者,作者与作品中的人物以及作者与作者自身的对话,这种对话的精神指归是单边性的,所有的回应都是预设的。这种特殊性也决定了文本复调的单一性。既是复调,也是单一,既是几条线索同时展开,几种声音同时合唱,又是每条线索有始有终,每种声音都有自己的内在秩序。使作品渗透了强烈的思辨色彩。
对从记忆中获得慰藉和归宿的“我”来说,回忆是现实中“我”的自我救赎的方式,回忆的姿态标志着“我”在现实生活中的缺席,而小说结尾,“我”把魔术师的胡须放进河灯让它流向天河,实际上是放下悲伤,从回忆的哀痛中走出来,获得了真正的心灵的宁静。蝴蝶绕指起舞的童话场景即是一种祝福,似乎魔术师欣悦于“我”的转变,化身蝴蝶给予爱的表达。
笔者认为这部作品的最妙处在于它的叙事技法,除了双线并进,互文结构等外,还精湛地采用了那輾、巧合、误会等传统写作技法。
双线并进,互文结构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从“我”遭遇丧夫之痛,独自远行写起,因山体滑坡,列车滞留在一个盛产煤炭和寡妇的小镇乌塘,因而得以听鬼故事、丧歌、嫁死以及诸如此类类似拍案惊奇的故事,目睹无所不在的苦难、黑暗和死亡。
其中“我”遭遇丧夫之痛,对魔术师的追怀成为小说中温情的主线,几乎“我”所见所闻的每一件事情每一种物体都能勾起我的泪水和绵长的思念。“我”们相识相知相恋到诀别的过程就时断时续地绵延在作品的叙述中。
而蒋百嫂的悲剧则是作品的隐线,是“我”东一耳朵西一耳朵有意无意中听来的,这样的寻寻觅觅中给故事罩上了一层神秘,带有古怪传奇的意味。然而迟子建绝对不是对鬼狐之道感兴趣的作家,她是紧贴大地的,及物的,是对现实有着苍凉而清醒的认知的优秀作家。笔者认为她想用这种潜隐叙事表达自己客观克制的写作态度,因为悲剧或者说伤痛如果过于渲染反会被稀释。正是以这种克制理性,迟子建貌似不经意地捡拾起一个又一个存在的悲剧:渴望上大学的卖笤帚的女孩,被民歌改变一生的陈绍纯老人,被无良兽医害死的金秀和她的家,母丧父残的云领,还有那些来嫁死的女人们,她们嫁过来就是为了等自己的矿工丈夫死,以便获得巨额赔偿……浓重的黑暗笼罩着作品,这些底层人群的遭遇不仅仅唤起我们的惊悚和同情,他们也构成了我们生存的背景。这些极为无辜良善的受害者是怎样被改写了人生?又将怎样继续自己的生活?作为作家的迟子建当然找不出答案,所以她选择了离开。
小说以“我”的意识流动和所见所闻结构全篇,“我”的故事和蒋百嫂的故事有着奇特的互文性。她们都遭遇了丧夫之痛,所以当“沉默的冰山”那一章,两个断肠人坐在一起推杯换盏时给人特别的感动。在人世间巨大的伤痛面前,无论对学识渊博的作家还是对矿工的女人,都是一样的惨痛。然而“我”的悲伤在蒋百嫂黑沉沉的秘密面前轻飘如浮云,她的痛才真正无药可救,寒凉彻骨。只要那个冰柜还藏在家中一天,她和她的儿子就一天被囚禁在寒冰里,没有快乐、幸福和未来,看不到丁点希望。
所以“我”逃离了乌塘,来到小说开头提到的三山湖,实现了用泥巴掩盖悲伤的愿望。在这个晶亮清澈的世界里,“我”寻找到了真正的心灵解脱之道。
传统技法“那輾”的运用
那輾是明末清初的金圣叹在点评《西厢记》中提到的一种写作技法,作者正使用的挪輾之法,将这一枯淡窘缩的题材写成一篇灿灿然的文字。那輾是搓那和輾开。搓那就是引出描述的主要对象和问题之后,不立即道明,而是左盘右旋,延缓情事的发展。輾开,就是在写到快要接近矛盾的解决的时候,又故意停顿下来,再远远地宕开去。那輾的主要方法是多重铺垫,曲径通幽:先有一个预设的目标,但不直接去接触它,而是采用陪衬、渲染、烘托的手法,为逐渐接近目标创造条件。
小说共分六章,“魔术师与跛足驴”、“蒋百嫂闹酒馆”、“说鬼的集市”、“失传的民歌”、“沉默的冰山”、“永别于清流”。从“我”渴望去三山湖戴上泥巴面具以掩盖忧伤写起,却立即写到列车滞留乌塘,直到最后一章才又续上三山湖的旅行。文中蒋百嫂的故事显然是写作的重点,但是小说中蒋百嫂却在千呼万唤中很晚才出场。“我”听说乌塘盛产寡妇时决定在这里下车,巧遇蒋百嫂的邻居周二家的和蒋三生,住进了蒋百嫂隔壁,此时用了人物聚焦法,所谓“聚焦”即凸现焦点,给人留下十分清晰的影像。是“一个文本精神所在,文脉所归,意蕴所集之点”,“是文本的最光亮之点。”(杨义:《叙事学》)人物聚焦也就是以主要人物作为刻画的焦点。蒋三生约八九岁,“穿一条膝盖露肉的皱巴巴的蓝布裤子,一件黄白条相间的背心,青黄的脸颊,矮矮的鼻梁,一双豆荚似的细长眼睛透着某种与他年龄不相称的忧郁。”这个孩子的外表清晰展现出他的缺乏照料,暗示着一个悲剧家庭即将出现。
紧接着“我”路遇蒋百嫂家忠心耿耿的狗,因不肯回家,它在等待和迎接蒋百的日子里变得气息恹恹。借用了一对过路的老人的议论:“一年多了,它就这么找啊找的,我看蒋百不回来,它也就熬干油了。哪像蒋百嫂,这一年多,跟了这个又跟那个,听说她前两天又把张大勺领回家了!你说张大勺摞起来没有三块豆腐高,她也看得上!蒋百要是回来,还不得休了她!看来还是狗忠诚啊!”这里巧妙使用了悬念。既为蒋百嫂的出场铺成出神秘的色彩,也写出乌塘人对她的误解诋毁和她处境的艰难。
这才写到“我”在暖肠酒馆遇见醉酒的蒋百嫂,又采用了欲扬先抑的写作技法。蒋百嫂邀“我”一同喝酒,一言不合即掀桌摔碗,撒泼闹事,这同样是为蒋百嫂所隐藏的惊天秘密和她内心深处深重的苦痛做足蓄势。
小说第二章写完蒋百嫂的儿子,她家的狗,蒋百嫂醉酒之后顿住不写了,宕开一笔,写周二带我去集镇听鬼故事。写乌塘浑浊的空气,众多人的生存悲剧,众多的小煤窑,隐藏的腐败,众多卑贱的矿工的生存态势,逗引了读者的阅读兴趣,也曲折了情节。小说就是这样在寻找与追问中层层向前推进,一步步地揭示深刻的主题。这与魏禧说的“说而不说”、刘熙载说的“上意本可接入下意,却偏不入。”是同一内涵。写文章如果直奔主题,没有曲折腾挪变化,就像以木击石,一响之后,便没有了余音,没有艺术感染力。
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悲歌
如果说乌塘人是我们社会缺乏关照的底层,那么生活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鄂温克人更是游逸出了我们的理解之外。他们古老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被现代社会视为原始落后,需要去拯救的。回溯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其实是一部对自然的征服史,人类从自然中获取各种各样的物质和精神的资源以满足自我的生存和发展。随着现代文明的深入发展,人类对自然的掠夺、侵占、控制、改造也逐渐加深,逐渐出现资源匮乏、环境恶化、物种灭绝等自然生态危机。
吴晓东等人认为,后发国家的文学普遍具有“双重的文化和美学特征:一方面是现代性的焦虑,其中交织着对现代性的既追求又疑虑的困惑;另一方面则是在现代性的强大冲击下,面临本土的传统美感日渐丧失所带来的深刻体验和挽歌情怀。”“在中国这样一个后发的民族国家中,挽歌的美必然与一种对现代性的焦虑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双重的文化和历史因素的叠合铸就了审美倾向的复杂性。沉迷在过往的东西中的小说家们一方面获得的是易逝以及丧失的深刻体验,这种挽歌般的怅惘体验中有一种天然的感伤性和抒情性;然而,消逝的并不是全然美好的,乡土中国自有其荒芜肃杀的一面,正像萧红记忆中的呼兰小城既覆盖着温馨也同时覆盖着荒凉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