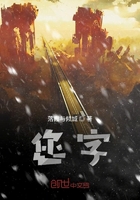乐果道:你别吃着鸭蛋说太平了。
老芳说:真的。
乐果道:你不要,真的舍得?
老芳笑了。有什么不舍得的?这么坏的东西,扔掉也没什么不舍得。
乐果道:你扔哪里,告诉我一声,我去捡。
老芳笑了,道:不用捡也是你的了。
乐果嘻地笑了起来。笑出了声。老芳赶紧拿食指按在嘴上,瞥瞥里间。她不明白乐果怎么会乐成这样了。难道就因为她自己没有小孩?
两个女人蹑手蹑脚到那门口窥探了一下,孩子好像没有听见。
当初生下来,细得跟小树苗似的。老芳说,拿毛线衣比划着。这么小。一点样子也没有,所以给取个名字。
老芳去拿小树小时候的照片。是七个月时候的。一张是光着屁股趴着的,那光溜溜的屁股看着让人恨不得咬它一口。一张是坐着的,露着小鸡鸡。那小鸡鸡似那个样,又不似那个样的。
乐果一愣,戳着小鸡鸡笑了。
老芳也笑了。乐果说,现在这小树要变大树啦。
老芳说,当初自己生小树,是难产。疼得哭天喊地,还是生不下来。医生问孩子他爸,是要大人还是要孩子?他其实想要的是小孩。后来他做那事就证明了这一点。哼,还两个都要!
乐果猛地跳了起来。好像被扎针了似的。男人这东西!她叫,是,他们会两个都要。
老芳道:你信他的!
他们要的是大老婆和小老婆。哼,两个都要!乐果道。我们都不给他!
给小树?老芳没有听明白。
我们呀!乐果道。凭什么他们想要,就要给他们?哼,还都要!都不给!没有他们,我们一样过得很好!
乐果的神情突然变得激愤。老芳很惊讶。她只得反过来缓和气氛。可是生孩子还得需要他们的。说着,她自己先笑了。她难得说这样一句俏皮的话,脸红了起来。
她以为乐果也会跟着笑。不料乐果的情绪更加强烈。没有男人,我自己也能生!她说。几乎是尖叫。
小树从里面出来了。你进去!乐果冲他喊。做你的作业!不要管那些乱七八糟的。要是你也乱七八糟的,看我怎么惩罚你!
老芳很吃惊:乐果老师怎么对学生这样说?
乐果就泡在学校。用领导的话说,爱校如家。
爱校如家只是因为没有家。她喜欢在学生中穿梭。喜欢课间操前在教学楼走廊被学生挤来挤去的感觉。喜欢听广播体操的音乐。那音乐一响,她的脚就禁不住随节奏打起拍子来。那是一种健康向上的音乐。
学生们却不。他们爱听乱七八糟的音乐。那些音乐乱七八糟,如果是从老教师嘴里说出来,情有可源。可是她不老(她还没有生孩子呢)。她喜欢什么音乐?罗大祐?崔健?
难道她真的老了?或是她用老来抵抗着什么?
学生间又流行起了哈韩风。一个学生穿了条超大码的灯笼裤,一甩一甩的。一下子很多男生都穿起了这种裤子。一下课,就一个个在走廊上、操场上摆来摆去,歪门邪气地。其中也有小树。乐果没有想到。她不知道老芳怎么肯给他买这样裤子了。
小树穿上又宽又大的灯笼裤,一下子成熟成大人了。也许是因为他长得高大,帅气。像他的父亲。乐果承认自己对小树好长相总是很不安。
小树一出现,同学们就围着小树转。他得意得腿一蹬一蹬的。那裤管就随着蹬腿一抖一抖的。就有人开始打起了拍子。所有的目光随着节拍、跟着那大裤管转,亮闪闪,湿漉漉。他忽然趴在地上打起了圈。女生们尖声叫了起来。
声音刺进了乐果的耳朵。可这是在课间,他们有权利这么疯。没什么可说的。可是乐果觉得对小树不一样,因为他是小树。
她把小树喝叫过来。她让他不要再穿这裤子。小树不回答。大概是碍着在这么多同学面前,他下不了台。再说,总不能让他现在就把裤子扒了吧?乐果想。我是让你以后不要再穿这裤子了。她又补充说。
我没裤子穿!小树却应道。
边上的人喝彩了。这句话你也可以往下流方面去理解。乐果没料到他会这么说。这是小树,老芳的儿子,也是她的。她绝对有权利征服他。她盯着他。可是他并不看她。好像没有她存在似的。他把头抬得高高的。他的个头比乐果还要高出一点,乐果觉得自己要被他吊起来了。她发觉自己掌握不了他。这棵小树已经霍霍长大了。长成了一棵大树。它要冲破头顶上的天。它的根要把脚下的地顶起来。
她恐惧。你没裤子穿就不要穿!她叫,给我回去,换了再来!
围观者不平了。为什么要换掉嘛?这裤子有什么不好?一个女生叫道。
她扭头瞧了瞧那女生。那女生也一副哈韩打扮。人高人大,胸脯丰满,像一只吃激素饲料长大的鸡。她的脸上还扑了些金闪闪的粉,好像五颜六色的雀斑。好像她已经成熟到了长雀斑的年龄。乐果猛被一扎。
你说什么?乐果道。
有什么不好嘛!女生又说一句。
有什么好?
酷嘛!女生应。
什么酷!乐果道,简直是流氓!
她这么说,自己也觉得不妥。她不知道自己怎么这样说了。在这样的年代。也许真是一种美。她自己不是也曾经喜欢穿牛仔裤吗?可是,她要扑灭美。
大家起哄了。她火了。她索性把小树连同那女生一并抓到了教研组。
她把他们关进教研室里间。然后她把班长找来。她总能从班长那里探听到一些她不知道的消息。班长很会告状。她也知道。她并不欣赏这样的间谍式的学生,但是她还是依靠他,让他当自己的左右手。有时候她觉得自己也够卑劣的。可是她没有办法。这是非常手段。她必须采用非常手段。
班长揭发,小树和那女生在谈恋爱。
乐果一惊。我怎么不知道?怪不得!小树他像吃了豹子胆似的,有恋人在场撑着。她很明白恋爱这东西的魔力的。自己曾经也有过这样的经历。这魔力曾经让她抗拒父母的意愿,跟着嵇康跑到这个城市来,远离父母、家乡。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久远得像一场梦。
她冲进里间。好啊!你们以为我不知道?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事?
两个学生很吃惊。抬头。可又马上低下头,躲避着乐果的目光。
里间没有窗户,他们头顶上亮着一盏白炽灯,照着他们,这使得他们的样子活像罪犯。乐果有点得意,终于镇住了他们。虽然不是在裤子问题上。可是这是个更大的问题,更根本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她甚至发现自己所以去抓裤子问题,是因为冲着这问题的。她有所预感。
她把女生赶了出去,留下小树。她要单独审问。这是她的经验。可是小树什么也不说。怎么问,就是不说。也许他根本没什么可说。并没有什么事。乐果这样希冀着。可是你就开口说你们没有呀。你为什么不开口?他是不肯开口。她简直没有了耐性。
蓦然,她发现小树眼睛迅速往门上一瞥。门外好像有什么响动。她似乎明白了。她为自己这发现而阴险地笑了。她不动声色,悄悄向门口移去。猛地打开门。那女生正贴着门听着。这时,乐果听到小树叫了起来。
他在喊那女生快逃。
乐果顿觉鼻梁上被砸了一下,那么不知所措,无所适从。她是遭到了意想不到的暗击。这使她更加愤怒。她猛地把那女生抓住。她从来没有这么凶。
好啊,她叫,我说呢!原来是有人给你撑腰了呢!原来如此……
女生挣扎,但是没有用。乐果也不知道自己哪来的这么大的力气。那女生衣服上金属扣子崩了,缀饰也撒到地上。那些扎眼的饰物,连同那张脸上的花花绿绿闪闪发光的金属粉,面前这个哪里是女学生,简直是妖怪!妓女!婊子!婊子……
她开始打。打那女生。她的情绪已经超出了教育范围。已经是仇恨。面前这个女人!是的,是一个女人!你看她一身圆滚滚的肉!她忌讳这肉。这肉在闪光。她仇恨闪光。这闪光,就像这都市的夜晚,妓女!
乐果发现自己对妓女有极度的仇恨。那些在阴道一样阴暗的巷道里游荡的女人,那些总是能战胜人家的妻子把男人勾引到自己怀中的女人,那些总是跟不一样男人上床的女人,那些可以在男人面前肆无忌惮叫春的女人,那些可以撒下一切什么也不管的女人,那些潇洒得简直令人羡慕的女人--莫非我在羡慕妓女?
这憎恨,只不过是嫉妒。
所有女人对女人的仇恨,都是对妓女的仇恨;所有对妓女的仇恨,都是嫉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