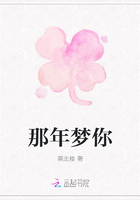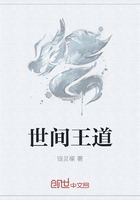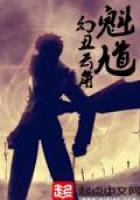代表作:《卧虎藏龙》/《英雄》/《夜宴》/《水乐》/《纸乐》/《垚乐:大地之声》等。
谭盾简介:
1957年出生于长沙,作曲家、指挥家。1978年进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后获硕士学位。1986年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获得音乐艺术博士学位。1999年因歌剧《马可·波罗》获得格莱美作曲大奖。2001年,以电影《卧虎藏龙》配乐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配乐奖”。2007年,在张艺谋导演的歌剧《秦始皇》中任作曲。2008年,为北京奥运会创作徽标Logo音乐和颁奖音乐。2010年担任中国上海世博会全球文化大使。
导语:
谭盾是中国先锋音乐的代表人物。他的音乐跨越了东方与西方、古典与现代。他的水乐、石乐备受争议。他的大胆、狂妄、离经叛道,从湖南到世界,听其乐,寻其来时路。
鬼
湖南人说鬼才指的是除了才能要异于常人,还要充满灵性和创造力。有人把谭盾称为中国最有鬼气的音乐家。他的作品充满了前卫风格。
许戈辉:如果要别人来形容你,你觉得这下面三个词,你更喜欢哪个?人才,天才,鬼才。
谭盾:作为一个湖南人来讲,我可能喜欢鬼才。
许戈辉:对啊,那是一个有鬼气的地方。
谭盾:太对了。我自己常常在梦里寻找我的因素,我也在非常奇遇的感受里边寻找我的灵感。我觉得山是充满了鬼气的地方。湖南有两多,一个是鬼才多,第二个是湘女多情。
1957年,谭盾出生于湖南长沙郊区“丝茅冲”。那里的人们从湘西带过来各种各样民间的音乐,从小在耳闻目睹中成长,儿时的记忆对他未来的音乐之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小时候的他最喜欢的就是追着村里为红白喜事做道场的巫师听他们讲鬼故事。
谭盾:小时候,我们喜欢听鬼故事。那么从鬼故事里面,我们就可以悟到很多很多人与来世、过世的对话,人与动物,人与石头,人与水的对话,那么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一个楚文化的现象。在楚文化和巫文化中间,你就发现,那时候的古人特别鬼气,特别富有艺术的想象力。他们可以把任何一个东西都当成有生命的神灵,他们之间是可以对话的。比如说鸟可以跟风对话,人可以跟石头对话,花儿可以跟蜜蜂对话,这样我觉得艺术就特别有意思。艺术,其实它是一个非真实性的,一种特别特别可贵的思想交流。如果我们活了一辈子,一天到晚只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生命的交流的话,就太可惜了。我觉得要有更多的,比如说有梦,有禅,有鬼,有灵气,让他们有冥想,生命才会有意思。那么湖南人的这种传统文化,其实给了我很多这方面的鬼气的渲染,正是在这种鬼气的渲染里面,我很幸运,我搞了音乐,幸亏我不是搞医学的。
1975年7月,谭盾被下放到长沙望城县黄金公社黄金大队。湘楚文化的博大魅力令谭盾在那几年里不断地受到当地民情民风的艺术滋养。
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招生。此时,正在湖南京剧团担任演奏员的谭盾,带着他那把只有三根弦的小提琴奔赴考场。主考老师叫他拉一段小提琴名曲,他却自作主张拉了一段自己根据湘西的民间音乐创作并命名的《铁牛进山了》。正是凭借这一自创曲目,谭盾顺利地走进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从此,开始了自己的职业音乐创作生涯。
谭盾:古代的竹林七贤之一嵇康,他也觉得是声无哀乐论。声无哀乐,就是声音本身并没有哀乐之分,那么为什么当你听到这个声音会有喜怒的感觉呢?是因为你的心就是这个声音的一面镜子,是因为你自己有感情,有情绪,而这个情绪是通过声音的沟通和传递来折射反映出来。
其实我觉得,听音乐就是说有形而上的,也可以是下里巴人的,都是很美的。我觉得音乐是一种非常冥想的东西,但是同时音乐又非常exciting,是非常非常令人兴奋的一种东西。我的音乐生活其实也是这样的。我特别喜欢听原生态的音乐,我觉得在原生态的音乐中间,会让我自己体会到一种很强烈的感染和力量。同时,我也非常喜欢听爵士乐,也很喜欢听摇滚音乐,我觉得摇滚音乐的节奏和力度,特别适合我。
大学时期,谭盾被誉为中央音乐学院著名的“四大才子”之一,被同学郭文景称作“绝对的天才”。那时的他,认为每一部作品都必须是“一块石头”,激起浪花,方才罢休。
1979年,谭盾的第一部交响乐作品《离骚》,就因使用了鼓、箫等当时被认为是前卫的音响和技术而引起争议。1983年赢得国际作曲大奖(Weberprizein Dresden)的交响曲《风雅颂》,以及1984年举行的“谭盾中国器乐作品专场音乐会”所发表的《天影》、《双阙》等多首曲目,都引起不少批评,并对当时的民乐界产生了震撼。
谭盾:我在北京待了九年,我觉得我是一个极为狂妄的、一个求知欲很强的青年。我觉得我血气方刚,很年轻。我那个时候对于现代思潮,艺术思潮的理解就是要砸烂一切,创新。所以我做《离骚》,我做实验音乐,我做所有这种自我制造的乐器。我要用人类最没有听到过的发声,比如说鼻声、耳声、喉声,还有各种器官的声音来营造咏叹调。我觉得甚至创造的所有的合奏,只有我自己的乐队可以演奏,谱子只有我自己可以看得懂,我觉得这就是创造,这是创举。
水
《地图--寻找消失中的根籁》完整真实地记录下湘西的淳朴民风。这部作品在2003年11月首次亮相于凤凰古城的沱江河畔,三千余名当地居民在现场聆听了谭盾的这场多媒体景观音乐会。
作品创作的灵感取自多年前他前往湘西土家族、苗族、侗族采风的启发,他把“地图”看作一个心理历程的地图、一个文化的地图,还是一个寻找过去与未来、寻找根与前景的地图。
《地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是难得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并支持其在世界巡演。而谭盾的《地图》手稿已被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世界作曲大师手稿廊收藏,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东方作曲家。
我特别喜欢看乡民在河里洗衣服,听他们敲击水的声音。你听--像爵士乐的节奏。在村寨里,音乐无处不在。如果你仔细聆听,立刻就能感觉到一切都是那么生动而多彩。
许戈辉:我发现在你的这些乐章里边,有风、有水、有石、有木,特别是水,我发现你真的对水情有独钟,一定是和童年和故乡有关系吧?
谭盾: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就听到了水,那么第一次听到妈妈肚子里的水的时候,也许正好奠定了你一生中的这个道。可以说,这个道在哪里,其实我们所有人都不知道,正是在你工作的辛勤的努力中间,慢慢地你会去寻找到,体味到这种东西。
湖南有很多我童年的回忆,特别是这里的音乐,这里的人,这里的水,这里的建筑都深深地嵌刻在我的心里,永远也无法抹去,流淌在我的血脉中。小时候在这里,什么东西都在河里面洗,洗澡、洗菜,看着乡下的堂客们洗碗、洗米,都在河里边。当时我总是觉得乐在其中,就是觉得一生中都跟水有关系。后来,到中学的时候就开始被沈从文感动,他总是经常提到水。我觉得我每次读沈从文的,无论是小说集还是散文集,他总是说水使你想到你从哪里来,要去哪里。那么无论是从他的《边城》,或是去他自己的故乡--凤凰,我理解了沈从文为什么总是谈到水,不光是一个生命的源头,也是灵感的源头。对我来说,这是回家,回到家乡,回到我音乐的故乡,回到我灵感的源头。
那么同时呢,我觉得水其实在很多很多文化中间都有这种生命起源的意义。比如说在日本,你要是去研习它的茶道,那么首先你就是要去听它的水的声音,听了水的声音以后,才可以进入它的茶室。听水,他们叫洗心。
我们搞现代音乐的人,做了一段重金属以后,做了一段摇滚乐以后,我们回到家里会听一段莫扎特,我们觉得那是洗心。我觉得在大自然万物中间,如果我们说雷电是摇滚的话,那么清澈的流水、溪声就是莫扎特。
歌剧《茶经》以唐朝为背景,讲述了一个日本王子为寻找陆羽《茶经》,和中国公主相爱的故事。谭盾亲自担任这部歌剧的指挥。
谭盾喜爱水的灵气,《永恒的水》就是由五十多种与水有关的装置来演奏的多媒体协奏曲。其独特的观念音乐也在音乐界内引起了很多的争议。
谭盾:我很多的作品都是从水开始的,比如说这次我们在《少林禅宗·音乐大典》里面,就做了很多很多水的音乐,大部分的水我们都是在嵩山里边去采集水的声音,去聆听这些水的声音,然后把它们录下来,制作成很好的音乐带子。
那么除此之外,我也做很多很多其他的比较大的音乐的水的制作。比如说我们可以把整个上海体育馆整个游泳池都包下来,包下来几天,我们把整个电脑设备和音响设备都运进去,做各种水的声音的分析采样。最开始我到了上海体育馆,请了十几个跳水运动员来。他们一来就说,谭老师,你要我跳什么姿势?我说,不。我说我先请教你们,如果是“嘭”,这是什么样的姿势跳下去,如果是“啪”,如果是“冲”呢?他们说,“嘭”,那一定是跳冰棍;“啪”,一定是背朝水;“冲”,一定是头先入水,然后一个弓字形,“嗡”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突然觉得,其实所有的跳水运动员,他们对水的感觉都非常在意、留心,可能在他们的训练中间,也许他们就是用水的声音去评判他们自己的动作到底好不好,因为他们看不到自己,他们只能是在落水那一瞬间,听到“冲”,或者是“啪”,所以他们用这样的和那样的水的声音判断,来看他自己跳水艺术的精湛或者失误。
正因为这样,我就把所有的跳水运动员拉进来跟我一块儿研究水的形状,水的颜色和水的力度。我们有水下的录音,也有水面上的录音。比如说我们有一段,两个跳水运动员一男一女从十米跳台上,是“嘭”这个声音;然后,“恰”就是三米的跳台上面,两个运动员是用背跳式跳下去;“啪”,就完全是背和屁股同时着地的那个正音,特别好听,就是两个运动员在水上用手打的这种声音。像这样把它们连起来,就正好形成特别美妙的水的节奏。
逆
1986年,谭盾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奖学金,得以进入音乐系攻读博士学位。初到美国,他也在餐馆刷过盘子,也曾走上街头拉琴卖艺。物质生活的艰苦却让他心中的狂野火种却越燃越烈。
到美国之后,谭盾一直在以他的努力来取得西方音乐界的承认。除了奥斯卡奖之外,他还获得过当今世界最权威的格莱美音乐奖。谭盾以他的东方民族音乐,在西方音乐殿堂里,占据了一席之地。1999年《纽约时报》把谭盾评为1998年度“国际乐坛最重要的十位音乐家之一”,而之前就是这份大名鼎鼎的报纸也曾经不接受他的作品,将他彻底否定。
谭盾:到了纽约,我觉得自己很狂妄,因为我觉得我来自中国,我很powerfully、很强大,因为我后面不光有老庄,还有孔孟之道。我的祖先除了发明了指南针等四大发明以外,中国的表演艺术从武功一直到京剧、戏曲,都是最好的。到了那里以后,我觉得我很伟大,我在中国也小有名气,我写了《离骚》,二十岁我就写了《火烧圆明园》的电影音乐,我还是中国第一个得过作曲大奖的作曲家,我当时就好像有点天花乱坠。
置身纽约格林威治村,多元化的国际音乐大环境,给谭盾音乐才能的发展带来了一片新天地。
谭盾:我在那个时候,见了很多西方的前卫艺术家、思潮分子,比如我见到过POP艺术的大师安迪?沃霍,我也见到过约翰?凯奇,美国最伟大的实验音乐的鼻祖,还见过很多很多的诗人。我们也在格林威治村见到非常非常多的共产党员,美国的共产党人。我们也见到过各式各样的人,我觉得纽约是一个超级大学,我在那里学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格林威治村,云集了全世界所有的笨蛋和天才们。那里极端前卫的艺术空气不假思索地裹袭着谭盾,而谭盾心中的音乐种子却在肆意中,复苏出东方古典主义的萌芽。他开始牵挂、反省自己的“中国”元素。飘荡在记忆远处的东方气味总是不自觉地进入他的音乐,那些粗糙的生命力引起了他内心极大的震颤。
谭盾:在纽约学习的过程中,我也碰到很多很多的挫折和困难。首先是文化的歧视。作为一个西方乐评人,西方的音乐家,他觉得中国的文化还属于习俗,它并没有进入西欧艺术的主流,我们这里是贝多芬、莫扎特,我们这里是米开朗琪罗、米罗、罗丹。你们那些花鸟、水墨,那个禅宗、二胡,这是宝贵的民俗。为什么谭盾你一定要用交响乐队奏出琵琶的感觉?一定要把马友友的大提琴奏成有点二胡的感觉?当时是给我泼了一头冷水,其实也影响到我学习的一些过程。
我把在景德镇,在湖南的潼关学到的中国陶瓷音乐和陶瓷艺术的感觉带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课堂。当时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我就跟教授切磋关于陶土的声音是什么。他就说,你能不能跟我讲一点我也懂的东西,我们两个人可以交流的东西,你不要老讲一些你来教我的东西。当然我会被伤害,但是我也觉得,这种挫折和伤害,其实也在慢慢地提醒我。其实我的价值是来源于一个非常非常深厚的文化,我的创作也许不能离开这个东西,我要是跟纽约的这帮前卫分子一样地去砸烂一切,我觉得我就失去了我应该有的优势。因为我来源于一个非常古老的文化,我的职责并不只是创造,我的另外职责是要把养育我的这片土地的文化传遍世界,使其得以再弘扬光大。这个弘扬光大和传遍世界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前卫的理念,因为你必须要用非常非常创新的一些想法,才能实现你自己的理想。正因为这样,我就想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们真正地心服口服地去认同我们的创新,认同我们的古老和传统。
虽然在东西方接受正规的学院派教育,但谭盾更乐于称自己为“象牙塔之外的音乐家”。
从1986年到美国,谭盾一直在尝试将中国音乐元素引入西方交响乐,而当地的乐评界却对此给予了强烈而长期的质疑。著名的《纽约时报》更是将他骂得狗血喷头,甚至恶言相加,说让谭盾一辈子去拉二胡。
然而最让谭盾感到痛苦的不仅仅是别人叫骂,更是自己如何才能从这一片叫骂声中成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