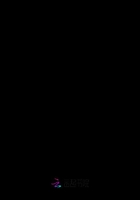护士走开,副师长点了点头,那是喜欢于飞的意思。而后,他闭上眼睛。于飞从他那没有点血色的脸上想到自己的责任,他恨不得火车能像飞机一样一转眼就到后方医院,赶紧进行抢救,他正在默默沉思时,忽然发现副师长又睁幵眼睛,好像缓过一口气。他的苍白的嘴唇在微微蠕动,他在说什么,可是听不见声音,于飞连忙把耳朵贴到嘴边,他听到副师长在说:
“我……这里……不需要什么了……你去吧!”
于飞心如刀绞,悲痛难忍,他真想伏在副师长身上大哭,可是他果断地抑制了自己,他觉得对副师长这样只有别人、没有自己的人给他哪怕一丝安慰,这就是在与生命作着最后一丝挣扎,遵守他的命令。于飞忍着强烈的悲痛,他答应了副师长的要求,站了起来,他放眼四处看了看,他发现:伤员谁也不肯喝,都推着茶缸让给别人,结果弄得这个护士手足无措。这一下惹得于飞怒气冲天,大声喝道:“这不是过雪山草地一你们看咱们缴获了这么多,这是华盛顿白宫送来的,你们不喝谁喝……”可是他这一番话,毫无效应,他愣住了,他知道关键还在副师长,他不喝,谁也不肯喝。
这时,于飞更加敬重副师长,他心中默想:
“就是这样,一个共产党员活要活得合格,死也要死得合格,”他想到他到不了医院了,就是到了医院,抢救也不会有希望,他惟一盼望的就是这一车厢伤员能活过来……“可是,我要做一件人们认为做不到的事,让副师长活到医院,送上手术台……我要是能把我全身的鲜血输给他,只要这个合格的共产党员能活,我身上哪怕吸干血液,又何足为惜……”
他的暴烈的火性,一下变为聪明智慧,他又走到副师长身边坐下来:
“没法子我的任务算完不成了!”
说着他用悲戚的声音,长长地叹了一口长气。
副师长一惊,惺忪地睁开两眼,但眼光是那样没有光泽,但显然向于飞发出关心地询问。
于飞说:“我要不把这些伤员安全送到医院,我还有什么脸再见朝鲜火线上的同志……”
“出了什么事?”
“首长!你带头绝食,谁也不肯张口,这不饿也饿死!”
“我不……是那个意思……让别人多喝一口好。”
“你看我搬来十箱,还不够?”
副师长眼光发亮了,顺着于飞手指看见那一大堆牛奶、饼干。
但副师长伤势最严重,就这一个动作,已使他力不能支,颓然倒下,没有气力地喘着气,喘了好一阵,于飞发现他的嘴唇嚅动,在说什么,他贴上耳朵去听,他听到副师长说:
“我……服从……你的命令,我先喝!”
他这话,使于飞这颗火热的心一下颤动了,落下两滴眼泪,--但他强力地制止了自己,做了一个手势,不久护士就端一碗牛奶递给他,于飞亲自用小勺一勺一勺地送进副师长口中。护士又递过饼干,于飞想了想,他觉得他内脏有伤,怕只能用些流质,就把护士的手推开,还是很吃力、很费劲地一勺一勺慢慢喂着,他看见副师长喉头颤,他知道他是多么痛苦,他不是为了自己性命,而是为了大家的性命,痛苦地吞咽着。于飞知道这样吞下一口,他内脏的伤口要流出多少血,一于飞恨自己怎么这样软弱,这样多情……可是,这关键的一关过了。
所有的伤员一个挨着一个喝下牛奶,有的还吞食了饼干,这使得于飞心上得到一阵温暧。
可就在这时,他忽然打了一个寒噤,原来从敞开的车厢门缝里冷风夹着冷雨吹了进来,扑在于飞身上,愈往北走愈加寒冷,从门缝望出去,还是白刷刷一片霜雪。那个严峻而悲壮的时代啊!刚刚诞生的中国还事事处在萌芽状态,为了提防美国强盗野心发作、突然袭击,猛向新中国打杀过来,像人们所说的:“把婴儿扼死在摇篮里。”靠近鸭绿江这一带的工厂、机关都纷纷向远处转移,因此,后方医院也设在遥远的地方。黑夜沉沉,车轮滚滚,于飞伴着这一车厢的灾难和痛苦,他只恨这黑夜过得太慢、太迟,他立志要把这些个重伤员都完完整整地送到医院。正在他紧抱双膝,坐在车门附近,荒凉的原野上呼啸着、沸腾着,整个天空和地面好像都跟于飞一样急躁、焦灼。正在这时,他忽然觉得有人走近他身边,抬头一看原来是医生,医生只无主地说了一句:
“副师长情况……”,于飞如同触了电一跃而起,抓住医生冷冰冰的双手:
“什么情况?”
医生说:“心速很慢很慢,怕……”
于飞杲断地边拉着医生走边说:
“想尽一切方法,说什么也要送到医院!”
“可是这里有什么方法,有什么方法!”
于飞一听勃然大怒:
“我活着就得让他活着!”
医生的手电筒的雪亮的灯光照着躺在草铺上的伤员。于飞突然发现他们都没睡着,他们都在痛苦的熬煎中,他们都睁着大眼睛,开始于飞责怪自己声音太大惊了他们,但是从那痛苦的眼光中,他忽然想到他们都在等候着天明,火车停在他们应该停的最后一站上,生之欲是多么刚强,多么坚韧!于飞希望大家的刚强、坚毅像地心之火一样燃烧着副师长的生命。可是他走到副师长面前蹲下来,一股冷气立刻袭上心来,副师长脸色像摘下来的菜叶一样,已经没有人色。他轻轻摸了摸心脏,他手指触到的是冰冷的石岩,是几乎觉察不出的搏动。于飞声音很轻,但决定性很大:
“加氧!”
护士嘟囔了一句:“氧气不够了,还有这么多伤员。”
这话一下惹怒了于飞,他猛地抢过氧气筒:
“只要救活他,就是救活全车的伤员。”
他这一点也不合乎逻辑的话,一点也没科学根据的话,却形成一股力量,一切行动都跟他的话声语气转动起来……再看时,医生摸着按在胸口的听诊器,侧脸向于飞点了点头,于飞知道已将消失的生命又找回来了,虽然十分微弱。护士以为他会训她一顿,谁知于飞却天真地对她既是喜悦,又是惨淡地笑了一下,又回到他原来坐的地方抱着双膝坐了下来,可是他坐不下来,他直挺挺地站在那里,但身子随了火车的颠簸而摇动,他一瞬不瞬地伸出手腕,望着夜光表跳跃的秒针,他的心也随了秒针而颤动,他不能十分弄得清楚,他的心情是怎么回事。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不是别人,而首先是他在等待着天明,渴望着天明,只要天一明,一切担心忧虑就消失了,什么都好了!因为据在这条线路上送过两趟伤员的护士说,只要天亮以后就到达目的地了。目的,他在黑暗中搏斗,和什么搏斗,和黑夜,不,和死亡。是的,是死亡,不过,我将胜利,我将胜利。
可是,谁能料到,就在清清的晨曦预示黎明即将到来的时候,他听到一个可怕的声音,这声音那样轻微,可又那样巨大,他分辨了一下才弄清楚,这是人的声音。
医生说:“他不行了!”
“什么?什么不行?”
“你去看看吧!”
他忽然觉得浑身一下子一点力气没有了,他踉踉跄跄跟着医生手电筒那注银色的亮光走去。
果不其然,副师长死了,那青白的脸上连最后一点血色也没有了。于飞伸手摸了一下,脸上像青霜一般冰冷。一个人,一个用大字写的人,在朝鲜火线上一次决定关头,他曾经向战士们挥手,带着他们像怒潮一般朝通红耀眼的战火冲去。在关键时刻,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可是,现在他静静地消失了。
于飞悄悄跟医生说:“不要惊动大家!”
医生明白他的意思,立刻熄灭了电灯。
于飞轻轻地拉起被头遮盖上副师长的面孔。
火车在急速地飞奔,可是车轮呀!你旋转得迟了--点。
于飞向原来站着的车门跟前走去,他蓦然一惊,黎明没有来迟!他张开两臂,把着车厢铁门,他吞着声音,号啕痛哭,他恨自己:“是我没有抓住时间,是我没有抓住时间!”这时的于飞真是五内如焚,肝肠断裂,痛不欲生……车厢里发生了一阵骚动,因为整列车已停在后方医院车站上,但是有三个重伤病号又已经生命垂危。于飞十分严厉,十分急灼,不等车轮停住便飞身跃下。火车像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雪白的烟雾立刻腾空而起笼罩一切。谭漱芬猛然一惊的是这些重伤员,连一点吟呻、一声呼唤都没有,这种庄严的气氛,好像在说:“我们总算跟美国强盗厮杀过了,我们受了伤,可是我们取得胜利!”在有人上车、有人下车的忙忙乱乱中,曹天标师长猛冲冲地从前面跑来,他大声喝道:“先抢救伤员,不动慰问品。”一他俯下身来,对从他身前--抬过的伤员,很温暧地说:“忍一忍!到了就好了!”“忍一忍!到了就好了!”不料一个年轻的伤员伸出紧紧颤抖的两手抓住师长:“丢下班上的同志在炮火里厮杀,我们到了这平静的地方,你忍得下?你忍得下?”说着便号啕大哭起来。
于飞听见哭声便飞快地向这面跑来,一这正是王亚芳以万分痛楚心情从车上看着于飞的那个时刻,一于飞一看痛斥过自己的师长,满面通红,僵硬地站在那里,师长不觉心中发出怒火,大叱一声:“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师长”师长向他投过一阵霍霍眼光,显然是在责怪他:你又怎么能这样对待伤员!指挥担架队的谭漱芬一眼看到于飞,她一下记起,在国内最后那场决战中,他也跟这些伤员一样痛苦地躺在担架上,--他的英俊的面孔,显得那样严峻。她似乎听到他疼痛得骨头缝都在咯咯作声,可是他紧皱双眉,一声不响。谭漱芬对这样的伤员,从心里发出一种好感,她用药棉花堵住他伤口上的流血。他向她看了一眼,觉得有点面熟,便微微一笑。谭漱芬见到副担架旁跟着一个警卫员,知道这是一个指挥员,棉被已经盖着脸,不觉心神一颤,从心里发出颤巍巍的一阵难过,--可是,曹天标、于飞、谭漱芬在这一时间都来不及想什么。谭漱芬向前跑去,为担架队引路向后方医院走去。
于飞他们把伤员交出去,院里的首长递烟送茶,热情招待了一阵,就提出请他们有天大的事也要先休息了再说,那意思绝不只是旅途辛劳,而是对于在朝鲜火线上那日日夜夜,出生入死,不言而喻的安慰。这一行人也实在疲劳不堪。曹天标便大喝一声:“客随主便,睡觉睡觉!”随后他们就被引进有一条长长火炕,上面铺着暖暄暄的被褥的房屋。曹天标是个粗壮肥胖的人,头一落枕就发出很响的鼾声。于飞躺下却怎么也睡不着,师长在火车上的死亡,使他心中总有些凄凉,不过,太阳光从大玻璃上射进来,一这样温暖,这样安宁,对于在朝鲜火线上随时随刻都在钢铁爆烈火蒸腾中度日的于飞,想着,想着,也慢慢睡着了而且睡得踏踏实实,连梦也没有做一个,睡得十分憩适,待他由于一点声动惊醒,心想:“糟糕,我太迟了。”便连忙翻身坐起,看了看手表,已经接近正午,忽然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升上心头,好像有什么重大事件遗忘了似的……什么?我失落了什么?于是一股甜蜜的心情涌上心头,一他想起王亚芳,这怎么会忘了呢?也难怪自从登上火车照料着一车厢重伤号,他的一颗心紧紧的,哪里还顾得上想……其实,他的心整个儿属于她的。现在,已经到了她身边,他真想一把就抓住那欢乐的时刻,他不知道见他最亲爱的人,他的生命,他的心灵,他该说什么呢?可是这一时刻还不能马上到来,待到曹天标起来,他对他那慢慢腾腾,磨磨蹭蹭的劲头,发生了一种焦灼难耐的心情,忍不住噗哧笑了一下。谁知他却忘了横在面前还有一件大事,就是院里首长邀他们去吃午饭。
可能是曹天标的手表忘了上弦,他猛然大喝:
“你们这里开饭这么早?”
“首长同志,我们来看了儿次,你一觉睡了四个小时,而且你那鼾声简直是大海狂涛,真吓人呀!”
“胡说,我从来都不打鼾。”
旁边就有两个人说:
“你不只打鼾,还憋气,我们真担心你一口气喘不过来……”曹天标仰天大笑。
“你们放心,我要死死到朝鲜火线,不会死在这舒舒服服的地方。”
在饭桌上,于飞心猿意马,思绪纷飞。
他多么想立刻看到王亚芳,他想王亚芳对于这意外的会晤,一定是很快乐,很快乐的。可是当他看见曹天标十分豪放地大口吞着红烧的肥肉,吃得痛快淋漓,他忍不住说:
“师长同志,你这一顿红烧肉下去,睡觉时又是一阵响雷。”此言一出,满桌欢腾,谁料由此就引起一个曹天标关于打鼾的笑话。于飞心里一震,糟了,这一说,又不知耽搁多少时间,不知把他和王亚芳的见面推迟何时。曹天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