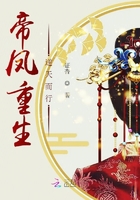这时,王亚芳只觉得全身从内到外都那样软绵绵的,没有一点力气,但她的性格,她的毅力,终于在于飞扶持下,站了起来。
哀乐还在空中回旋。
哀乐还在空中回旋。
金晖那庄严的声音使王亚芳清醒过来。
金晖说:“只有我能送苏雪梅的遗体到火化炉前,作为证明人,你们到一个地方去等候着迎接骨灰盒。”
这时,缕缕而行的中国人、美国人,默默无声地绕过苏雪梅的遗体。这么多怀着正义与同情的人,使司徒南的胆子壮了起来,他感到他们是在这强大人群的保护之中,黑势力也不得不为这威力所震慑,不敢向这儿插手。司徒南决定就近找一家咖啡馆去消磨这段时间。金晖一时一刻不能离开苏雪梅遗体,他也主张王亚芳他们三人暂时离开。哪里晓得刚一出门,于飞的臂膀突然被一只强有力的手掌抓住,司徒南猛然一愣,冲了过去。于飞抬头看时,原来是汤姆森,连忙跟司徒南解释,并为之介绍:
“这是我的老朋友汤姆森博士,这是司徒南先生。”
司徒南跟汤姆森握了手,还是建议:
“我们还是找个地方歇一歇吧!”
汤姆森说:“跟我来,我认识这旁边街道上一家亨泰利酒店的经理,到那里也许方便一些。”
他们到了酒店,找了一个座位坐下。
857风风雨雨太平洋桌上已经点燃一根蜡烛,还在一个小瓶里插着一朵鲜花。一坐下,汤姆森就急不可耐地说了起来:
“事情发生了,我向波士顿打了多次电话,都没人接,在这样灾难的时刻,我这个主人却把客人丢失了,这怎么能行,我给马丁打电话,是玛丽的声音,她说你们赶到洛杉矶来了,我就连忙搭飞机。可是在这茫茫人海中,我不知道你们在哪儿,我跟你们无法联系,我真急得头上直冒烟,这几天不分日夜地到处寻找于飞!你应该给我打一个电话呀!”
于飞怀着深深歉意,但又无可奈何地朝司徒南望了一眼。
司徒南说:“你了解洛杉矶是个什么地方,为了他们的安全,我把他们秘密地藏了起来,要他们断绝一切联系,这样对整个事情比较有利。”
汤姆森理解地点了点头,他从焦灼中缓和下来。
他望了望王亚芳,王亚芳一直沉默不语。她发现汤姆森看,就抽出手把那个小花瓶从她面前推开,苦涩地乞求:
“我请求你,让你的朋友把这朵花拿开好吗?”
这时,她的一颗破碎的心,对于这鲜艳的色彩简直无法协调。
汤姆森做了个手势,一个穿着白衣衫的人过来,汤姆森把花瓶拿给他,挥了挥手,便拿走了。
饧姆森跟司徒南商量:
“我想,在这里停留的时间不会很短,这屋里灯光明亮,我们坐在这大玻璃窗前,也许不很方便,是不是我找这里的经理安排一个僻静的地方?”
这正是司徒南心中所想的,他便点了点头。
“我想那样好些。”
就在这时,王亚芳发出愤怒的声音:“不,就在这里倒下一个中国女人,又坐着一个中国女人,有子弹让他们朝我打吧!”
汤姆森走后不久,带了一个上唇蓄了短胡须的中年人来,汤姆森说:
“这人十分通情达理,这就是拉辛格经理,他一定要来向你们致敬!”拉辛格鞠了一躬,于飞起来跟他握手。拉辛格十分为难地说:“在中国人身上,发生了这样事情,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十分羞愧。”
于飞没有做声,王亚芳什么也说不出来,只由司徒南周旋了一下,那经理便退走了,汤姆森这时才说:
“有一件重要的事,我必须立刻找到你们!”
王亚芳十分肃静地坐在那里,只由于飞跟汤姆森交谈。
汤姆森说:
“程树森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要我想方设法立刻找到你们。”于飞说:“我们处理火化的事,还有向法院起诉的事……”汤姆森十分鋳躇,但只好直截了当地讲出来:
“西蒙,迪尔西已经发动一个大的行动。”
听到迪尔西这个名字,似乎有一股暖气冲到王亚芳心底,这么久她第一次发出声音,她仰起头面对汤姆森问:
“迪尔西……什么行动?”
“她发动了二十五万人向华盛顿大游行,她要求你到最后的大集会上发表讲演。迪尔西不但在黑人中被看作是马丁路德金的继承人,就是在白人中也有很大威望,她要是竞选国会议员,一定能够当选,可是她不屑于把精力浪费到无谓的争论上,她宁愿在哈佛做一个副教授,她面对着苏雪梅悲惨的死亡,她认为做一个正义的美国人是不能沉默的……”
王亚芳挺直了腰板,立刻果断地回答说:
“我有话要说。”
一种炽烈的勇气突破了深深的悲哀,她像从黑夜中看到一颗明亮的光点,她为一个美国黑人的义举感到万分的温暖、鼓舞,她心下叨念着:“我要为苏雪梅说话,我要对美国说话,一定,一定,这是我应该做的,必需做的。”她并没征求于飞的意见,但她感到了于飞的支持。
倒是汤姆森有点犹豫地说:
“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汤姆森博士,这有什么考虑的?你认为我不应该说话吗?”“不是这个意思,这是你应该做的,不过,苏雪梅惨遭黑势力杀害的消息一发表,不但美国,--而且在全世界,舆论一片哗然,当然大都是谴责这种罪行的。迪尔西发动这一大举动,显然是一种正义的行为,不过,你的出现,你的讲话,会在熊熊燃烧的火焰上,冒出更强烈的大火。”
王亚芳淡然笑了一下,说:
“地下的火总是掩埋不着,火终于要爆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要发出声音。汤姆森博士,我想我不会给你添什么麻烦的。”汤姆森习惯地摇了摇头,伸手理了一下卷曲的白发说:
“我真心是同意你的,对于丑恶的暴力,我们有责任进行揭发。这样,我立刻就把你的决定告诉迪尔西、王亚芳!我希望听到你的讲演。”
王亚芳说:“我不想煽动,不想夸张,中国有一句话:事实胜于雄辩!”
王亚芳忽然转身向外说:“你们看!”
她向大玻璃窗外一指,街上泼了浓墨一般的黑夜里,无数人群手上举着蜡烛,烛光在微风中发出熠熠的闪光。汤姆森、司徒南、于飞都为人们的哀悼所感动,星星点点的烛光汇成一片金黄色的海洋,这是人性之光,这是真理之光。
王亚芳站起来向人群招手。
人们发现,这里又出现一个中国女人,便举起手中的蜡烛向她挥舞致敬。
王亚芳郑重地对汤姆森说:
“我相信,这才是洛杉矶真正的面孔。”他们在这儿吃了一顿晚餐,喝了一杯咖啡,王亚芳虽然口中无味,难以下咽,但是饥饿之火燃烧着她的胸膛,特别是得到迪尔西的信息,使她一下信心百倍,奋然而起。
汤姆森焦急地拍了一下于飞的肩膀,看了一眼司徒南说:
“我想,往你那里打电话不方便。”
司徒南的确不愿意把自家的电话号码告诉一个并不熟悉的美国人,因此就没有做声。汤姆森说:“这祥吧!我把我的电话号码写给你。”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记事本,撕下一张纸在上面写了一串阿拉伯字码,递给于飞说:“我要把你太太的决定通知迪尔西,你把苏雪梅的事料理完,跟我联系吧!”说罢他站起身就匆匆走了。
夜晚十时,司徒南用寻呼机和金晖联系,金晖要他们马上到他那里去。王亚芳一下子从悲哀的深渊转入隆重的境界,她迈着急速的步子,在悲哀的洞窟般的屋子里,她发现这里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了。金晖领了她走到一处宽阔的窗口,有一小群美国人聚集在那儿,其中一个捧着一个骨灰匣。王亚芳肝肠痛断,悲心欲绝,全身一阵发热一雪梅!我把你抱回来了……”她用颤抖的双手接过骨灰盒,走上汽车,于飞知道她整个灵魂在颤抖,便从左面搂住她的肩膀,王亚芳把骨灰盒紧紧抱在自己的怀里,一种神圣的感觉笼罩在她的灵魂之中,她很严肃,很郑重,不是悲哀而是亲切。她心中反复说:“我不能把她扔在那冰冷的地方,我终于把她抱回来了。”司徒南开着汽车从大街上缓缓穿过,这时,两边都是人群,有中国人,有美国人,他们和她们手上拿着悼念的蜡烛,不时有人向汽车挥动点点火苗,微微颤抖。可是,王亚芳两只眼睛静静地朝着前面,她似乎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发现,她只觉得苏雪梅站在高高的天穹之上,--她还活着,她还微笑……“雪梅!你有什么话跟我说出来,你的灵魂不会熄灭,我要在你生命消失的美国土地上,大声地呼吁出来,让你的灵魂向全世界闪光。”
林楚楚在她们家的客厅正面墙下,已经安置了一条红木长桌,林楚楚引上王亚芳把骨灰盒端端正正放在长桌当中。
这时,王亚芳一眼瞅见司徒南的老母亲颤巍巍地给两个孙儿扶着,她衰老了,她没有跟谁打招呼,慢慢地一步一步走到苏雪梅骨灰前。王亚芳完全没有料到,这老人竟然要下跪。王亚芳急火火地过去想挡住她,可是她已经跪在地上,老人家双手合拢,说着王亚芳并没有听清楚的话语,但她知道老人家是在祈祷亡灵--对死去的人的尊敬的古老礼节。这在现在的中国已经没有了,而在远隔重洋的海外还保存着,而正是这,成为华人凝聚的强大力量。王亚芳和林楚楚连忙把老人家搀扶起来,走到会客室,老人家坐在红木雕花、铺了金黄锦缎座椅上,王亚芳连忙走到她的身边,老人家伸出颤抖的手臂把王亚芳一把揽在怀里,她说:“这是我一辈子对逝世的人行这样大礼!两个中国人同样的命运,可是她还年轻呀!”这时,王亚芳再也无可忍耐喊了一声:“司徒妈妈!”她一头栽在老人家怀里,这么久这么久憋闷在胸中的悲恸一下倾泻而出,她全身颤抖,失声痛哭。人老了,好像眼泪已经流干,她的干枯的两眼只是闪露着一丝模模糊糊的眼光她拍着王亚芳喃喃地说:“哭吧!尽情地哭吧!眼泪不在美国人面前流,只能在中国自家人面前流!中国人是有骨气的。”司徒南、林楚楚知道老人家勾引起数十年前那场同样的悲恸,他们着急,可又束手无策。
在这难解难分的时刻,还是于飞向前跨上一步,有几分严峻地叫了一声:
“亚芳?不能再折腾老人家了!”
王亚芳立刻打了一个寒战,猛然惊醒,挺起身来:
862长篇小说“司徒妈妈,我不应该……”
“不,孩子!这样大的一个洛杉矶,你不到我这儿,能到哪儿去呢!”
王亚芳有点惭愧,她望了望林楚楚,林楚楚点了点头,她俩内心十分默契,俩人一左一右搀起老人家颤颤巍巍迈着小步,给她们送进卧房,让老人卧在床上,林楚楚轻轻地给老人家拉起一条薄棉被盖上。王亚芳十分内疚地说:
“司徒妈妈,我打搅你了。”
“亚芳!你们折腾了一天半夜,你该歇歇了。”
王亚芳和林楚楚走出门来,王亚芳十分惊恐地望楚楚,楚楚说:
“不会,不会……老人家要是不坚强,也不能带着司徒南度过这漫长的岁月,有今天这份家业。她常常教导我们,不管遇到什么困难,要让外国佬看得起我们中国人。”
林楚楚两眼在会客室里巡视了一下,见司徒南和于飞埋身长沙发上,正在说话,就说:
“亚芳!我送你上楼歇息一下吧!”
王亚芳想了想,点头说:“也好。”
当她们上楼时,王亚芳一蹬一蹬迈着楼梯,才觉得自己全身乏困不堪,可是到了卧室里林楚楚让她躺上床,她却不肯,林楚楚从心眼里同情她,可怜她,王亚芳拉着林楚楚柔软的手掌,十分亲昵地说:
“楚楚!我们一来就把你们家搅乱了,司徒南只管料理苏雪梅的事,连公司也没去。”
“不要紧!我们的妹妹司徒娇是个很能干、很有魄力的人,实际上,司徒南只担任个董事长,司徒娇已经是总经理,她一心扑在事业上。你们来了,她除了陪你们吃了一小会饭,你再看到她的影子没有?人家都说她是女强人,她现在也没办婚事,我看她也不会结婚了。”
与此同时,于飞和司徒南在楼下会客厅里,亲切密谈:
“你累了吧!你为苏雪梅做了很多事。”
“我很兴奋,这样的场面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不过说实在的,我确实有点倦乏,喝一点酒怎么样?”
“最好给我一点威士忌!”
“带冰块的?”
于飞微微一笑,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