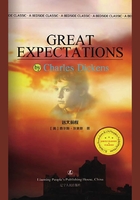吃饭时,王亚芳才看到司徒南原来还保持着中国古老的传统,维护着一个大家庭。当林楚楚引导王亚芳、于飞步入一个四方形宽敞的饭厅,看到一个大的漆木圆桌上面已经坐着一位穿着旗袍,一头银发的老婆婆,不用说这是司徒南的母亲,她身边是一位未到中年的妇女,衣着朴素,但是从面孔上看出在温柔中透出干练神色,经林楚楚介绍这是司徒南的妹妹司徒娇。后来才知道,司徒家这个庞大的企业集团,由司徒南经常奔走世界各国,照料许多家子公司,在美国的总公司,就完全由司徒娇操作运848长篇小说行。她一心扑在事业上,至今没有结婚。王亚芳心下想,这样有魄力的女性,怕不会再陷在家庭琐事,因此,当王亚芳的眼光和司徒美的微笑相逢时,王亚芳很敬佩这有男子气的女人。另外,司徒南有一个女儿,已经出嫁,远在纽约安家,有一个儿子在新泽西州经营着一个下属的工厂。老婆婆另外一边坐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坐的位置就说明受到祖母深深的钟爱孙男、孙女。司徒南夫妇陪着王亚芳、于飞坐在圆桌的另外一面。在迎着餐桌的墙壁上,还供奉着一张朱砂判官,于飞心想连国内已经消失了的风俗习惯,在海外华人中还保存着,中华民族这悠久的古老文化是一种多么强大的凝聚力。地球上的各洲各国,甚至贫困的华侨,这种文化就像一张张开的巨大网络,这就是炎黄子孙的伟大的灵魂。这一顿饭吃得很慢,说话当然都集中在苏雪梅这件事上。王亚芳心情郁悒不大说话,只好由于飞应酬场面。司徒娇在进行到一半时,就放下碗、筷,站起来,很亲切很自如地做了一个手势说:“你们不忙,我有一个活动得先走了。”她特别朝王亚芳点了点头,从神情中看得出他对王亚芳也十分尊敬。她匆匆走出不久,听到汽车轻轻的发动声,显然,他开汽车走了。从司徒南和于飞交谈中,王亚芳知道苏雪梅的后事,已由司徒南亲手作了安排。谈到这里,司徒南向王亚芳投出征询的眼光,王亚芳对于海外骨肉之情十分感动,她只谈了一句话:
“我一定要把骨灰盒抱回去。”
“当然是这样了。于先生,我看你同我一道,找上金铎去奔跑几天吧!”
在这几天里,法医化验苏雪梅的尸体,做了极其繁琐而复杂的“被枪杀”的证明。
王亚芳一个人坐在屋里,她有时很久很久沉默地坐在沙发里,有时在地面上踱来踱去,总有一个念头缠住她不放:“几十年前,在朝鲜东海岸硝烟里进行战斗,现在几十年后,在美国我要进行没有硝烟的战斗……”她好像在向上帝宣誓:“我绝不能把苏雪梅丢在远隔太平洋的异国他乡……”隔一段时间,林楚楚就迈着静悄悄的脚步走了进来,这个温柔的妇女操持着这个大家庭,忙忙碌碌,但出于女性的特殊的同情,她还是到王亚芳这里来看望。她懂得王亚芳心里不好过,她有意地说些闲话将王亚芳从优伤里引开。从她的谈话里,王亚芳才了解到司徒南这份家业,也是经过多少艰难困苦,才挣扎出来的。当王亚芳听到司徒南的父亲在商战中给对手雇了打手,在一个夜晚,趁他们在路上,砰砰、砰砰几声枪响,老人就葬身在鲜红的血泊里了。听到这里,王亚芳吓得瞪大了眼睛:“哎呀!美国在世界上,那样吹嘘它是最民主,最自由,讲究人权,--还时时刻刻用人权制裁别的国家,可是,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竟是这样残酷无情。”“洛杉矶这个在美国除纽约以外,最繁华的第二大都市,可是在灯红酒绿的背后,充满暴力。”“杀人难道这样方便吗?”“美国人人有枪,一这是美国法律允许的。你要看美国的报纸,一种报纸,一大摞,其实上面就是金钱、暴力两个字,我给你拿来,你看看。”王亚芳紧紧握着楚楚的两只手说:“我太需要了,麻烦你赶紧拿给我,我太需要了!”林楚楚除了司徒南交给她保障王亚芳、于飞的安全之外,出于女性之爱,她从她自己内心里想的是怎样安慰王亚芳,想方设法帮助王亚芳度过这一段痛苦的时间。过了一阵,林楚楚提了一提包软盘,她说,“这里面俾存了几十年的各种报纸,你看吧!”楚楚扶着王亚芳的手说:“有不少美国人从报纸上寻觅凶杀案,还是看得津津有味,已经成了嗜好。”王亚芳不禁吐出一句话:“太残酷了!但要看看美国社会的黑暗面,为苏雪梅死因弄个明白。”她把软盘放到计算机里,又从手提包里取出一个笔记簿,一根日本圆珠笔,随后按动操纵键,荧屏亮了,出现了清晰的文字,从这时起她就日夜不停地摘录有用的资料。王亚芳是一个办一件事就要追究到底的人,一这是她的坚韧的性格,这性格在这时像狂骤的风暴把她的灵魂推上九霄云外。于飞和司徒南整天在外面,为了向法院起诉,为了火化遗体,向各处奔走。王亚芳也在奔跑,不过她是用手、用眼、用笔……有时一种恐惧感把她推入极深极深的深渊,在这里她看到邪恶、罪孽、血迹斑斑。林楚楚有时悄悄推开门,想向她送一杯茶,可是她像一尊神圣的石雕,奋笔直书,全身一丝不动,根本听不到开门的声音。林楚楚也不好惊动她,就轻轻掩上门走了。林楚楚很可怜这位北京来的女教授,可是就是在餐厅里吃饭时,王亚芳也是沉默不语。老祖母对王亚芳又是怜爱,又是担心,她就让女儿跟王亚芳换个坐位,招呼王亚芳坐到她身旁的坐位上。这时一种深深的母爱才把王亚芳从沉睡中唤醒过来,她十分抱歉地笑了一下,老人家叹了口气说:
“孩子!不要闷在心里,有话说出来吗!我们在海外不好过呀!你知道他们爷爷《指了指孙男、孙女)的事……”
王亚芳怕老人伤心,连忙伸手堵住这九十几岁老妈妈的嘴巴。王亚芳皱着眉头,像在妈妈面前撒娇的女儿,说:
“都怪我太不礼貌了,我总堵着自己的嘴,不说话!”
老人缺牙短齿的,发出不太清晰的声音:
“我喜欢你……我们家还没来过你这样的女教授!”
“您可不要这样称呼,您叫我亚芳就行了。”
“楚楚!那样行吗?现在世界跟我们年轻时的世界可不一样了。”
林楚楚说:
“行,行,是咱们中国来的亲人嘛!”
老人点了点头,说出下面一段话:
“亚芳!我在美国活了一辈子,看了一辈子,有人说这里是天堂,那是收了人家的钱,给金钱迷昏了脑子的人的混账话。这种人是没良心的人。亚芳!你看我们现在有这一份家业,这是851风风雨雨太平洋(老人用筷子点了点孙男、孙女)他们的爷爷用命换来的。”
林楚楚想用话岔开:“菜凉了……奶奶!”
老人家不听楚楚的话:
“他们的爷爷死得很惨呀!是给白……人……楚楚叫什么来的。”
“白人至上主义。”
“对、对,是这么一伙恶棍,他们看到皮肤上有颜色的人,一就绝不允许你有出头之日……”
人老了,眼眶枯干了,已经挤不出一滴眼泪,可是,王亚芳心里感觉到这老人的内心搁着沉甸甸的一块悲痛,一触动它,她眼里流不出泪,心里流得出血呀!
王亚芳朝着耳聋的老人家大声说:
“奶奶!现在的中国人不是给人做奴才的中国人,我们在全世界已经作为一个强盛的国家站起来,我们决不能让苏雪梅就这样给暴力害死,我要为她赎回这条命……”
老人家伸出颤巍巍的干枯的手扶着王亚芳的手说:
“我看你是一个有志气的人,做人要有志气呀!”
从这一场谈话之后,王亚芳把老人家那块沉甸的悲痛移到自己心上,本来沉痛得就像给刀子剜着一样疼得流血。王亚芳就是王亚芳,她硬下一颗心,一定要给苏雪梅找回一份公平,于是,她又注视着荧屏,迅速地做着摘录。有一天,她从荧屏上真的发现了“白人至上主义”。尽管这是抨击这种邪恶与罪孽的文字,但是一看到这几个字,王亚芳就拍案而起,一人类就这样进步到文明时代了吗?这是愚昧,这是无耻……她用力按闭电钮,熄灭了荧屏。她站了好一阵,然后她在房间里从这一头到那一头走着,一她唤着“雪梅!雪梅……”
不料一个夜晚,她坐着,看着,记着。
已经到了深夜,怎么还不见于飞回来?
这充满暴力凶杀的罪恶深渊,像一片黑漆漆的夜压到王亚芳身上,尽管她极力冷静地压制自己,但她还是有好几次几乎站起来,冲出去找林楚楚探听消息,她很担心,可是刚强的王亚芳随即嘲讽自己:为什么这样软弱?她强力安慰自己,还是凝注双眸在注视,忙碌着两手做摘录,突然使她吃惊的是荧屏上果然出现了“白人至上主义”的字眼。尽管这是抨击的文章,但老夫人的悲惨遭遇,终于得到了明证,摘录完一段话,她停下手,静静地沉思:
“过去只知美国有三X党,好像还在电影上看到从头到底穿着雪白的长袍,只在脸部有两个洞露出穷凶极恶的眼睛,阴森森的令人感到恐怖,这些匪徒专门屠杀黑人,哪里晓得现在又冒出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这是什么主义?这种主义把一切有色人种,当然连中国人都包括在内,正是这种西方帝国主义、这种罪恶的思潮,使得中国一百多年遭受凌辱,遭受杀戮……殖民主义弄得整个地球上到处鲜血淋漓,一希特勒不就是宣扬日耳曼人种是世界上最优越的人种,只有他们应该统治世界,发动了法西斯战争这场人类史上最残暴的大搏斗,亿万人的白骨抛遍田野……这场犯罪的活动过去很久了,现在打在苏雪梅身上的可恨的子弹,不还是这种‘白人至上主义”在作祟吗?一种令人疼痛的力量敲击在王亚芳心灵之上。
为了宇宙的纯洁。
为了人生的公正。
为了自己对苏雪梅的惨死有个交代。
她痛恨。
她悲哀。
她真欲冲进这繁华景象,将所掩盖的罪恶网撕得粉碎。
“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是为真理而战斗的人,为什么不能给人间一片圣洁、干净,一现在我就应该做到这一点!”
王亚芳的内心激烈地颤动着。
正在这时,屋门忽然砰地冲开,她猛然转过头,看见于飞迈着稳定的脚步走进来,尽管他面不改色,镇定自如,但是,王亚芳在一瞥之下,已经感觉到一他疲惫不堪,义愤填膺。王亚芳立刻迎上去,抚摸着于飞的手臂,于飞朝她点了点头,随即又轻蔑地微笑了一下,从这一微笑中,她理解了他向来对丑恶的东西所持有的态度。但于飞强力地抑制自己,说:
“可以打开窗帘了!”
王亚芳莫名其妙,只有“噌”地跑到窗前拉开窗帘。
哎呀!夭已大亮了。
一种怜爰的情愫升上心头,她在长沙发上的于飞身旁坐下,非常惊讶地问:
“你们折腾了一夜啊?”
“幸亏你没去,--亚芳!那不是人去的地方呀!”
王亚芳连忙走去想给于飞倒一杯水喝,这时,她听到于飞严厉地吐出一个字:
“酒!”
王亚芳体贴地觉察出于飞内心如火烧,需要冷却。
她往杯子里倒了浅浅一点威士忌,又从冰箱里夹了好几块冰块投在酒中。
于飞浅浅地喝了儿口,他渐渐冷静下来了。
“他们对死了的人还要进行各种折磨。”
“于飞,苏雪梅怎么样了?”王亚芳睁大了眼睛,她脸颊上动手术留下的像细线一样的伤痕微微颤抖了一下。她相信一定生了什么特别可恨的事情,否则久经战火锤炼的于飞是不会如此愤慨的。
于飞呷着酒,慢慢缓和下来,他说:
妇854长篇小说“你知道,司密特公布了凶杀现场的录像,黑势力对他是不会轻饶的,甚至司法当局为了遮盖美国的形象,也会在他身上做些手脚,--但是他已是打官司的人证、物证。电视台发布的录像,是从他那转录的,原始的录像还掌握在司密特手上,金晖用尽千方百计,跟司密特取得联系。司密特带上原始的录像带到一个咖啡馆里会了面,金晖说明形势的严峻,必须把他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马密特倒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他宁愿坐在家中等候一切祸害,而且他这样做更合乎他的人格。亚芳!我们到来,被害者的代理人已经来了,这消息已经传遍洛杉矶。这反映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面的是有人能挺身而出,为苏雪梅申冤抱屈了,反面的是黑势力帮伙力图消赃灭迹,也要把枪口对准你。”王亚芳听到这里勃然大怒,站了起来。
“我不怕,让他们打吧!我跟苏雪梅一道走,看美国人在世界面前怎么交代!”
于飞看到王亚芳倔强的个性,又像火一样爆发起来。她巍然挺立,她是一个战士。
于飞:“亚芳!最主要的是为雪梅打赢这场官司。”
王亚芳气昂昂地喝道:“这就是美国的人权!”
“是呀!这个社会复杂呀!司徒南为了保护我们专门找了一辆防弹汽车。”
柔软的感情升上王亚芳心灵,她说:
“司徒南……难得呀!”
于飞继续说下去,“我和司徒南按照金晖的布置到达那个咖啡屋里,加入谈判,最后我向司密特说:‘我代表我的太太,她已经得到苏雪梅父母的委托,来到洛杉矶向法院起诉,我们绝对地需要你在审判时说明真相。为了苏雪梅,我和我太太恳求你暂时隐蔽一下你知道黑暗势力是无孔不入、无恶不作的,我想你会同情一个中国女性的愿望的。”亚芳!我用你打动了司密特,我们出了咖啡馆上了防弹汽车,一我真没想到汽车要奔走那么长久的时间,不知走了多少路途,这时我才知道洛杉矶是分成多少块构成这个大城市总体,一我们到了离开这个市中心很远很远的地方。司徒南告诉我这里是以华人为主的居住区,司密特能够受到保护。为了安置司密特,我们奔跑了一个白天。金晖真是一个极其聪明、雄辩的能手,下一步就是力争,按中国礼仪近期对苏雪梅进行火葬,不让他们在这已经死亡了的人身上找麻烦。”
王亚芳沉默无言,用两手捂着面颊,她心里反复吟诵着一句话:“我要向你最后诀别!我要向你最后诀别!”然后,缓缓抬起头向于飞投去十分忧伤的眼光,她怕说,但还是说出来了。
“那么……我还能再见雪梅一面。”
“我想这是理所当然的。”
这个理所当然的时刻,过了若干天后,一个将近黄昏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司徒南开着那辆防弹汽车,十分小心地绕了几条小街才到达目的地。
当王亚芳一步迈进那像冰窟一样清冷如霜的房子,一神苦恸的激情便从心底一下涌了上来。这时哀乐一像哭泣的声音,那样伤感又那样庄严地在飞旋回荡,这是一个灵魂向人世间永远告别的声音;这是另一个灵魂向这个苦涩的灵魂告别的声音。这时,王亚芳再也无可忍耐,她匆匆向停着苏雪梅尸体的木台奔过去,她大声地喊叫:
“雪梅!”
“雪梅!”
她的声音是那样凄厉,那样哀痛,使得挤在门口的好些个女人刷地流下眼泪。她心如刀绞,一下昏迷过去,于飞抢上一步把她抱着。王亚芳顽强地喘息一下,睁开两只大眼睛,她踉踉跄跄又走向苏雪梅,她看到苏雪梅只是安详地睡着了。她的脸色虽然雪白,但还是那样娇嫩。王亚芳亲昵地对她说:“雪梅!我来了!”她把自己的脸亲密地贴在那既冰冷而又酥软的苏雪梅的脸上,一再没有发出声音,但她的眼泪像瀑布一样纷纷洒了下来,她好半天抬不起身子来,悲恸欲绝,还是于飞在她的耳边轻轻说:
“很多人来向苏雪梅告别,都挤在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