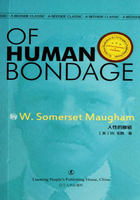表姐不由给了我一个充满喜悦的赞赏目光。我带着五分眩晕,三分迷醉,两分愧疚,跟着桑家榆上了车。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坐到飘窗上,手里捏着那个打火机,轻轻地抚摸着。已是凌晨两三点,夜阑人静,月光流泻,只有一两声江上的汽笛声传过来,所有的声音都在这夜色里沉睡了。
我颤抖着用那只打火机点了支烟,并不吸,只闻着那淡淡的香烟味道。那燃烧着的、很快暗下去的烟头上升起一丝袅娜的烟雾,就像我此刻的心境和思念。
楼下一个忽明忽暗的亮光吸引了我,我探身看去,就在我的窗下,一个男人靠在车子的引擎盖上抽烟。车灯未开,我看不清他的模样,但他有着和桑家榆一样清瘦的身影。
我的思念和这夜色一样,浓得化不开了。
我想了想,给他写了条短信:可惜吗?手机正紧张地传送,我突然意识到这样不妥,赶紧使劲按取消键。也不知道是没有取消掉,还是真正的巧合,桑家榆给我回了条短信:
我能上来坐坐吗?
我惊讶地朝窗下看去,他在月色朦胧中朝我挥了挥手中的手机。
我连忙回复:欢迎——只有两个字,连标点也没有,多余的什么都来不及……
十七、晚礼服背后的手
旅游学院的酒会设在龟山电视塔的旋转餐厅里,离丁霁心自己住的武昌也不远,但她却偏要来我住的地方化妆,好在她自己轻车熟路,很快就可以搞定。
今天学院给她准备了三套衣服,开场时是一件暗绿绣花的软缎旗袍,第二件是一套职业套装,第三件是一件很清凉的低胸露背晚礼服。
我一直在旁边看她化妆,看她给自己本来白皙光泽的脸施上薄粉,然后描出眉毛,眉梢稍稍一挑,便是一副楚楚动人的模样。接着,她熟练地给自己画上眼线、贴上假睫毛、刷好睫毛膏,那眼珠就更加乌溜溜、水滴滴了,她在镜子里偏头对我笑了笑,顿时让满屋子都涌动着笙歌曼舞了。
“好一个美人微笑转星眸啊!——今天又想要迷倒谁呢?”
“所有帅哥!”她躬着身子,又向镜子前凑了凑,两笔就勾画好唇线,然后嘟着自己性感的嘴唇,在上面涂上靓丽的唇彩,毫不含糊地回答。
看她化完妆,我拿了本书在旁边坐着,心不在焉地翻着。
“那份工作,你真不打算做了?”她在穿衣镜前拿着衣服在身上比试着,检查着、调整着妆容,一边问我。
“是啊,他也没有发邮件过来了啊。再说,一个人在你面前说了他最隐秘的事情,你若没有成为他最亲密的朋友,便永远失去了他。”
“为什么?怎么突然说这么高深的话?”丁霁心又拿着首饰和衣服比画着,“你过来帮一下忙吧,帮我把衣服拿着,我来看看首饰配不配。”
“他看到你就会想起自己的隐痛,你出现在他面前就是提醒他自己的伤痛。他会越来越不想看见你。”
“这个晚礼服又露背又低胸……”她盯着镜子中的衣服,撅起嘴来摇了摇头,“首饰又太小气,撑不起这件衣服啊!
“唉,我又没有那么大的首饰!”丁霁心一边爱惜地抚摸着那件晚礼服,一边和我说话,她拿起自己唯一的一件铂金项链,放在胸口比了比,的确是太小了。
“这件衣服这么清凉,不便宜吧?”我拉着衣服看了看,这件晚礼服前面挖得很下,后背全部镂空,只有两根极细的带子和前胸那两片连在一起,下面倒是袅袅娜娜到了脚下。
“当然,书商赞助的,现在的衣服,布料越少越贵。”说着,她从首饰盒中挑出了一串玛瑙项链,这串项链非常漂亮,玛瑙的成色也很好,红润透泽,是一个和她同姓的玉石鉴定专家送给她的,她非常珍爱,平日里经常挂在脖子上。
“可是,这个配晚礼服不太搭吧?”
“也是,颜色不搭。”
“没有别的首饰了。”丁霁心边说边在首饰箱里挑挑拣拣。只见她打开一个长方形的小盒,里面尽是些闪亮的水钻。她又找出一根白色的丝线,用打火机烧了烧,然后把线头捻细,一颗一颗地穿起水钻来。她十指尖尖,穿得非常快,看得我都入迷了,那些亮晶晶的水钻在她的调理下像听话似的排成各种形状。不一会儿,一串光芒四射的钻石项链闪耀登场了。
“好漂亮!”我不由得赞叹。
“漂亮是漂亮,可是……你不觉得这样重大的酒会戴这样山寨的首饰很讽刺吗?”我又有点儿疑惑。
“越是重大的酒会,佩戴的越是山寨版的首饰。有谁肯将真首饰戴上去?”丁霁心肯定地说。
“穿衣服配首饰,主要在乎个人的感觉。如果你有足够的信心征服这件衣服,并用笑容告诉所有人:我穿的是最华丽的衣服、戴的是最华贵的首饰,其他人也会产生同样的想法,你的人和衣服会交相辉映。反之,如果你畏畏缩缩,不够自信、不够大气,征服不了衣服,那么你穿上再华丽的衣服、戴上再昂贵的首饰,也不过是一个撑不起衣服的衣架。”
丁霁心的这番话在酒会上得到了证实。
五点半我们开车上了龟山,丁霁心去后台准备,我就在旋转餐厅里转悠。
餐厅地势很高,而且夜色未至,正好可以俯瞰武汉三镇的美景。窗外像一幅绵延不绝流动的画面,长江汉江在这里交汇,蛇山龟山隔江相望。窗外三分之一是鳞次栉比的高楼,而画面的七分则被天空占据。响晴的夏天的傍晚,东、南、北三方天空湛蓝深邃,大朵大朵蓬松而洁白的云彩在天空飘浮着。而西面的天空被大片大片金光闪闪的晚霞包裹着。太阳向下飞坠,云彩因为太阳的运动而闪现出不同的色彩和形状。
我正在神游间,音乐响起来,我们的丁霁心盛装登场了。
一件暗绿色的高领绣花旗袍,把丁霁心的身段挤掐得玲珑有致,她简单地盘了个髻,配着翡翠耳坠和翠玉手镯,显得雍容华贵而不失女性的妩媚。她和另一位男主持一起简短地介绍了学院的历史、人文特色、办学方向和今天揭牌的图书馆。
一个宣传短片过后,他们又介绍了与会的领导,还有不少政要,据说主管文教卫的副市长也来了。我向前排扫了一圈,只看到一片乌压压的黑西服,不知道哪个是副市长。
丁霁心换上露背晚礼服的时候,我特地看了看那串项链,果然如她所说,她自信的微笑,加上镁光灯的照射,那串项链吸引了最多的目光。
那串绞丝的项链正坠在她的胸口,挡住了那个露出来的最美的地方,那份犹抱琵琶的欲说还休别有一番风味。
轻柔的华尔兹想起的时候,酒会才真正开始,人们才脱掉一个个的符号和职位。有人在舞池中间拥舞,有人找到自己喜欢的人搭讪,也有人三三两两地暗织蛛网,借此机会网罗青年才俊。佩佩也是舞会上的女王,多个男人邀请她,把她忙得不亦乐乎。好在小女孩和丁霁心一样,有应付男人的天赋。
我端了杯红酒去窗边坐着,欣赏着这城市美丽的夜景。脚下灯光闪烁、车来车往。这三年,武昌也长高了,临江矗立的一座座闪烁着的高楼像一位位临水梳妆的美人,夜色中的黄鹤楼在灯光的照射下,更是晶莹通透。
“在这里发什么呆?”突然有人拍了我一下,是丁霁心。她今天穿了八厘米高的高跟鞋,又高了一截。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的话,就有一位男士走过来请她跳舞,只见他身材颀长,五官也生得端正,左手手腕上赫然戴着一块浪琴表。丁霁心介绍这是一位书商,学院图书馆有一万册图书是他捐的,他的名字将被刻在图书馆门口的金砖上。
“曾小姐好!常听霁心提起你,谢谢你代我照顾她。”书商向我伸出手来。丁霁心在他背后向我吐了吐舌头,我知道了,这是她新交的男朋友,这是我们之间的暗号。
我将红酒换到左手,伸出手和他礼貌地握了握。丁霁心又向我眨了眨眼睛,还把头向书商偏了偏,我明白她的意思,她是叫我给他打分。书商转向丁霁心,用右手轻揽着她的腰。
接着又走过来一位诗人。诗人用诗一样的语言向丁霁心打招呼:
“晚会的女王!夜晚的精灵!原来你在这里!”
听到这样的赞美,丁霁心很给面子的,马上走过去,向诗人“赐”出了她的纤纤玉手,诗人握在手里,果然弯下腰来,吻了吻她的手背。
我看了看书商,想看看他什么表情,发现他正在打量我,四目相对,他很温和地笑了笑。我再看向丁霁心时,发现她又在诗人背后吐舌头。
我一向对现当代诗人没什么好感,我认识的诗人好像都很好色,仿佛诗歌就藏在女人的裙子底下。这位诗人怎么样我不敢妄下评论。我向他摇了摇头,表示我不了解,我不妄下评论。
“请问这位美女是从瑶池来的吗?”诗人指着我,转向丁霁心,“女王怎么也不介绍介绍?”
“嗯……”丁霁心微笑着偏着头,卖了个关子,说,“不能介绍,不能介绍给你,我怕介绍了,被你抢了去。”
两个男人都哈哈笑了,书商抱着胳膊,叉开两腿站着,显现出一副大人看小孩胡闹般的宽容。诗人则笑得很放浪形骸。
“敢问小姐芳名?”诗人还是向我伸出手来。
我老老实实地答了:“曾子麦。”
“敢问是哪三个字?”诗人还抓着我的手。
“曾皙的曾,孔子的子,麦……”我想戏弄一下诗人,脑海里还在搜寻,无奈丁霁心不解风情地说了出来:
“麦田的麦。”
我不由瞪了她一眼。
“有渊源有渊源,曾小姐人长得漂亮,名字也大有来历。初次见面,给曾小姐讲个故事,怎么样?”诗人问我。
我最怕现代诗人作诗,既然是讲故事,自然可以接受,我愉快地点了点头。哪知丁霁心在旁边直给我使眼色,拼命摇头,待我明白过来想阻拦时,诗人已经声情并茂地开始了:
“话说盘古开天地之后若干年,西泠城有个员外,富甲一方,年届六十,膝下却无子嗣,只有一女……”
丁霁心和诗人相视而笑。我不明白他们笑什么,只听得诗人继续讲下去。
“女儿生得如花似玉,国色天香……”诗人说着,拿手掌指着丁霁心,从上往下一比画,丁霁心很配合地微微一曲膝,表示过奖了。诗人含笑点一点头,又继续讲下去,“小女已经到了出阁的年龄,员外为小姐的婚事伤透了脑筋,小姐自觉美貌无比,一定要寻一个天上独有、地下无双的一等一的人才来……”
这下,丁霁心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她不知是要继续微笑好还是板下脸来更好。
“这年,员外下定决心,一定要为小姐招个贤婿。于是,他在城门外贴下榜文,榜文言:某某员外之千金,如何如何,今择良婿,不论贫富贵贱,识得这百字天书即可。
“且说这榜文下附着的百字天书,乃是那狗头员外自己造就的字,天下间哪有人认得?一个个满腹经纶的才子都摇头叹息而归,只有一个放牛的,捏着一根牛鞭子,在榜文下看了半天,说:‘真可惜,一个字不认识!’
“看榜的家丁听了,大喜过望,总算有人认识了,只有一个字不认识有什么关系呢?他们把放牛的拉着去见了员外。员外一见,大叹真是天赐良缘啊,这择日不如撞日,不如就今日给小姐完婚,遂征求小姐的意见,小姐也是不亦乐乎……”
一行人听着,脸上都不知是什么表情。可是,诗人还是自顾自地讲着:
“于是当天晚上,郎情妾意、干柴烈火……”三个人都低下头去,丁霁心撇了一下嘴巴,明显地吞下了一口怒火。可诗人似乎浑然不觉,他继续兴高采烈、绘声绘色地讲下去:
“……做成了好事。这好事做完了,小姐才想起来要问:‘情郎啊,那些字都是些什么字啊?’放牛的倒是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一个不认识啊!’如此半天,小姐才明白这个自己肚皮上的男人什么字都不认识,她一脚把他踢到地上去,骂道:‘你什么字都认识,拿支笔充什么读书人唦?’”诗人故意把个“人”字念得又快又轻。
“放牛的被他踢火了,从地上爬起来,吼道:‘你自己瞎了眼怪我?我拿的是牛鞭,不是笔,你硬说我要充什么读书人唦?’”
讲完,诗人自顾自地大笑起来。“不好笑吗?你们怎么不笑呢?”谁都听出诗人是讽刺书商的,他是怎么样也笑不出来,丁霁心也没有那肚量,我没有办法,只得应付地笑了笑。哪知诗人又说:
“还是曾小姐有文化,我就知道曾小姐喜欢听我讲的故事……”
丁霁心和书商没那么好的修养,他们不理他了,牵着手要下舞池,可巧学院领导和副市长迎面走来,学院领导把丁霁心介绍给副市长,书商连忙把丁霁心递到他手上,于是,挽着丁霁心滑入舞池翩翩起舞的就是市长大人了。
书商只得又回到我和诗人身边来了。
诗人没再理他了,他又对我大谈其谈现代诗歌的出路。丁霁心和市长跳了一曲又一曲,他还在谈拜伦和雪莱,我完全没有办法脱身,只好端着酒杯听着,任由自己的肚子饿得咕咕叫,眼见诗人将侍者端来的一碟又一碟的水果、糕点统统装下肚,最后还说了句:“现代诗歌,完了!”说着,他将最后一块火龙果塞进了嘴里。
市长去一边休息了,丁霁心向我们走来。书商想迎上去,丁霁心拿起旁边的一杯红酒一饮而尽,将空酒杯塞给他,深情款款地向诗人走过去。
“算了,我决定了。”酒会快结束的时候,丁霁心拨弄着胸前的水钻项链,告诉我。
“什么?”我摸不着头脑。
“决定正儿八经谈个男朋友。”
我朝舞池指了指书商:“就是那个?”
“他们两个显然都不行。”
我有点摸不着头脑。
“书商刚才把我堵在化妆间,差点没给我直接开个价出来……
“他刚才和我跳舞,一直把我往舞池边上挤……到了舞池边上,他又把我往化妆间那里带。……”丁霁心笑了一下。
“他先天南地北不着调地侃着,我也装作少不更事地听着,其实我心里在琢磨,他什么时候下手……
“果不其然,不一会儿,他顺势把右手搭到我的肩上——他在试探——我笑着推了推,也没真用力,没有推开,也就任由他那样搭着。最初,他没有动作,只是轻轻地、若有若无的搭着……
“我知道他在等待时机,但我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我只是想看看,他这个人到底是怎样的,他的底线到底在哪里……
“他的手轻轻地抚摸起来,那湿湿的、腻腻的手指头在皮肤上打着圈,摩挲着,然后慢慢地向下滑,一团火在完全裸露的背上游走,大手滑到腰的下部,停在那个地方,他在犹豫……手在那里停顿了一下,又装作若无其事地向上移动,停到腰中间,那里是晚礼服两根丝带交叉的地方,那两根细细的带子梗在中间——他可能就要下手了,果然,他突然掀起带子,手正要往前面伸,就在那一刹那,我一转身,一把抓住他的手掀开,从化妆台上抓起一根簪子朝他手心里猛扎……刺得他疼得直咧嘴却又不敢出声……”
十八、良家妇男
“想来想去,哪有多少良家男人啊,呆也就呆点吧。”那个书商的举动最终让我选择了我并不喜欢的宋一鸣——那个医生。
和书商相比,宋一鸣简直是太规矩了、太正派了。他陪我逛街帮我拎衣服时不小心碰到我的手,还要跟我说声对不起,每次过马路牵我的手还要咨询我的意见……我简直要晕了,按照他的这个速度,一本书写完,我们还隔着遥远的十万八千里。
不温不火地谈着恋爱,每次约会我总喜欢拉上几个死党,曾子麦不太喜欢这样,她自认为是二百五十瓦的电灯泡,但是我一意孤行,非拽上她不可。
“你这样拖着我们,也不想想宋一鸣什么感受?”一天在酒楼里吃饭,趁宋一鸣上洗手间的当儿,她教训我。
“这有什么?他敢有什么意见?”我不以为然,瞧宋一鸣看我的那眼神,我就知道我吃定他了。“每回跟他在一起也无趣,逛街就拎着东西在后面跟着,你们要不来,我就要闷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