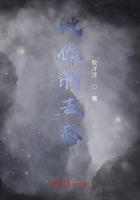埃斯拉在痛苦中清醒了过来。整个晚上她都处在一种焦躁不安的状态下,几乎一直是半梦半醒的状态。她从床上坐了起来。呻吟了整个晚上的艾丽芙终于睡着了,一整晚都在坚持照看艾丽芙的凯末尔也最终在早上得以稍微休息一下。为了不打扰到他们两个,埃斯拉轻手轻脚地钻进了洗手间。洗完脸之后,她从包里摸出手机,走出房门去到了走廊里。
走廊里已经不像晚上那么寂静了,空气中分明可以感受到一种早餐时间的繁忙感。护士们手里端着食物盘,这些是要分发给病人以及家属的。她觉得去花园里说话可能会方便一点儿。她在门后找到一个安静的角落,拨通了警局的电话。总机旁边值班士兵的声音立刻出现在电话的那头,当意识到电话这头是谁了的时候,他立即会心地说道:
“我帮你接到上校那里去。”
所以这倒帮她省了不少事。
“你好,埃斯拉。”
当她听到上校的声音之后终于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是的,是我。你怎么样了?还好吗?”
“我很好,很不错,真的。”上校回答道。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但仍然很自信。“神灵保佑,我们的人没有伤亡……他们也告诉我说你昨晚打电话来过了。”
“是的,我昨晚打了。你为什么不回复我?”
“我回到警局的时候都已经凌晨三点了。我不想这么晚了打扰你。”
她正要说“你应该打来的,我一整晚都在担心着你”,但她随后便改变了主意。
“昨天听到交火声的时候我真的很担心。”
“我正在想要不要今天早上路过考古现场的时候去找你,告诉你昨天发生的事情。”
“但我现在不在现场,我在加齐安泰普的医院里。”
“你说你在医院里?”
听到他明显紧张的声音,她心里隐隐有一种莫名的激动。
“我很好。艾丽芙被一只蝎子咬伤了。”
“我希望她会没事。”
“她已经好很多了。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了?我真的非常想知道。”
“我看我还是不要在电话里告诉你吧。现在我只能说,一切都很好。现在你们考古队可以继续你们的事情了。”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抓到凶手了吗?”
“是的,他们不会再来招惹到你们了。”
“他们认罪了吗?”
“我们抓住他们的时候他们都已经死了。”
接着对话暂停了几秒钟。
“你确定他们是凶手?”
又是一阵沉默,接着上校用困惑的语气问道:“现在在电话里讨论这个事情不是很合适。你什么时候能回来?”
“我不确定,不过有可能是下午吧。”
“那你回来的时候顺路过来一下吧,我再告诉你细节。”
其实埃斯拉当下还是很想知道事情原委,但她意识到这时候再苦苦追问也无济于事。
“好吧,那下午再见。”
她其实什么都不用担心了,上校安然无恙。但她还是不能完全放心下来,她觉得上校似乎话里有话。她再次回想起是分离派分子所为这种假设,但她自己也不是很相信这种假设,这对她来说一切都讲不通。要说他们谋杀村庄护卫队队长热沙特还说得通,但谋杀哈吉·赛塔尔就实在是莫名其妙了。还有,如果真是分离派分子承认犯了凶杀案,他们也会发布一个公告;他们完全没有什么理由隐瞒事实。而且热沙特·阿伽的凶案是在昨天刚刚发生的,如果真是分离派分子干的,至少现在也应该出现一份关于哈吉·赛塔尔的公告了。她满脑子都是这些问题,在走进医院的时候差点儿和大卫迎面撞上了。
“早上好。”医生看起来很高兴,“我正在找你呢。你还没吃早饭吧?”
“还没有,怎么了?”
“那去我那里吧。我父亲邀请你共进早餐。”
“太棒了,但我的朋友还在睡觉。”
“他们醒了之后护士会告诉他们我们在哪里的。”
埃斯拉有些无法抉择。她真的很想和大卫的父亲谈谈,但眼下艾丽芙还没有完全苏醒过来,她怎么好在这个时候弃她而去呢。
“但是艾丽芙……”她说道。
“完全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毒性正在逐步消退。”
“好吧,我们走吧。”埃斯拉说道,“他们会告诉我朋友我们去哪里了的吧?”
大卫露出了自信的微笑。
“你一点儿也不必担心,我现在就去通知护士长。马上就回来。”
医生正往外走的时候,埃斯拉的电话响了起来。电话那头是泰奥曼,他打电话来问问艾丽芙怎么样了。埃斯拉向他讲了目前的情况。考古队那边也是一切都好,蒂莫西也和他们一道去了现场。他们现在正在休息,工人们正在抓紧吃早饭,他也刚好抓住时机给她打个电话问一下情况。工人们也一切都好。除了西里之外所有人都来了。也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没有出现,但其他人都在努力工作。今天将会举行哈吉·赛塔尔的葬礼,所以他们都想早点收工。泰奥曼和穆拉特会把工人们带到村子里去。他们中的两人会代表考古队出席葬礼。噢,对了,他和穆拉特都化好妆了。他都还不知道前一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他道歉了。埃斯拉现在不想谈这些,她让他向其他人传达问候之后便挂了电话。
让泰奥曼小小地紧张一下也许是好的。他需要好好学习一下应该怎样对待朋友。
事实上,埃斯拉也对前一晚泰奥曼的行为震惊不已,因为他一直是一个非常好相处的人。他不是一个特别有个性的人,他对自己的人生以及事业也没有多大的雄心壮志。他曾经的梦想是当一名建筑师,但他高中时和现在一样懒散,完全没有为那个目标去努力奋斗。当他发现在大学里补考实在是太痛苦的时候,他选择了考古学。对他而言,吃、喝、睡、玩即是他生活中最爱做的事情。简而言之,他就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人。但昨晚上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他突然间就失控了。有可能是穆拉特对他有些太过分了。“不管是什么原因,他都没有任何理由这么做。”埃斯拉这么想道。她在他们还在讲电话的时候就在想,现在表明自己已经原谅他了似乎还有些为时过早。
大卫的大众高尔夫在狭窄的黑石街道上缓缓前行,车灯照射着街边宏伟房屋的镀锌大门以及石墙,仿佛给这座城市笼上了一层薄幕。这时,车子驶上了一条宽阔的大道。这条街和你在伊斯坦布尔或是土耳其可以找到的任何一条丑陋的大街没什么两样,一排排的商店,人行道上匆忙赶路的行人,以及到处充斥着的汽车马达声和喇叭声。谢天谢地,这一路并不是很长。大众高尔夫转入了另一条街,两旁是种满了桑树的人行道。埃斯拉回想起自己初来这座城市的时候是来过这条街的。所以,加齐安泰普给她留下的第一印象便是正面的。而眼前这条街也快要走到尽头了,出现了两旁没有树木的人行道以及一大圈的楼房。还好,这条街也不是很长,很快他们就再次被郁郁葱葱的绿色给包围了。这里很少有建筑,只有偶尔可见的一两栋房屋。
埃斯拉感到有一丝的紧张。
“我们这是要出城去吗?”
大卫傻傻地笑了。
“别担心,我不会把你卖了。我的父亲在萨利古尔鲁克的避暑别墅里。我们现在要去那里。”
“那萨利古尔鲁克到底在哪里?”埃斯拉半开玩笑地问道,“你确定不是在拐卖我吗?”
“我确定。”不一会儿他伸出手指向前面,“这里就是萨利古尔鲁克。那就是我们的别墅。”
“真漂亮。”埃斯拉看到这座石屋,“看起来似乎已经有些年代了。”
“确实很古老。这座房子修起来的时候,这里周围还没有什么人烟呢,但最近周围出现了许多建筑。”
这栋两层建筑物直挺挺地屹立在一片果园中央。一丛五颜六色的玫瑰中间矗立着一棵直插入云霄的胡桃树,树下、屋前摆放着一张早餐桌。埃斯拉看到两位老人坐在桌前,一个中年女人正端着满满一盘子的早餐小心翼翼地走过去。
“戴眼镜的那位就是我父亲。”大卫介绍道。
“他是一个人住在这里吗?”
“那个站在那里的女人叫古尔萨姆·巴奇,是她在照顾我父亲。我太太和我的孩子们也时不时地会来看望我父亲。”他停了下来,接着戏谑似的看着埃斯拉。“但他们现在出去度假了。所以你也可以看出来,在夏天我就是一个单身汉。”
“那另一个男人是谁?”埃斯拉想表现出她对医生的所谓“单身”状态一点儿也不感兴趣。
“萨基普·阿玛卡,他是我父亲的一个朋友。他可是加齐安泰普的一个名人;他是参加过独立战争的一名老兵,是一位退休教师……”
大众高尔夫终于开到了别墅面前,停在左边的相思木树荫下。“我不知道他也来了。”大卫熄灭了发动机,“现在他们俩一定是在斗嘴,像两只在打架的山羊。”
“他们合不来吗?”
“完全合不来,他们就是敌人。我父亲从来不认同萨基普·阿玛卡的行事方式,但当他年龄逐渐增大之后,他就开始经常刺激他了。只要他们俩一碰面,争论总是不可避免,但他们却又谁也离不开谁,总是形影不离。他们一起在美国念完了高中,现在他们的朋友都已经去世了,只剩他们俩了。要是他们其中一个先走了的话,另一个将会十分孤独……但是,今天这种场合,萨基普·阿玛卡还是不来的好。”
“他可能是认为他的朋友一个人在家很无聊吧。”
大卫摇了摇头,他并不同意我的看法。
他们穿过花园一路往摆在树荫下的餐桌走去,空气中布满了玫瑰花香,桌上是丰富的早餐。两位老人站了起来。尼古拉斯的蓝眼睛在如同神灵一般满是皱纹的脸上忽闪忽闪的,往前站了出来,把手伸向埃斯拉。
“你好,我是尼古拉斯,我是一名退休医生。”
埃斯拉握住了老人的手,明显触摸到他紫色的脉络,也在此时向他做起了自我介绍。
“这位是我的老朋友,萨基普。”他作出了一个淘气的笑容,这笑容使得他那两排整齐的假牙尤为明显。
就在此时,埃斯拉才注意到萨基普是靠着一根手杖才勉强站了起来。
“退休历史教师萨基普。”老人向女人伸出了微微颤抖的手,他的每个字都说得铿锵有力,仿佛是要填满朋友未仔细介绍的空白。
从他满头的白发可以想象出他年轻时候的样子,只是现在变白了而已,但他深肤色脸上那双棕色的眼睛里已经出现了小黑点,已逐渐变成灰色了,就像是一幅悬挂在他们面前的窗帘一样。埃斯拉突然发觉老人站得离自己有些太近了,这样让她感觉有一点儿不舒服,所以她立即往后退了一小步。
“请原谅我站这么近。”老人解释道。和他虚弱的身体不同,他的声音依然饱满有力。“我的大孙子把我的眼镜弄坏了,所以我必须要站得特别近才能看清楚。我希望这没有让你觉得有什么不适。”他冲尼古拉斯点点头继续说道:“我和这家伙一直处不来,但当他在电话里告诉我说他会和埃斯拉·哈尼姆一起聊聊过去的老时光的时候,我就不能控制自己了,所以我就来了。”
“你来挺好的。”大卫插了嘴,“要是我父亲有什么遗漏的话你正好可以补充一下。”
尼古拉斯颤颤巍巍地伸出手,示意客人在他对面坐下。
“请坐。”
当埃斯拉坐下以后,她的眼神和古尔萨姆·巴奇的眼神交会在一起。
“欢迎。”古尔萨姆怯怯地说道。
在古尔萨姆的坚持下,大家都立即坐下来开始享用早餐。她准备了一系列美味的食物,有蜂蜜和自制果酱、加齐安泰普浓芝士和图卢姆芝士、橄榄油沙拉和扁豆沙拉。这两个老伙计什么都想吃,但他们的肚子已经承受不了这么多东西了,所以很快他们就开始问一些常规的问题:她住在伊斯坦布尔的哪个区?她是在哪里念的书?她已经做了多久的考古学家了?幼发拉底河流域的考古挖掘会持续多久?埃斯拉一边吃着早餐,一边简要而又准确地回答了这一系列的问题。这样的状态持续了整个早餐时间。
当古尔萨姆·巴奇把桌上的东西收拾停当,给老人端来柠檬菩提茶,给大卫和客人端来土耳其咖啡之后,他们的探讨才真正算是开始了。
“你告诉大卫先生说最近发生的两起凶案和七十八年前在这里发生的凶案很相似。”埃斯拉说道,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老医生身上。“你肯定吗?”
“我当然肯定了。”尼古拉斯说道,“萨基普肯定也记得他们。那是七十八年前的事情了。要是我没记错的话,那是1921年。”
“是1339年吗?”萨基普斜视着尼古拉斯。
“不,不是的,根据哈吉拉日历应该是1340年。”
“我记得。加齐安泰普被包围了。希望上帝保佑我们再也不要经历那样的日子了。哦,那是怎样痛苦的日子啊!”
“我说的是被包围之后的日子。”他的朋友提醒道。
“对,对。你说的是包围被打破之后,就是加齐安泰普军队上校奥兹德米尔攻破了法国军队的包围圈逃出去……”
“不,不对,我说的是那之后的事情。”尼古拉斯再次纠正了他朋友的话,“我说的是法国决定撤出加齐安泰普的伦敦会议之后。”
萨基普现在算是彻底明白了。
“亲爱的,我懂了。你说的是亚美尼亚人准备逃亡的时候。”
“这下你懂了……那就是我说的时候。所有的亚美尼亚人都开始担心1915年大流亡会再次重演,所以他们都变卖了所有的家当前往叙利亚去了。”
“他们当然应该这么做。”萨基普说道,“他们一定在脑海里想过要是高唱马赛曲手持旗帜的法国军队攻入加齐安泰普时他们会做什么,他们会穿上军装,昂首阔步,为的只是激励自己的同胞们奋起反抗。”
“他们怎么会知道?他们还以为法国人是来拯救他们的……总之,总之,继续吧。”尼古拉斯清了清嗓子,“我们现在说到哪里了?啊,对了,亚美尼亚人开始逃离了这座城市,但有一小部分人,就是生活在你们现在正在挖掘的地方以及周边的那些人并没有离开。1915年大逃亡以后,大概有五六家人留了下来,他们觉得在那个时刻应该不会再发生什么事情了,所以选择了留下。他们当中就有教堂的牧师柯克尔,拥有现今高文村周围大量土地的敖汉内斯先生,以及铜匠伽罗。然而,这三个人在法国军队撤离之后的一周内被残忍地杀害了。柯克尔牧师被人从钟楼上推了下来,也就是现在的清真寺。敖汉内斯先生被人杀害在去往村里的路上,头颅被人砍下,放在其膝盖上。伽罗则在自己的商店里悬梁自尽。”
“太诡异了。”埃斯拉喃喃道,“前两起凶案完全和哈吉·赛塔尔与热沙特·阿伽的案子一模一样。那么,凶手被抓到了吗?”
“抓到?那时候,我们在打仗。亚美尼亚人被视作我们的敌人,他们会去抓谁?”
“在战争中,谁又知道谁是有罪的,而谁又是无辜的呢?”萨基普补充道。
“得了吧,萨基普,谁是有罪的现在不是已经很明显了吗?大家都在说有一支专门制造混乱的队伍,他们经常在大家的眼皮子底下进行杀戮。大家都看见了,其实就是库尔德人阿伽,热沙特·特科格鲁的祖父,昨天的凶案,他就有很大的嫌疑。毕竟,不正是阿伽抢夺了敖汉内斯先生的土地然后取而代之的吗?”
“我并不知道这些事情。”老人辩解道,“这就是一个礼尚往来的世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要是亚美尼亚人只是管好自己的话这些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
埃斯拉对萨基普的话并没有多大兴趣。
“那这些被害人的家庭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
“我不了解敖汉内斯先生和铜匠伽罗的家里人,但伽罗神父的家人都逃到贝鲁特去了。这男人有个年轻的儿子,还有个更小的女儿。当这个年轻男人意识到自己的妹妹只会拖累自己的时候,便把她留给一个善良的邻居照顾,自己则和母亲一起逃到贝鲁特去了。之后,他们又从那里去到了法国……”
“你为什么会问起他们的家人?”大卫打断道,“难道你认为会是他们家人中的一人犯下这些凶案的吗?”
“你别再让自己过多地纠结于这个猜想上面了。”萨基普如是说,仿佛有人在征求他的意见似的,“这些凶案都是恐怖分子干的。那些下层阶级的人企图分裂这个国家。每天都有陷阱,每天都有人会牺牲。那些卑鄙的流氓,我们并不比亚美尼亚人少吃多少苦。”
“但亚美尼亚人在你手下也没少吃苦,现在不还是这样吗?”尼古拉斯可不打算让他的朋友占据上风。大卫对自己父亲的话感到心烦意乱,所以他转过身过去看埃斯拉会作出怎样的反应,但埃斯拉还在细细回想七十八年前发生的命案和现在的案子之间的相似之处。
“任何人听了你这话都会认为你所说的就是真相。”萨基普抓了抓自己的拐杖,“是他们最先毁了我们之间的友谊,毁了我们之间的兄弟之情。我们已经接受了他们,我们像兄弟一般生活在一起,我们完全没有干涉他们的语言或是他们的民族。加齐安泰普最大的宗教建筑就是圣母玛利亚教堂,不是吗?”
“但之后你就残忍地让他们去流亡了。”
“都是因为你们。”萨基普现在已经愤怒了,“是你煽动我们这么去做的,是你们叫他们去寻找他们自己的国家的。所以那些笨蛋就轻易地上当了,开始在我们背后做起小动作来。”
“别把亚美尼亚人牵扯到这里面来。”尼古拉斯说道。他的态度如同是足球比赛里,一个球迷坚决维护自己主队的状态一样,具有相同的倾向性。“背后做小动作的是英国人、俄罗斯人以及法国人。我们并没有煽动谁去做什么事情。”
萨基普激动地把拐杖往地上拄了几下。
“那是个谎言!你们也牵扯其中。”
他把脸转向埃斯拉,继续说着。
“亲爱的,他在撒谎。他们离美国好几万千米距离,关他们什么事?”
埃斯拉对这一点也很好奇。
“打扰一下。”老人对大卫说道,“我说的不是你。你现在也是我们之中的一员了,希望我的话没有冒犯到你。”他又转过去看着埃斯拉。
“上世纪初期,新教徒创立了一个叫美部会的组织。”
“美国州县外国事务行政委员会。”尼古拉斯很享受这种一直纠正他的话的做法。
“好吧,好吧,别打断我。”萨基普反驳道,“你也能够猜到,这些人打算在像我们这样的国度传播他们的宗教。当他们一建立起这个组织以后,就立即把加齐安泰普纳入了他们的计划,就像是我们特别要求他们这样似的。”
“并不是在他们一成立就这么做了。”尼古拉斯似乎是想证明自己的记忆力依旧很好,“美部会是在1810年成立的,加齐安泰普被纳入他们的计划是在1819年。”
“好了,我们知道了,现在请闭嘴……总之,亲爱的,你也可以猜想到,这些人就这么被默许了。当买买提·艾柯夫提到‘单齿怪兽’的时候,他所说的帝国主义仅剩的一根獠牙就是美国。所以,当我们狡诈的奥托曼帝国允诺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的时候,这些伙计们就开始一边取悦我们的国家,一边在背后搞起小动作来。”
“所以,我们就搞了小动作,后果又是什么?我们开办了一所学校,建立了一所医院,做了各种行善积德的好事。”
“没错,但你们为什么要开学校和医院?为了分裂我们的国家,侵占我们的土地。”
“萨基普,你真的变成了一个脾气暴躁的老人。”尼古拉斯说道。
“有罪的人当然知道把责任归咎于谁。来吧,大声说出来,叫我老头子。说你想说的话吧,你也不能阻止我揭露你的阴谋诡计。”
现在,萨基普看起来是真的愤怒了。埃斯拉开始有些自责,自己不该在两个朋友之间提起这么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她已经对她想要了解的事情有所了解了,所以现在她开始想是不是可以尽早离开这里了。
“说真的,尼古拉斯,即使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我有时候都还是会梦到马西斯。在那个孩子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在那以后,你也再也没有听说过他的消息,是吗?”
在听到马西斯这个名字的时候,尼古拉斯眼里的愉悦瞬间消失了,眼神黯淡了下来。萨基普也注意到这一点了,所以他把脸转向了他们的客人。
“马西斯是你的朋友吗?”
“仅仅是朋友还不够;他是我们的亲兄弟。我们就像是一个豆荚里的三颗豌豆。我们是不可分割的。在高中的时候,这个家伙、马西斯和我就像是三个火枪手。少的那个就是达尔达尼央。”
当萨基普点头示意尼古拉斯就是他所说的“这个家伙”时,埃斯拉的眼神落到了坐在她对面的这个男人身上。也就是在这时,埃斯拉才发现尼古拉斯先前眼神里的愉悦已经全然消失了。不得不说,大卫脸上似乎也出现了相同的沮丧表情。萨基普则完全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话带来的影响,继续说着。
“马西斯比我们年长几岁。他就像是我们的大哥哥一样,保护我们不受比我们年龄大的孩子的欺负。说实话,他打架真的很厉害,他也很聪明。”
“他出什么事了?”
“他失踪了。”萨基普说道,“之后没有人见过他,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当加齐安泰普被攻占的时候,我们都站在不同的阵营。马西斯加入了法国阵营,他们支持亚美尼亚军队。尼古拉斯则进入了他父亲的医院,战争期间他都在里面。我参加了抵抗运动。因为我的速度很快,所以我成为了奥兹德米尔阁下的私人信使。我向第二兵团的萨拉赫丁上校发送代码字母,穿梭于包围整个城市的法国军队之中。敌军不管是在兵器还是在参战人数上都远远优于我们,城里的人却忍饥挨饿有几个月之久了。当地人用杏树种子做面包,用干草煮汤,为了争夺马匹的尸体不惜恶语相向。奥兹德米尔阁下和萨拉赫丁阁下常常互通书信。在我第五次送信的时候被为法国军队做事的亚美尼亚人抓住了。我穿的是平民的衣服,我试图向他们解释我并不是士兵。他们搜了我的身,但是并没有发现任何代码字谜,可他们还是很怀疑我。两名士兵用他们刺刀的把手狠狠地揍我,希望能从我嘴里套出点什么话来。他们狠狠地击打我的踝骨、膝盖以及肘部。我被打得趴在地上。我觉得我随时都有可能被打死,就在那时,我听到一声‘住手!’喊这话的人是马西斯。‘放他走。’他说道,‘他没问题,我可以保证。’可事实上,他是知道我加入了抵抗阵营的。但在那时,友谊,我们之间的友谊比我们俩所处的对立面更为强大。我站起身来拥抱了他。‘你最好先离开这里。’他警告我。我和他待了几分钟,稍微休息了一下,接着我走出了第二兵团。所以马西斯不仅救了我的命,还帮我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埃斯拉一边听着萨基普·阿玛卡的话一边看着尼古拉斯。当他的朋友一直在赞美马西斯之际,尼古拉斯的脸有些拉长了,蓝色的眼睛也变得毫无生气。埃斯拉想趁这间隙离开。
“谢谢你邀请我来享受这美味的早餐,这次谈话很愉快。”她说道,“但我现在真的应该走了。”
“现在不是还早吗?”尼古拉斯说是这么说,但他并没有坚持。
萨基普看起来似乎有些失望。
“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说……”
“下次吧。”埃斯拉微笑着。
“我们还是别为难客人了吧,萨基普·阿玛卡。”大卫对埃斯拉表示了支持,“我答应你另外找个时间再把她带过来。”
萨基普和尼古拉斯都站起身来目送埃斯拉离开。可是,现在的尼古拉斯确实已经不像刚开始那样兴致高昂了,他似乎有什么话想说。
泥板十七
阿诗穆妮卡一点儿也没变。当我看到她坐在皮斯里斯身旁的时候,这就是我的第一想法。她和我在神庙里看到她的时候一模一样,异常美丽、自信。
第二天早上,我坐在图书馆里的一把木制长椅上等着阿诗穆妮卡。就是这个女人,让我第一次感受到女人嘴唇的香甜,让我第一次触摸到女人身体的美好;这个名字,甚至是在我独自一人的时候都不敢提及。我自己都不知道此刻我的心情是恐惧大过欢愉还是欢愉大过恐惧。我只知道一看到她我就很开心,但同时也很害怕。除此之外,我就再也没有其他想法了。而我自己也不想有其他什么想法。就在前一天,在我和皮斯里斯国王以及阿诗穆妮卡作别之后,我就来到了图书馆,仔细查看了所有的史诗资料,把它们整齐地排成排,并把它们的标题刻在一块泥板上面。当阿诗穆妮卡来找东西的时候,她只需要看看这块泥板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知道图书馆里有哪些资料了。
当我等待她的到来时,我不禁在脑海里思索,她到底是会只身一人前来还是会有一名官员伴其左右。我希望她会和一名官员或是皮斯里斯的一个亲信前来。这样我说话就会舒服多了,我也就能正常执行国王交代给我的命令了。这个问题我还没来得及想多久,阿诗穆妮卡就光鲜亮丽地出现在图书馆大门口,如同一颗闪亮的晨星。
当我看到她出现在大门口时,我的心脏以及身体里就涌出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感,这感觉就和当初我第一次在神庙里看到她的时候是一样的。她身着一条设计有花纹图案的蜜色裙子,脖子上戴一条银色项链。她用她那比小麦色皮肤更深一些的棕色眼睛盯着我,神情中带着甜蜜。
我弯下腰,躲开了她的眼神。
“欢迎,高贵的阿诗穆妮卡。”我用一种冷冷的、虚假的声音说着。
然而她却用一种热情而真诚的声音作出了回应:
“谢谢,帕塔萨那,过了这么久了,能再次和你独处是多么好啊。”
我卸下了防备,抬起头,正在这时,我看到了她棕色眼睛里的火苗。神庙里那个害羞的小女孩已经不见了,现在的她是一个双眼装满了故事的女人。在这一刻,我发现否认一切都是于事无补了;阿诗穆妮卡就是我的宿命,我是无法离开她的。虽然如此,我还是做了些抵抗。
“我为你列了一个单子。”我指了指前一天做好的泥板,“上面记录了我们图书馆所有的史诗、传奇、歌谣以及诗歌。你可以在清单上选择你想要找的资料。”
阿诗穆妮卡挪了挪和我站得更近了,仿佛完全无视我刚刚说的话。
“帕塔萨那,你为什么装作不认识我的样子?”她问道。
站在我身旁的这个女孩就是那天我醒来之后发现她的离开让我几乎快要疯了的女孩;也是我苦苦哀求大祭司瓦尔瓦兹迪告诉我她身世的女孩。现在她主动来找我了,并且在寻求和我亲密接触的机会,我们很可能会完成那一晚没有完成的神圣的事情。我眼前浮现出她蜜色裙子下她那赤裸的身体,但是我还是立即把这样的画面从我眼前抹去。
“我认识你。”我回答道,“你是阿诗穆妮卡,是我们伟大的皮斯里斯国王的挚爱。我只是一个要遵循你和国王命令的仆人。”
“你不是我的仆人。”她说道,“对我来说,你是和我同床共枕的第一个男人,早于皮斯里斯。”
我紧张地环顾四周,确保没人听见我们之间的对话,接着我低声说道:
“求求你别再说这样的话了,神灵会惩罚我们的。”
“不会的,神灵已经安排我们俩在一起了。是皮斯里斯破坏了神灵的旨意。他是个永远不知满足的人,妄图成为这世上所有人的主人。正是因为如此,只有他才应该被神灵惩罚。”
“你不能这么说我们的国王。”我警告她,“他很爱你。”
“他爱的是他自己。他同时爱着我和其他十个女人。”她说道,“很快,他就会找到一个比我更年轻、更漂亮的女人,把他带去闺房,成为其挚爱。另外,即使他爱我,我也不爱他。他有权力,但丑陋;他高贵,但粗鲁。他从没像你这么温柔地看我,他也不像你这么美好地对着我笑,他的声音也没有你的好听。”
当我听到阿诗穆妮卡的这席话时,脸不自觉地红了起来,这时,我注意到莱马斯就站在门边。我立即转变了话题,故意大声地说话,好让莱马斯听到:
“尊敬的阿诗穆妮卡,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就把这块泥板带走吧,这样你就可以好好看看清单也好作出自己的选择。”
阿诗穆妮卡也看到了莱马斯。
“我想要苏美尔诗人琳格写给他母亲的诗。”
“当然可以。”我说道。当我伸手去放置琳格诗集的架子寻找时,脑海中浮出一个问题,于是我转身面向阿诗穆妮卡问道:
“请原谅我这么问,但这首诗是用阿卡德语写的。我想知道您能看懂阿卡德语吗?”
她眼里出现了一丝奇怪的神情,随即又假装没什么异常。
“会一点点。”她说道。
“那不好意思了,你最好还是不要读。”我尊敬地低下了头,“读琳格的作品,你必须要熟练地掌握阿卡德语。”
听到这里之后,莱马斯向我们走了过来,极其恭敬地说道。
“你看看你,帕塔萨那。”他说道,“你怎么不为尊敬的阿诗穆妮卡把诗歌翻译一下呢?毕竟,这些诗你都已经烂熟于心了,不是吗?”
“不行!”我边吼边往后退,像是手被火烧到了一样,“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做。”
阿诗穆妮卡微微闭了闭她那双美丽的眼睛,接着对我说道:“那我就去告诉国王,他会为我找一个人翻译的。”
拒绝翻译就是违抗皮斯里斯的旨意。
“不,不,没必要这么做。”我努力挽救愈发不可收拾的局面,“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会把诗歌翻译好的。”
阿诗穆妮卡自信地盯着我看。“你翻译的时候我想在旁边看。”她说道,“那样的话你就可以帮我提升我的阿卡德语水平了。”
“这简直是我们天大的荣幸啊。”好事的莱马斯再次大声地说道。
我内心不断咒骂着,脸却转过来看着阿诗穆妮卡。
“只要皮斯里斯允许,为您效劳就是我的荣幸。”我说道。
“你不用担心,镌刻师帕塔萨那。”她脸上露出的是这世上最美丽的笑容,“我马上就能得到允许。准备好明天就开始翻译吧。”
接着,她带着泥板离开了图书馆。她离开的时候,老莱马斯站起身来盯着她离去的背影。
“她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女孩子。”他说道,“如同一株石头缝里长出的小草,一束融化冰雪的火焰,一阵剑指大海的春风。我们的国王是多么的幸运啊!不管是谁,只要一看到她就如同看到了比我们幼发拉底河岸边的花园还要广阔的花园;不管是谁,只要一听到她的声音就会在内心找到平静,就像是听到了一曲美妙的音乐;和她在一起,再平淡无趣的生活也会变成稍纵即逝的美好时光。”
当莱马斯目不转睛敬畏地盯着阿诗穆妮卡离去的大门时,我不禁在想,要是他知道发生在我们俩之间的事情之后,他是否还会有如现在一样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