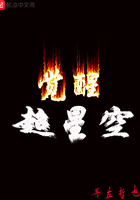好在这片刻的休息等过了乌云和细雨,再迷茫的人,也是应该重新打起精神了。西面就是边塞上的泾州,再往北去就是戍守边疆的哨所和烽火台。远望过去,泾州城上空飘着白烟,安定城内的树木已变成了秋天的模样。这里和内地平原地区完全不同的风土人情,竟让人一点都提不起兴奋之情。哪里需要把这归咎于喜欢不喜欢呢,此地的水土也一样养育着此地的人们,心情总是自惹一身枯燥,思来想去,也终是要从这异地他乡遍寻出故乡的千般的,也才让人能舒下心来,好好地过活一场。
只可惜,此地不是旅人的故乡,风景再好,也只是中点;环境再恶劣,也不是终点。何必非要为这无端之物烦忧!
登高一望数千年,若要从故纸堆中寻出几个沉溺于文字中的人,这样的情殇似乎是最适合李商隐的。
唐文宗时期,朝廷中的朋党争权斗争异常激烈,这两派官员分属于牛党和李党,他们各自都用尽权势想要提拔本党成员、排斥异己。李商隐最初是受到了牛党令狐楚的赏识,从而在令狐楚的门下任职多年。纵然是无心,也总是容易被李党之人当成是牛党人士来看的。
政治这件事情,哪里就适合李商隐做了呢?越想越觉得不对头,可历史偏偏就这么上演了,留给后人的只有这么些可有可无的哀叹。
唐文宗开成二年,令狐楚去世,驻守在泾州的泾原节度使王茂元请李商隐做自己的幕僚。李商隐来到泾州后,因着一腔才华而深得王茂元的器重,并且还就此做上了金龟婿。只是王茂元属于李党,李商隐同意当他的幕僚并同他的女儿结婚,这在牛党人的眼中看来是真真切切的背叛。令狐楚的儿子令狐綯认为李商隐有负他的家恩,对李商隐更是怀恨在心。这一婚事,也就自此筑成了李商隐一生的命运。
开成三年,李商隐来到长安参加应博学宏词科的考试。本来高中只是探囊取物的事情,可当吏部将录取名单上报给中书省以后,中书省中掌权的官员看见了李商隐的名字,脸色却比寒冰还要冷。只因执掌生杀大权的官员是牛党之人,李商隐的一世理想也就此断送了。
天底下的人儿,竟真的再找不出一个能承受如此苦痛的了。
落榜后,李商隐回到了泾州岳父家中暂住。他心中毕竟是有些不平之气的,这才有了这首七言律诗《安定城楼》:
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
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
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
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
在绵延的安定城墙上,有着高达百尺的城楼。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恐怕在李商隐看来,此时的沉默更是怕惊醒内心的忧愁吧。从年纪轻轻就开始为国事担心,最终却还是得不了功名,前程怎么能就此了断呢?从长安出来后,本想要在这荒遥之地散散心情,却只看到了末路穷途,于是只得一场大哭。当年年轻的贾谊上表痛陈国事却不被汉文帝采用,又有王粲因失意才远游,这些不都是在说尽自己的心事吗?这份忧虑,恐怕只有从前朝人的身上去寻觅出一些影子了。
每个文人心中都藏着一个愿景,他们大抵都是希望能够用十年寒窗苦换来一朝成名天下知。在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后,只需一叶扁舟,便可以了却残生。这样的人生,写满了理想和传奇。可在现实这块大石头面前,再多理想的鸡蛋,也终是要磕得粉碎。谁还能想到那些看重功名利禄的人,见到了如此清扬的异类,就像猫头鹰看见了腐烂的老鼠肉一般,若不争抢干净,又哪里来的罢休的道理?
只是可怜了普天之下的所谓“君子”,皆被染上了乌鸦的黑色,于政治中再看不见半点光明。但愿此时流下的一滴眼泪,能化成一泓清泉,洗濯每一个沾染了尘世的心灵。或许这样的梦想,终是要破灭的。可有人曾经为此努力过,便足以值得纪念了。
论尽古今之事,得了一个李商隐,哪里还需复求其他!
远方的天涯
在两国交界的地方,总是要设立一座关卡,即便是只是形式化的象征,也终得有一座城镇来着证明此地的不同意义。
在库尔勒市北郊8公里处,有一座铁门关。它扼住了孔雀河上游陡峭峡谷的出口,曾是南北疆交通的天险要冲,更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中道咽喉。自晋代时候便在这里设关,因其险固,故称“铁门关”。
在铁门关还流传着“塔依尔与卓赫拉”的民间故事,故事中的爱情似乎也正是在向社会控诉着,究竟这道铁门挡住了敌人的入侵,还是挡住了男女对爱情的自由向往。
传说古焉耆国王的公主卓赫拉和一位牧羊人相爱,阴险毒辣的丞相卡热汗唆使国王抓了塔依尔,并打算将他处死。卓赫拉知道这个消息后,设法救出了心上人。不料却被丞相发现,他立即派人追赶这对亡命鸳鸯。痴怨的情人夜奔出关时,不幸连人带马坠入深涧。后人为缅怀这对为爱情和自由而死的恋人,在铁门关对面公主岭上建造了“塔依尔与卓赫拉”。
自古以来,这样的爱情故事总是动人的。两个相爱却不能在一起的人,在当时的封建礼教下,有勇气去突破父母的管教以私奔来解决问题,多少是有些悲凉的。在这份冲动的背后,自然应该悲伤起对爱情的坚贞不渝。可这样的结局并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结果。然而后世的人们总是愿意享受这份悲切,他们似乎早已经认定了但凡能够流传下来的故事,必定要有一番破茧而出的苦楚。至于最后能不能够羽化成蝶,那又是另当别论的事情了。
陷入爱情中的男女,大抵也是不会去考虑后世人的看法了吧。
由焉耆向西前进不远,就可以到达今天的库尔勒市。在库尔勒城的北面,便是这座险要的铁门关,由此出去就到了塔里木盆地。一出此地,风景就和关内大不相同了。诗人岑参第一次赶赴西域时,在旅经铁门关时登上了临关楼极目远眺。不看则罢,这一看,不免要引出来一些故事:
题铁门关楼
铁关天西涯,极目少行客。
关门一小吏,终日对石壁。
桥跨千仞危,路盘两崖窄。
试登西楼望,一望头欲白。
从此地往西望去,虽已经是更上一层楼了,却依旧只能看得见茫茫大路伸向远方,遍寻不着行人的影子,更看不见终点究竟在何处。这样的景色,未免显得单调了一些。对于守城的那个小兵来说,是不是就该把这个词汇换成是“孤单”呢?诗人远眺,看到的风景引发的是独属于自己的心绪。可那个小兵远眺的时候,该引发谁的一番感慨呢?大概终须是要让诗人把这一人一景看在眼里的进而又化成了自己的愁苦。
好在登高一看,总是有些风景的。两岸山高百余丈,在悬崖见到的只有一座危桥勾连,若是走在上面,恐怕双腿都要发软。看看这险峻的地势,竟然是可以让人把头发都吓白的。
然而岑参没有说出来的终归不是这里地势的险要,而是出了铁门关,还有比此更险要十分的世事和人心。最难测的,往往是在身边却看不见的事情。危险,也从来都喜欢假装成和善的面目,以满面含笑来迎人送客。
行路之难,难于上青天。
可是若再给这份旅程加上从军两个字呢?
李白的一首《从军行》,便从铁门关的险峻起了一场调调:
从军玉门道,逐虏金微山。
笛奏梅花曲,刀开明月环。
鼓声鸣海上,兵气拥云间。
愿斩单于首,长驱静铁关。
当军队经由玉门关的时候,敌人怕是还在仓皇逃窜。对于性命这件事情,没有人是不珍惜的。虽然战场打仗不是士兵的本来意愿,但对待逃跑却是丝毫马虎不得的。追敌的队伍一直行进到了金微山的脚下,这里便是当今的阿尔泰山。眼看着马上就出离国土了,却依旧不能熄灭杀敌的愿景。《梅花落》的笛声已经响了起来,恰似带着环佩的斗志在月光下叮咚作响。每一道亮光,都应该映射出军士们同仇敌忾的豪情,就像是军鼓大作一样冲破天边的云彩。
于是,不得不再一次感叹起李白的胸怀了。在他的眼里,从来都没有因为远离了故土而产生的悲愁,因为面前还有着更伟大的事情要去做,他哪里有时间和心情去思虑这些儿女情长的事情?唯求能够一举拿下敌军首领的首级,带军长驱直入消灭铁门关附近的敌人,然后才能得长久之安。
这是一份属于男儿的豪情,是从来都不会打上折扣的事情。
可是诗人李白故意给我们忽略掉的,是这里的环境。即便众所周知其是恶劣的,但宝剑锋从磨砺出,随军打仗哪里还需要去计较环境的好坏呢?只是纵然故意忽视不见,在此地,却依旧难以闻听到几声莺啼。说起来,不免觉得荒凉了一些。
丝绸之路北线上最大的城市是龟兹(今新疆库车),其东面距离轮台大约一百公里,在没有便捷交通工具的年代,往往需要把一两天的时间浪费在行路上。有时遇到恶劣的天气,从起点到终点的过程,就更不知道会充满什么样的艰险了。
晚唐诗人吕敞,在旅途经过龟兹时,正好是春末夏初之际,因听见了边塞上难得的莺啼声,于是才有所感慨地写下了《龟兹闻莺》一诗:
边树正参差,新莺复陆离。
娇非胡俗变,啼是汉音移。
绣羽花间覆,繁声风外吹。
人言曾不辨,鸟语却相知。
出谷情何寄,迁乔义取斯。
今朝乡陌伴,几处坐高枝。
我们常常忘记了,边塞也是有春天的。
春天是属于整个世界的,再荒凉的地界,也应该迎来属于它的一抹绿色。树木在这个季节正努力生长,似乎是要极力把冬日的严寒驱走,以便开始迎接下一个季节的酷热。偶有几处早莺,大概也是习惯了此地的环境,几声啼叫,就道尽了复回家乡的温情。时间在流转,年复一年,尽管胡地的环境已经改变了它原本娇小的样子,可这份清脆的啼声却始终如一。就像是久在远方的游子一样,虽是苍老了容容颜,惟独能够保存下来的,只有心中的这份清澈。
尤其是到了异地他乡,周边人说话的语调完全是听不懂的,恰恰黄莺飞来,不免又因为记忆中的鸣叫而染上了思念的油彩。好在在这千里之外,还有一两只懂得诗人回忆的鸟儿于枝头婉转啼鸣,这就已经算是最大的慰藉了。
在遥远的边塞,人们心中总是要升起一种胆怯的感觉。家乡是那么的遥远,即使夜夜梦回,也开始要担心会不会迷路了。抬头望,只有家乡那一轮多情的明月,恰恰也照着边关的游子,像是在说着母亲的眷眷关怀。“哪知故园月,也到铁关西。”
原来,不是我们忘记了家乡,更不是我们不适应边疆的荒凉,只是我们丢失了曾经极易在生活中寻得到欢乐的那一颗真心,从此只剩下影单身冷。我们缺少的,竟是被自己白白丢掉的东西,曾几何时,这竟然成为了习性,想要戒掉也变得如此困难。
若再没有征战
在甘肃省的天水市背后,潜藏着一个动人的传说。
天水这个地名始于汉代。相传在汉武帝元鼎三年,有一天突然电闪雷鸣,大地也开始不停颤动。天水市南面的地面上竟出现了一条大裂缝,天上的河水开始无节制地注入到这条裂缝中,由此便形成了一个湖泊。据说这湖水是“夏不增,冬不减,旱不涸,涝不溢”。为此,汉武帝在湖边修建了一座城池,命之为天水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