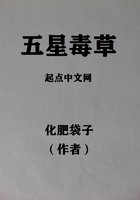“自去年寿宴后,我父亲被某个年轻姨娘灌了迷魂汤,”萧昱用无名指刮了下眉骨,推着沙盘上的骠马车队向北行进了十里,“整日和几个真人厮混在一起,吞服金丹妄求壮阳,呵,祖父若还活着,肯定直接气死。”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何况像他这样有些自傲的人,怎么会缺附和?
谢焕成心转移话题,“……看服饰衣着,这一班人马是长生阁的杀手组织,那另外一片,喏,就是这儿,他们是什么人啊?”
“等下你就知道了。”
萧昱嘴角一撩,余光望了眼沙盘一侧的铜雀小日晷,自顾自言道,“要说这个姨娘,来的还真是时候,萧知礼一心求‘道’,我二哥又是个点子扎手的人物,够他这个大公子喝一壶的。”
谢焕这才听明白。
“鹬蚌相争,才能让他们的注意力从你身上转移开来,这道圣旨才颁发的如此稳当。”
萧昱盯着沙盘局势唔了一声,“你还是没听懂啊……”
“什么?”
看她短手短脚的,萧昱不由轻笑,变出一根打马球的月杖,“用这个。”
即使见识过他的身手,谢焕很难想象眼前人也会像个寻常少爷般呼鹰博猎,纵酒使气,顿时就觉得这条月杖沉甸甸的。
“……这样?”她虾着身用月杖往西南向一推。
萧昱挑眉倒退了两步,抖手一甩,那把石榴刀狠狠削断了沙盘上早已立好的“大纛旗”,遮蔽了天日。他用二指旋绕一挡,骠马车队干净利落里逃出了最危险的风陵狭道。
而刚刚的石榴刀不偏不倚正扎在沙盘的水关机括上,汩汩水流运作,谢焕的两队人顿时被冲下了山崖!
本来是瓮中捉鳖,结果倒成了人家请君入瓮。
“这也可以?!”没见过这样耍无赖的,谢焕目瞪口呆。
“怎么不行?”
萧昱循循善诱,“此时正值河水涨潮之际,旬内我们必然要动身,如果我们从这儿,这样走,距离哨岗森严的官道不过一箭之遥。所以,这条风陵狭谷是他们唯一的机会。”
“这是什么?”她拈起那面“泼天盖地”的旗帜。
“暂时保密。”萧昱眨了下眼睛,“你刚才不是想知道这些人是谁么?是……”
“萧府的人,”谢焕笃定地打断它,手腕晃动间,雀舌茶在白如雪的邢窑盏中载浮载沉,“准确的来说,是你大哥的人。”
“你倒聪明。”
谢焕摊手,“因为实在没有别的可能了。”
萧昱怔了下,回过神来继续给她讲演,“你看,长生阁的杀手就好比我二哥,章法心机有余,然太过急于求成。这些的确是大哥的手下,我大哥是个宁停勿进,空谈仁义的宋襄公,却正与二哥相反。”
谢焕被他绕糊涂了,“照你这么说,这样的性子,他又怎么会豢养武士来截杀你呢?”
萧昱凉凉而笑,小指勾住银鱼袋甩来甩去,“栽赃给流寇是一码事,朝廷命官死在任上又是一码事,他不得不来。”
“可是……”谢焕颦拢烟眉,“若我是你大哥,必会尽力保住你,一则加强与朝廷的联系,不至于蹲在盱眙城这口井中变成青蛙。二来,时不时的有你在皇帝陛下眼前表忠心,让萧家洗掉‘南朝廷’的恶名声。”
“说的不错,”他赞许地打了个响指。
“不过这里面的关窍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他们切不准陛下的脉,总以为我是去当人质了。再者京城里我还有个故人,若是连起手来,居高临下地收拾萧家,啧……”
他捋了一把假想中的微髯,不知在模仿谁的口吻。
“你别是以前有什么事亏心吧。”谢焕若有所思。
萧昱故意作色,四个指尖一拍她的后脑海,“小丫头,把我当什么人?挤兑正人君子的地皮无赖?”
“哎——”谢焕粲然一笑,身形偏了下就躲开了,“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这么有理,你别躲啊,”萧昱笑道,颔身援臂将月杖拾起来递给她,“这次我们交换一下,你来指挥我们进京的车马队,而我,负责这两批人马……”
……
“干爹,干爹!”
黄天作幕,一轮残阳圆登登如空印般稳稳盖在题跋处。九重宫阙尽头小步趋来一个戴幞头着圆领袍的小宦官。
此人年纪不大,却生了一副三角眼,流露出的光色简直会粘人,“干爹,您看看,薛府向来是通透人儿,这是给您做得脸面!”
“干爹”是个四旬出头的太监总管,皮肤很白,也许傅了粉,他瞟了眼那份长之又长的礼单,鼻子里哼声,“东珠珊瑚的,好歹是个尚书,怎么净学这一套!咱家无功不受禄,这脸面可要不来啊。”
朱红曳撒一甩,小太监赶紧跟在后面整扯着琵琶袖,“不是儿子说您,干爹这话就说岔批了。您这叫无心插柳,随口那么提两句,就能把昭明公主的意思压下来,把那个姓萧的毛小子送到尚书大人的脚下头。”
小太监察言观色,见他只不言不语地望着殷日坠落,殷勤地补了句,“干爹就全当是白拣的。”
“白捡的,”总管扬起藏锋的眉毛,眼中精光一闪,“好儿子,干爹命都是白捡的,再拣点什么,反正总大不过命去。”
小宦官闻言有点惶恐,连忙赔笑。他干爹忽然弹了弹那份礼单的金描硬地封壳,比划了一根食指,那意思是你可抽走一成。
目送小宦官透着欢喜的步态,总管笑了笑,抽出一方缂丝帕子抹汗。
“哟,郑总管,您可来了!陛下在里面等您半天了!”
郑总管抬眼打量,认得,是内务府的管事。
登时笑意更深,嘴上客气,却在两人擦肩之时将帕子高扬,轻飘飘扔进对方怀里。
内务府的下意识伸手一捞,觑见之下顿时有些傻眼。
缂丝帕子,这可是好东西!
内务府的珍而重之地把帕子揣进怀里,冲着他的背影暗啐道,“女里女气,指不定哪位对食送的,呸!没根的人,也配叫莲花儿?”
……
郑总管抬脚跨进了正殿,抬眼看时,当今圣上指腹间搓着根朱笔,眉心川字隐隐,翻看着一份节略。
“陛下,老奴在此。”
“莲花,”穆天歌舒展神色,“莫要老奴老奴的,你看着可不像四十好几的人。”
郑莲直躬身站在一旁微笑,“在陛下面前,奴才确是老了,奴才想,陛下的意思是,臣看着不像翰林院的学究。”
“是啊,看着不像,行事也不那么拘泥古板。上次与公主下兽棋,就可见你是个极有分寸的人。”
“公主天真无邪,陛下多爱护一些也是应当的。”郑莲直将剩余半盏冰雪饮子连托盘一起抽走,交给身后的侍女。
“嗯,”提及昭明,穆天歌持重老成的外相出现了一丝裂缝,“那件事,你做得如何了?”
“奴才已经办妥了,”他自然知道陛下所指为何,“新建成的萧府距大内不远,却也清净雅致,不怎么匠气。”
穆天歌思索了一瞬,“崇云殿的院判与这位萧公子是交好?”
郑莲直微惊,他知道当今圣上过目不忘,有“复刻式记忆”的美誉,可没想到竟能强悍至斯!
“那就让他到时搬去同住吧。”少年天子用不甚在意的语气,“想来萧家那边也该动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