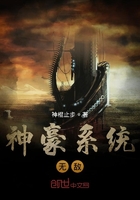沿着旋转的崎岖石台阶向下,覃唯停下脚步,悄然驻足,不知是笑还是叹息,只是自言自语喃喃道:
“怒弦动了,这肃杀的剑气是殿主大人。看来我的猜想有一半是对了,剩下的一半就要靠太师来解答了。”
东南阳天,太华殿主便是此处尊上,代代都是自下方挑选出来的剑者,上一任仙逝,下一任上位。
到了太师这里,不知是为什么,中途早早便让了位,把殿主的权利移交给朱猎的师父,自己下了主殿,到这里来住,除非真有能力的年轻一辈有问题才能见面。
而覃唯因为师父外出游历,赌博赌翻了,把他丢给这位老人管教,但也不是常常见面,他每每只有被问题困扰的实在不行了才来。
而这一次,是为了朝清和朱猎而来。
生死碑冢教给他很多东西,其中有一个特别的传说,他一直是当笑话看的,可是在遇见朝清的那天,他开始震惊的发现,也许这不仅仅是个故事,而是一段少有人知的密闻。
因为他牵扯太大,涉及太广,才成了一个笑话,一个人人都知道,并且予以否决的真实秘密。
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回这里?为什么要去生死碑冢?为什么要师兄和朝清对战?为什么会单独来这里?为什么明知朝清见殿主危险还要他去?……
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对这里产生了疑惑,他不能信任这里,他恐惧于这一切,甚至怀疑他和朝清的相遇是个阴谋,然而如果要说一切迷惑要有源头,那一定就是那个教导着他,并且早早退位,隐藏在这里不见任何人的一位老人——太师朱霎。
五百一十六阶。
踏下最后一阶,是一块不大不小的平台,正对着一座普通的殿宇,它坐落在孤山之上,背后是半环状的山壁,一架木桥搭上两边悬崖,覃唯再熟悉不过的一段路。
走上木桥,桥小是深不见底的深渊,云海漂浮,孤雁的叫声传来。
他记得那是太师收养的鸟,它是通知太师有人来了。
步下木桥,收敛心情,覃唯望着那紧闭的中门,等待太师传唤。
不多时,一个沙哑的声音传来:
“你这次来,以什么问?”
这是太师的一个习惯,让后辈做好准备,不轻易提问,提问前要想好付出的代价。苦力,禁闭,抄书,等等。
“以自由问。”
覃唯答到。
“多久?”
这个回答显示了一个人的决心,而覃唯已经有了失去性命心理准备,因此答道:“一生!”
随着他的回答完毕,那扇紧闭的门突然“吱吖"一声开了,只听里面传来太师淡淡的声音:“看来这个问题还真是困扰你很深啊,竟然让你不惜性命来问我。”
覃唯整理神色,带着犹如往常的笑容,轻浅慢慢的走进大殿内,那是一个穿着月白色长袍仙风道古的白发人,他背负双手背对着覃唯,仰头望着那七米长的挂幅,上书“天地君亲师”五个大字,意为祭天地,祭祖,祭圣贤之意。
室内,左右两根朱红色梁柱,太师立于中间,挂幅前悬空三把古朴长剑,色彩黯淡,中间那把甚至锈迹斑斑,犹如千年未开。
他转而回头,目如明珠,眼瞳色浅,似乎通透,肤色无碍一如婴儿,额心一抹金色符文,书写潦草,形似甲骨文鱼字。
“太师在上,弟子覃唯参拜。”
轻身跪下,低头俯身,双手抵额交叉,再慢慢抬头,便见到那双似乎非人的眼睛。
“你要问我什么?是非问不可,还是犹豫不决?是执意要问,还是稍待片刻再问?”
太师声音清晰,语调缓慢,说话时面色的表情不曾动了分毫,精美如画卷。
“便是片刻也等不得了。”覃唯不笑不怒,平静坚定的道:“弟子现下就要问,师兄的身世!”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为难之事,”直视他眼睛的太师看不出心情如何,只是淡淡道:“这事你不该问我,他是朱谣养大的,当年,人也是他抱回来的,些许陈年往事,困扰你什么?”
“那么,太师知道吗?师兄断剑之事!”覃唯仔细的看着太师面色,不肯漏看一丝,一字一句道:"两场剑战,每每剑断!"
雪白的眉轻浅皱了皱,那双骇人的眼瞳淡然不在,锐利微显,掀起波澜,声如钟乐高音:“你过了!”
“这就过了吗!?”覃唯提高声音,淡雅气度换作激烈,面色沉重,咬牙道:"这算什么过了,他连拿树枝作剑,都在要紧关头断裂,我如何能看不出,天下人如何认不出,你把世人都当傻子吗!?太师!"
“覃唯!!”
“不要这样警告我!”他一双带着愤怒和痛苦的眼睛看着这个他尊敬的人,带着控诉和指责“我如果怕死就不会来了,我既然敢来,就是把命放在你的手心里。我是要来问一问,你是否要为了自己的野心做出这样残忍的事来,我要搞清楚你是不是装了几十年,等这一天,时时刻刻用这样可怕的用心在对待师兄和我的师父!你你……”
覃唯说不下去了,因为他没有在这个男人的眼里看到丝毫的动摇和挣扎,只有洞悉一切的平静与淡漠。
“你说完了,”朱霎看着他,注视如一滴尘埃“知道很多吗?还有哪些,一起说来听听。”
“当然还有……”覃唯面色苍白的颓然笑道:"十剑藏首的传说以及寻剑人。"
这个时候,太师没有回他的话,只是居高临下看着他跪倒在地上,面色苍白疲倦,眼神黯淡,风度不在。
殿内是没有风的,寂静无声,压抑阴郁。
“承影,纯均,鱼肠,”这麽多天以来压抑和折磨他的就是这二十个字,把它们说出来就像把负担抛下,覃唯慢慢坐直身体,神情渐渐恢复冷静,闭上眼睛:“干将,莫邪,太阿,龙渊,赤霄,湛泸,轩辕。”
“不错,正是这十剑。”
朱霎没有再看他,而是转身走到挂幅前仰视着那三把古剑平静道。
“我一直不太明白的就是,它们不是一个时代的东西,不是同一个人打造出来的,甚至有的毁坏有的丢失,怎麽就联系在一起,成了同一个传说呢?”
覃唯说道这里,就忍不住停下来苦笑:"看到师兄后我终于明白了,原来竟是这样……"
“看来你猜到了,”朱霎清冷的声音回荡在室内:"其实很简单!剑乃伤人之心!这个东西它是本来就在的天地的道理,人的作用是把它具现化成实物,因此不管是谁打造了它,不管是谁使用了它,都无法隔断它们的联系,它的形状的用途不是工匠之间互相讨论得到的,而是相隔千里的人们脑海里同时出现的共同思想,由这个共同思想创造出来的东西就叫做剑!"
“它们早已在冥冥之中存在于未知的天地,通过人赋予的形态在这世上生存,而师兄就是它们存在必须仰仗的一样物体,也可以说是宿主。太师……”覃唯坐在那里,竭力克制自己的情绪,用平静而肯定的语气说道:"这是一件千百前来都没有人能做到的事情,你也不可能!"
“不,”朱霎衣袖浮动,那张俊美的脸上是睥睨的冷傲,眉眼之间没有丝毫动摇和迟疑,一派淡然冷清“你想错了,我不是认为自己能做到,而是决定抓住这个上天赋予的机会。”
“什么机会?”
“一个鱼肠剑主不说,连千百前来传说中的寻剑人都送到了我眼前,你有什么理由阻止我去这么做。二十年前,朱谣抱着这个孩子来找我,我就决定让位与他,你明白吗?上天的意愿就是巧合,而且我的境界你这个没有修为的人是不会明白的。”
“通玄境吗?”
“不,是更高的境界。我思故我在,我诚至我道。”
“你这么做会毁了这个地方,这里所有的人都没法幸存,不会有人赞成你这么做,总会有些人要不顾性命来阻止你!”
“谁会来阻止我,谁?”
争吵在这里停下了,说这话的朱霎脸上是平静与不容质疑,还带了一点微微的嘲讽和怜悯的眼神。
他轻轻挥手,像抚去灰尘,神色淡然,月白色衣裳像是神仙,轻语道:“没有人会来的,当另外天地的人知道的时候已经迟了。”
早在覃唯第一次想到这些的时候,他感觉到的不是震惊而是恐惧,对于一个清楚太师实力的人来说,如果这真的和他有关,有谁能阻止,又有谁会来阻止,先不说打不打得过,就算打得过,会打吗?
答案是,不会的。
这个人,在这里,在那些从小在这里长大的人心里,他是一个地位尊崇,犹如神明的存在。
他们不会违背他的意志,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的性命,也不会阻止这个人的野心,而且,野心这种东西他们又何尝没有。
而另外的天地里,又有谁在意这个已经退位隐居的太师,他们恐怕连他长什么样也不清楚吧。
“你准备好了吗?”
“如果你是说死的话,永远也不可能准备好。但是不要紧,你要杀就杀吧,我还有可以相信的人活在这世上,我把我的一切都托付给他们了,连带你的事情。”
“我不会杀你的。”
覃唯突然听见朱霎这样说,睁开了眼睛,惊讶道:"我可是知道了你的秘密,你不杀人灭口,难道还要留我看戏吗。"
“在这个有趣的布局里,你要知道清醒的人很少,一共只有两个半人。如果你死了,一切就会显得很无趣。”朱霎如是说道。
“哦,你,我,殿主大人?”覃唯感兴趣的问道。
“不,”朱霎颜色浅淡的瞳孔深深的注视着他,表情有一丝波澜,似乎是笑了“你,我,你师傅算半个。”
“师父?”覃唯仰头望着他,满脸黑线和惊讶:"那个烂赌鬼!你说他是清醒的?!"
“你知道一切源于生死碑冢,你师傅是前一任看守和描摹的人,你觉得他不知道这个传说吗?只是他懒得往深处想,把你丢给我,是监视和警告之用,可惜你自己送上门来,只要我不杀你,他大约是不会管的。”朱霎徐徐走过覃唯身边,不顾他错愕的神色缓缓道:"毕竟他是很懒的一个人,除了赌博和睡觉,什么都不感兴趣的一个人。"
好不容易消化了朱霎所说的话的意思,他跪在地上转身唤道:"等等!你我……"
还不等他说完,朱霎身前的两扇大门轰然洞开,光线照进室内,那清晰的声音犹如编钟敲震,回响在室内:
“殿内弟子覃唯,冒犯尊上,巧言令色,撒谎成性,自愿在天剑塔内禁闭一生,修行悔过。殿侍何在,带他下去!”
原来这就是留他一命,覃唯面色苍白,神情震惊,一生自由换他活着,既不惊动师父,又可以让他看戏,而天剑塔有天干地支二十四道门,十二层塔,他这一生将永无重见天日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