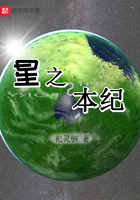雷明章急切的推开房门,隐约看到一个男人搂着雷媚躺在被窝里。雷媚明显的在抖动个不停。雷明章举起枪,打开灯,那个男人一下子用手遮住了眼睛。雷媚也用被蒙住头,雷明章冲过去掀开被,那个男人适应灯光后,把手拿了下来,雷明章一惊,说:“是你?”这时雷媚也从惊呆中醒过神来,一下扑到雷明章的怀里哭了起来,边哭边说:“爸,我怕,我怕。”雷明章气坏了,质问道:“朗良,你这是玩什么花样?你深更半夜的闯到媚媚的房里干什么?”说着就要抓朗良。朗良很平静,他从床上下来,说:“雷叔,我没想到竟然连你也不相信我。”雷明章说:“你怎么让我相信?今天的事你又怎么解释?我要是发现晚了,今晚你不就得逞了吗?”这时雷媚也说:“朗良,没想到你会是这样的人,本来我想把事情弄清楚后,我不计较你的过去,可......可你......”朗良并不急,他说:“雷叔,媚媚,咱们心平气和的谈谈。”雷明章说:“你别叫我雷叔。”雷媚也说:“你别叫我媚媚,恶心。”这时的朗良竟然乐了,他说:“先给我杯水好吗?”雷媚不情愿的给朗良倒了杯水。朗良接过水杯并没有喝,而是双手搂着水杯,沉思了一会儿,说:“雷叔,事到如今,我就把话都倒出来吧!其实,我在这儿呆这么长时间就是等那个假朗良的出现,并非为了媚媚,因为我已经不配媚媚了,虽然我爱她,可我不能让她受委屈。假朗良一直没出现,直到前几天,我发现气氛不对,总感到紧张,还有股子陌生味,这是我在特务连呆的那年训练出来的敏感,我感到要出事,而这个人很狡猾,只要我在他就不出现,我就假装走掉,本以为他会跟着我,可我出了城后,感觉就不对劲,好像那个人对我没兴趣似的。于是,我在夜里潜了回来,藏在后院,到晚上十一点时,我发现了那红外线望远镜,我知道他要行动了。媚媚灯熄后,我发现望远镜不动了,好像支在什么地方,如果是人手握着有颤感,能分辨出来,我知道那人已经行动了。我就钻是了媚媚的房里,本想让媚媚躲在衣柜里,我躲在床上,可媚媚惊叫了一声,而后是您的枪声,都怪我没事先打声招呼,弄成这个样子。”雷媚这时走过来,说:“蒋哥,对不起,我错怪了你。”朗良说:“都怪我,吓坏了吧?”雷媚点点头,依在朗良的怀里。雷明章说:“老了哟!比不得你们年轻人了。”
这时天已蒙蒙亮了,雷明章和朗良上了山,找到了那个望远镜,它支在树杈上,周围的草和树枝被压弯,踩倒。明显,这人已经不是在这儿呆一两天了。雷明章说:“这是个军用望远镜,看来这个人就是部队的。”朗良说:“能弄到这种望远镜,至少是连排长。”雷明章说:“你现在有怀疑的对象吧?”朗良说:“我们回去再说吧!媚媚和大娘在家我有点不放心。”他们从山上转回来,进了屋,一下就慌了:屋里被翻得乱七八糟,一看就有人来过了。他们冲进屋,屋里没人,雷明章喊了声:“坏了,我们被骗了,赶快找人。”朗良说:“您别急,给雷媚单位打个电话。”电话接通后,雷媚接了电话,她对这里的事一无所知。电话刚放下,雷明章的老伴就进来了,进门就说:“老雷,你玩哪门子邪?让我去,你又在家里。”雷明章问:“怎么回事?”雷明章的老伴说:“上士打电话说你找我有急事,我就去了。”雷明章问:“你听清楚是上士吗?”雷明章的老伴说:“你们当兵的都一个动静,我上哪儿知道谁是谁,他说他是上士。”朗良这时说:“看来这人对你们家的情况也了解个底掉,先别说别的了,我们看看少什么东西没有。”
雷明章和老伴就开始检查。东西一件没少,就连雷明章收藏的许多名贵项链也一条没少,当然,这些项链要和搓色桃核项链是没法比的。看来,这人来的目的是明确的,不得到搓色桃核项链誓不罢休了。这时朗良站起来说“雷叔,我总感觉你对我有成见,有些话你没和我说透,既然都这样了,我们不妨开诚布公的谈谈。”雷明章想了一会儿说:“确实是有些话我想问你,但考虑你可能有自己的想法,不便于说,便没问。”朗良说:“雷叔,您就说吧!其实,我是有些顾虑,但绝对没有其他的想法。”雷明章说:“那我也就不用掖着藏着了,我问你,你那天晚上在客厅睡毛愣了,你知道吧!以前你有这毛病吗?”朗良说:“我妈活着的时候说我心事重,小时候到有几回,可大了后就没了,那天我说什么了吗?”雷明章说:“这正是我想问你的,那天你几次提到一个名字,好像叫丁城,大概就是这个音。”朗良听到丁城明显的一愣,半天说:“不可能,丁城是我叔伯家二叔的儿子,我们根本就没什么来往,就是我爸去世那年他来过,是代表他爸、妈来的,来了连饭也没吃,放下钱就走了,他家在县城,瞧不上我们这个穷亲戚,来往很少。倒是他爸妈常来,后来他们出了车祸,双腿瘸了,就不来往了,我看过他们几回,挺可怜的。”雷明章说:“你想想,村里都知道你父亲手里有搓色桃核,丁城也该知道,他有没有忽然的对你家感起兴趣来,比如走动得多了,脸色好看了。”朗良说:“没有,我看脸子倒是比以前更冷了。”雷明章说:“那就怪了,你无缘无故的就提到丁城,为什么?你这段时间想过他的什么事吗?”朗良说:“没有,我根本就不会想到他。”雷明章这时也陷入了沉思,不再说话了。突然,朗良冷丁站起来,把雷明章吓了一跳,朗良说:“还别说,我一下想起了一件事。那是在那个村子关着的时候,那天夜里他们审我,我看见一个人在窗户前闪了一下,那人特别像丁城,可我转念一想,我的家乡离这儿几千里,他不可能来这儿。而且,丁城下巴底下长了个痦子,痦子上面长了撮毛,可那人没有。我也只是一闪念,以至于没想起来。”这时雷明章眼睛一亮,他说:“这个人可能就是假朗良,我那次倒是没认真看,把媚媚叫来,叫她想想。”雷媚回来后,听了这事后,她寻思起来,说:“好像他下巴有个点,像是被什么东西碰伤过留下的。”雷明章说:“看来这个丁城就是假朗良,事情很明了,我们就在军区里找,肯定跑不了他。”朗良说:“真没想到,真没想到。”
雷明章马上打电话给刘师长,说了情况后,让他给查丁城。可是雷明章没想到,根本就没有丁城这个人。雷明章说:“难道这个丁城不在这个军区?可是他和媚媚通的电话和信件都证明在这个军区呀!”朗良说:“他来部队目的明确,就是想得到那个搓色桃核项链,可是没想到会出现这么多的叉头。我看,我们就沉住气,等他出现,他迟早靠不过我们的。”雷明章实际上也没办法可使,只好这么办了。
可是,没想到的是,这人居然猴急到这个地步。当天晚上就打电话到了雷明章的家。雷明接起电话,假朗良说:“雷团长是吧?”雷明章听这动静挺阴沉的,心情就不痛快,没好声的说:“是我。”假朗良说:“不开心是吧!我是假朗良,我有句话要说,你别瞎搅和,识趣的话就把项链拿出来,不管那个项链在谁手里,拿了项链我就永远不打搅你们。”雷明章一愣,说:“你是丁城吧?”那边明显愣了一下,说:“不错,我是丁城,不过你查不到我的,同时我也告诉你放弃你们的想法,否则......”雷明章打断他的话说:“我们也想知道搓色桃核项链的去处。”丁城说:“别当我是傻瓜,你看看那后院的树,如果再这样,雷媚就是这个后果。”丁城恶狠狠的挂了电话。
雷明章立马把电话打到总机,查打进来的电话位置。居然是刘师长的专线。雷明章立马把电话打到师部,刘师长说:“没人打过电话,我一直在师部。”然而,刘师长查了电话记录,还真有一个打到雷明章家电话的三分二十秒的记录。这让两个人都很吃惊,看来这个丁城不太好对付。这时,雷明章才想起丁城刚说过的话,他和朗良、雷媚来到后院,往树上一看,差点没惊出魂来。
雷明章、朗良和雷媚看到树上挂的东西都吸了一口冷气。那是一截血淋淋的手臂,上面系了一块红纱巾......雷媚惊叫了一声,捂住眼睛,雷明章锁紧眉头。朗良走过去从树上摘下那血淋淋的手臂,原来是一节狗腿,洒着新鲜的血,看来是刚挂上去的,这个丁城本事不小呀!
回到屋里,朗良说:“先把媚媚安排好,让她住到招待所,班也不要上,让警卫员和大娘天天跟着。”雷明章说:“只好如此,他对咱俩动手得考虑一下。”朗良说:“我们也不能干等着了。”雷明章说:“我也这么想的,先从那个小盒子查起,本来它应该在河里,可为什么会让丁城得到,并送到这里来。”
第二天,他们把雷媚安排到招待所。朗良说:“媚媚,别到处乱走,有事让警卫员陪你去。”雷媚说:“蒋哥,我怕......”说着依在朗良的肩上。朗良说:“我们去去就回,听话。”说完,他们就去了刘师长那里。刘师长见到雷明章“哈哈”笑着说:“明章,带新女婿来了,我这个老丈人也得给点钱呀!”弄得朗良半红脸。雷明章说:“还跑了你不成,礼轻了媚媚还不闹死你呀!”两个人“哈哈”笑了起来。进了师部,刘师长把警卫员打发出去,关上了门说:“那件事我也有耳闻,今天要我帮什么忙就直说吧!”雷明章说:“牺牲留下的东西是不是都按遗书上写的办?”刘师长说:“绝对的,没人敢不经请示干出别的事,那是要掉头的。”雷明章说:“当时清点物品,朗良的小盒子在其中吗?”刘师长说:“都造了册子,马上就能查到。”刘师长让警卫员把造的册子拿来,果然没出路,所有物品都登记在上面。雷明章又问:“那么登记后,东西有可能被别人动过吗?”刘师长说:“不可能,当时就封存了起来,那地方没人能进去,守仓库的全是挑出来的,而且有一个连长和一个营长昼夜看守。这种情况不可能出错,除非是封存以前,也就是说问题出在朗良的身上。”雷明章看了一眼朗良,又说:“那么朗良的遗书是将小盒子扔到河里,这个环节上会出叉吗?”刘师长说:“不可能,当时朗良是咱们军区的,出了这么个英雄,当然我也荣兴,那回要不是朗良不知道要死多少百姓和战士,是我亲手把那个小盒子投到河里的。”雷明章想了一会儿说:“会不会让人调包了?”刘师长说:“调包也只可能出现在朗良身上,就是说在朗良自己保管的时候。”雷明章说:“这就怪了,朗良,你想想,那个小盒子是你的那个吗?”朗良说:“是,绝对没错,可是那小盒子没有浸过水,连里面的信都没湿。”刘师长听了,当时脸就绷不住了,说:“这话什么意思?”朗良忙说:“刘师长,我不是那意思,只是觉得奇怪。”刘师长说:“我******没文化,但绝对干不出那事,我也觉得奇怪,真是我亲手扔下去的,除非有一个和你那个一模一样的盒子。”朗良说:“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这小盒子是我父亲亲手打的。”刘师长说:“这事我也就知道这些,帮不上什么忙,不过我再查查看,还真说不定有什么叉头。”朗良说:“那就多谢刘师长了。”雷明章说:“刘师长,还有件事,就是朗良......”刘师长说:“不用说了,我们已经开始调查了,如果清白的话自然好说,如果真有那事,那只有军事法庭见了!”朗良一下紧张起来:“我真的没干,再说我也不回部队了。”刘师长说:“我说你说都没用,让事实说话,你现在还是军人,至少你的一切手续还在,你要受军人纪律的约束。”朗良还想说什么,雷明章用脚碰了他一下后,就告辞了。
他们从师部出来就去了墓地。朗良的空冢显得更加荒凉和落寂,显然那个人再也没有出现过。两个人在墓地前各有各的想法,谁也没有说话,十多分钟后就离开了那里。
回到雷明章家后不久,丁城突然来电话说:“雷团长,你不用再去调查了,这些我已经调查过了,实话跟你说,其实搓色桃核项链就在朗良手里,他这样做无非是想找个庇护的地方,你别太傻了,让人玩了还不知道。”雷明章说:“你什么也别说,我问你那个小盒子你是怎么得到的?”丁城说:“这个你就不用管了,我再次警告你,别把人逼急了。”丁城说完就挂了电话。雷明章放下电话时,看到朗良手里正玩着一条搓色桃核项链,他愣了一下,问:“你什么时候把它拿来的?”朗良说:“在墓地的时候啊!”雷明章说:“我怎么没看到它还在那儿?”朗良说:“也许您没太注意,不过这个仿制的搓色桃核项链还真有点水准。”雷明章有些火:“你别左右而言其他,你到底什么目的?你给媚媚写信是不是早就预谋好的了?”朗良张大嘴看着雷明章发出这莫明其妙的火来,他一时半时的不知说什么好。雷明章又说:“你用不着做出无辜的样子,查来查去根本就没一点线索,如果是外人做的不可能不留下线索,只有当事者本人才能把事做得天衣无缝,不过你也别觉得你高明。”朗良一屁股坐回沙发,脸色苍白,半天才说:“雷叔,千万别听丁城胡说八道。”雷明章说:“我不是三岁孩子,我有头脑,我会自己想的,用不着你提醒我。”朗良呆了半天,站起来颤抖着说:“雷叔,既然你不相信我,那我只好告辞了,我走后,小心丁城,让媚媚小心。”朗良转身出了门,走了。雷明章摇了摇头。
当天很晚时,招待所的人说媚媚还没回来。雷明章匆匆忙忙的去了招待所,只见老伴在哭,警卫员傻傻地站着,见雷明章来了,老伴一下扑到雷明章的怀里说:“媚媚丢了。”当时雷明章头晕目眩,险些栽倒。
雷明章无心责怪他们,问了问事情的原因。老伴说:“媚媚接了个电话后,说上厕所就再也没回来。”雷明章根据时间一分析,正是朗良走的时间,他骂了句:“兔崽子,动到我的头上来了。”雷明章立马派车拦住了几个路口。半个小时后,雷明章在车站看到了朗良,可是没有看到媚媚,雷明章急不可耐的冲到朗良面前,抓住朗良的领子问:“媚媚呢?”朗良一愣说:“雷叔,我真的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朗良哭了。雷明章知道事情并非那么简单,看来朗良真的没有把雷媚带走,如果媚媚落在丁城的手里可就坏了。雷明章急得一圈圈的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