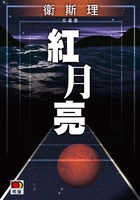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发桥又来“陪”我。他给我带来了一本古典小说《二刻拍案惊奇》,自己则捧着一本杂志看。村里能干活的大人小孩都下地干活去了,几个四、五岁的儿童在草朵周围捉迷藏,撵得一群鸡子叽叽喳喳地四散而飞。发桥聚精会神看着杂志,对眼前的一切充耳不闻。我拿着书,不停地翻着,一个字也看不进。我合上书,想求发桥帮我,却又不知道从何开口。
发桥大概看完了一篇文章,便把书放在椅子旁边的地上,伸了一个长长的懒腰。他见我没有看书,就捡起杂志,走过来,把杂志递给我:“不喜欢看古典小说,就看这个。”
“你愿意帮我吗?”我没有接他递来的杂志,站起来盯着他问道。发桥膘了我一眼,把杂志塞给我,拿过《二刻拍案惊奇》,一言不发地转身回去在椅子上。
“你知不知道我是被拐卖来的?”我冲着发桥问道。
发桥像是没听见似的,打开书继续看。
我走到他的面前,双膝跪下,哭道:“陈老师,你是有知识的人,应该是非分明,他们这样把我囚禁在这里是犯法的。你要救救我。我求你了!”发桥见我来这一招,心就慌了,连忙扔下书,俯身扶我:“快起来,不要哭,有话好说。”
“如果你不救我,我只有死在这里。”我赖着不起,哭得更凶。发桥撒手,站起来对我说:“你这成什么样子?如果你不听劝,谁也不会管你。”
我见发桥的话留有余地,觉得他内心可能还是想帮我,就听了他的劝告,站起来不再哭了。发桥让我坐在他的椅子上,过去将我的椅子往前挪近了我一些自己坐下,说道:“不是我不愿意帮你,是没有办法帮你。”
“你可以帮我报警呀。”我提醒道。
“报警?”发桥停顿了一下继续说,“当然也可以。那样的话,大桥的爸爸、妈妈,甚至姐姐都有可能坐牢,几个家庭就永远地毁了。还有,如果族人们知道是我报的警,我恐怕也不能在村里呆了。”
“他们会把你怎样?”我问。
“轻则挨扳子,重则丢小命。”发桥说。
“我不信。”我怀疑发桥在找由头,不想帮我。
“你不知道山里的风俗,所以你不信。”发桥像是给学生讲课似的抑扬顿挫起来,“几年前,我们村有一名叫陈武安的青年与一名叫陈善珍的姑娘好上了。算起来,他们是同一个祖宗的第九代。在我们这里族人是禁止通婚的。可是,陈武安与陈善珍爱得死去活来,他们听不进任何劝告,执意要结婚。不久,他们没有拿结婚证就住到一起了。双方的父母因此在村里抬不起头,见不了人,请求族人们正家法。结果,陈武安被绑在一个石磨上沉到了村前的池塘里,陈善珍被赶出了村寨。陈武安死后不久,陈善珍偷偷的跑回村寨,吊死在村后的一棵树枝上。”
“难道没有人来管他们?”我又问。
“天高皇帝远,谁管得了?”发桥反问道。
“难道这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不了村民?”我激动起来。
“法律当然能够管住村民,但是法律管不住一种势力,一种习俗。村民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来形成的习俗是谁也管不了的洪水、猛兽。”发桥像是发表在演讲。
“愚昧,愚昧。”我不停地摇头。
“愚昧,你说村民愚昧吗?”发桥走到我的跟前质问我。
“不把法律当回事,难道不算愚昧?”我反问发桥。
“可是,不把法律当回事的难道仅仅是山寨的村民吗?”发桥转过身,来回走动着,继续他的演讲,“国家的法律规定,公民一律平等。但是,山寨的村民能要求与城里人平等吗?譬如,我们教师,上一样的课,教一样的学生,公办教师每月300多元,而民办教师只有40元。”
“这完全不一回事。”我申辩道。
“怎么不是一回事?”发桥突然激动起来,“这不也是不执行国家法律吗?”
“这是由于国家太穷的缘故,并不是人为的不执行法律。它与村民因愚昧而置法律于不顾有本质的区别。”我试图说服发桥。
“那好。我再问你,我们的法律不是规定,公民有游行、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吗?你敢去游行,敢去成立一个政党吗?这个跟国家太穷没有关系吧?难道那些不让你游行和结社的人也愚昧吗?我看不尽然。他们有的是出于一己私利,有的则是屈服于一种势力、一种习惯。”发桥越说越激动,声音越来越大,几个捉迷藏的儿童以为他在与我吵架,都围过来看热闹。我感到无法说服发桥,便不再作声。发桥见一群儿童围过来,就冲他们说:“走,走,玩你们的去!”
孩子们吼着闹着跑开了。发桥回到椅子上坐下,默默地仰头望着天空,半天不说话。微风吹得树枝沙沙作响,几片半黄的叶子落到地上。
发桥没有答应帮我报警,让我感到非常失望。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悲伤,轻轻地哭泣起来。
“我理解你的处境和心情,但是你也要理解别人的难处。”发桥走到我身边,像是在安慰我,更像是在自我辩解。
“难道我就只能认命,放弃自由,在这个穷山沟呆一辈子?”我突然站起来,冲发桥吼道。发桥被我的举止吓了一跳,但他马上镇定下来,轻言轻语地对我说:“在这里呆一辈子的,你既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发桥告诉我,陈家寨这一带是有名的穷山沟,姑娘都削尖脑壳往外嫁,外面的姑娘又不愿嫁进来,一些在周边找不到媳妇而家境又穷的人只得打一辈子光棍,家境好一点的,就攒几个钱,到外面去买一个媳妇。村里那天帮大桥家看管我的翠就是被拐卖过来的。翠刚来时,也跟我现在一样,拼死拼活地往外跑,后来生了孩子,就不跑了,再后来还回了娘家,现在她与娘家人有往有来。
我警告发桥,我不翠,永远也不会成为翠!发桥说:“当然,你跟翠不一样,你有文化,有知识,所以你比翠更痛苦,也可能比翠悲惨。”在这种环境下,我最不想人知道的真实身份,尤其是不愿让人知道我是大学生。所以,忽然听到发桥说我有文化、有知识,我便有些心慌,想说的话也不知道说了。
虽然发桥不肯帮我,但是通过这么一次推心置腹地交流,我觉得发桥还是比较可靠的人,或者说是村寨唯一能够进行交流的人。我发现,发桥其实并不是不愿意帮我,而是找不到一个万全之策。慢慢地,我完全把发桥当朋友了,甚至将自己的逃跑计划毫不隐晦告诉他,让他参谋或提供帮助。但他每次都摇头表示行不通,并告诉我原因所在。
再后来,我渐渐地对发桥有一种依赖的感觉,希望双休日马上到来,好与发桥聊一聊,解一解心中的郁闷。发桥也善解人意,每次跟我在一起,天南地北地尽聊一些让我开心的事,千方百计让我忘却目前的处境,从不问我的身世。
然而,不论怎样,我总忘不了我的处境,忘不了我逃跑的计划。我得依靠和利用发桥,实现我的目的。
一个星期六的上午,发桥像往常一样来陪我。等村里人都到地里去了后,我就起身向村后走去。发桥也不阻止我,掉在我身后十来米远跟着我。我假装要逃的样子,快步向村后的山上走去。发桥慌了神,冲我喊道:“陈阿妹,别犯傻,你跑不掉的,村前村后都是人,他们知道你要逃,会打你的。快回来。”我转过身站着对发桥说:“除非你肯帮我,否则,就是被打死我也要逃。”发桥看了一下四周,见没有人,就朝我点了点头,并招手要我过去。
我走到一个早垛旁,紧靠着草垛坐下。发桥也跟过来,挨我坐着。他第一次靠我这么近,我能闻到他的气息,感受到他的呼吸,内心有一种隐隐的蠕动。我可怜兮兮含情默默地望着发桥:“发桥哥,”我第一次这么称呼他,“只要你能帮我逃出去,我永世报答你。”
“你怎么报答我?”发桥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任何一个女性都能够从这种眼神中看出一个男性的期盼或热望。
“只要我能够办到的,你提什么要求我都答应。”我低下头,声音小得不能再小。
“我一定帮你。”发桥凑近我,瞳孔放大,呼吸紧凑。
“你要说话算数。”我闭上眼睛,等待着发桥……
发桥轻轻地吻着我,我也吻他。突然,发桥两手托起我,走进两个草垛之间的空隙地。他从草垛上扯下一些稻草铺在地上,把我放倒在上面,快速地解开我的衣服……
事完后,发桥搂着我,温柔而又坚定地说:“我决不会辜负你的。”我完全相信他,忽然觉得有了依靠,心里塌实了,喉咙痒痒的,泪水便夺眶而出。发桥见我哭了,以为我在怪他占有了我,就向我道歉说:“对不起,我实在不应该趁人之危。”我怕发桥太自责了,就揩干了眼泪,主动拉着他的一只手。发桥拍着我的肩膀:“好了。咱们赶快离开这里。”我说:“发桥哥,你一定要帮我。”发桥使劲地点了点头:“一定!”
在期盼中,又迎来了一个星期天。见面后,发桥跟我说,他已经有了帮我逃走的主意。我上前搂住他的脖子,迫不及待地要他告诉我。发桥则要我先答应他一个条件。我用双手捧住他的脸问:“什么条件?”发桥说:“你必须保证,逃出去后不报警。”我知道,他是在为大桥的爸妈担心。其实,由于我害怕被人知道了被拐卖的经历,内心里也不想报警。我说:“我答应。”发桥说:“发誓。”我说:“可以。”于是,举起右手发誓:“如果我出去后报警,就……”发桥马上捂住我的嘴巴,按下我举起的手,说:“不用了,我相信你。”
发桥告诉我,他的主意就是让我想办法取得大桥爸妈的信任,跟他们到地里干活,然后偷偷溜到马路边,他到镇上租一辆车子,在马路边接应我。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可靠的办法,顿感逃脱指日可待,光明就在眼前。我踮起脚,感激地亲了一下发桥。发桥一把拉住我的手,进了屋里,走进我的房间,然后把我推倒在床上……
“牛——吃——草——,马——吃——谷——,人——家——娶——媳——妇——,我——享——福——。”当发桥和我走出屋子,坐在屋前的道场上休息时,一个男子唱着喊着从屋后走向远处。我问发桥,那人是谁?发桥说,是村里的海疯子。我说,他好像不疯。发桥说,天知道他疯不疯。
从星期一开始,我就按照发桥的要求,实施我的逃跑计划。我对大桥妈说,我一直呆在村里闷得慌,想到地里帮着干点力所能及的活,也好吐吐气。大桥妈不答应,说想干活,不必到地里去,家里也有许多事要做。大桥爸在旁边说,让她去吧,总不能一辈子呆在家里不出门。就这样,我顺利地走出了村,完成了逃跑的第一步计划。现在,只等双休日到来,发桥去镇里租车过来。然而,天公不作美,到了双休日,下起了大雨,两天两夜很少停息。村里人大多呆在家里休息。我既不能实施逃跑的关键计划,也不能与发桥商量。只好等着下一个双休日。
第二周的一天,大桥爸耙田,我和大桥跟在后面打那些耙不细的土渣。我既无力干活,更没有心思干活,打一块渣,就站着东张西望,休息片刻。将近中午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穿警服的人骑着摩托车进了村寨,心便怦怦直跳,我希望那位警察就是来解救我的。我不动声色地对大桥爸说:“我肚子饿了,想先回去。”我从来不称呼大桥的爸爸妈妈什么,要说话,就走到他们的跟前直说。大桥爸看了看太阳,已经当顶了,就说:“回去吧。如果饭没有熟,就吃点生花生压压饿。”
我不知道骑摩托车的警察到谁家去了,走到村口就呆在那儿等着。不一会,就听见了摩托车的响声,我迎着声音走过去,拐过一堵墙,就看见警察跨在摩托车上戴头盔,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我连忙跑过去,告诉警察,我是被拐卖到这里的,我要报警。正说着,村里的陈主任拿着一包烟从屋里出来。他把烟塞给警察,就跟警察耳语。警察突然垮下脸来,正色道:“老陈,你以为我是傻瓜,随便就能被骗住。你看她像疯子吗?”说着警察停下摩托,把我领进了陈主任的屋里。他拿出本子和笔,给我做笔录。我把我被拐骗的前因后果一一说了出来,但用了假名——苏亚琴,地址、身份也是假的。做完笔录,警察收起笔,合上本子,然后对陈主任说:“老陈,你是村干部,又是党员,应该知道拐卖妇女是犯法的。这事上面知道了,你是下不了台的。”陈主任不停地点头哈腰,一脸的微笑,连连说:“是,是,是,请童警官多多包涵。”
警察看了看我,就对陈主任摆摆手说:“老陈,你先出去回避一下,我要问苏亚琴几个问题。”陈主任极不情愿的离开了屋子。警察站起来,走近我压低声说道:“这里的村民不好对付,我一个人无法带你走。我先回去向领导汇报,然后组织力量来解救你。你暂时不要离开这里。”我感激地连连说:“谢谢,谢谢童警官。”我学着陈主任称呼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