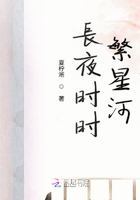从近处看,改革开放以来,民众中靠劳动挣工薪的普通员工,典型的如农民工,十年、八年前还是五六百块钱的月工资,现在都是几千块钱了。由于劳动成本持续增加,企业家都喊生产成本上升得太高太快了,所以很多产业要向东南亚转移。亚行和北大的一项合作研究认为,近年来实际工资的增长率已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因此我们显然不能说一线工人变穷了。那么,富人是不是变穷了?好像也不是。前两天我看央视评选的年度经济人物,大佬们赌一件不大的事情,张口就是拿一个亿起价,而现在一个贫困县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就是一个亿左右,所以富人显然也没有变穷。所以,我就不明白了:我们今天那么多重量级嘉宾高谈阔论“重返民富之路”,想说的是什么意思?
再回到我今天参加的这个分论坛的主题,叫作“深化财税分权”,这个我也没有搞太懂。财税分权这是政府内部的事情,政府研究财税分权,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经常开会,他们也不请我们去,人家自己把这个问题该讨论的都讨论了,真是用不着咱帮他们操心。中国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关系,如果和国际上比起来,比例很正常,跟别的国家差不多,中央财政占的比例并不算高,转移支付的情况其他国家也存在。我在英国生活很多年,它的中央财政的集中度比咱们还高,然后再做转移支付。中国的财税分权体制固然还有问题,比如需要减少专项转移,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故确有改进的余地,但中央和地方之间永远有矛盾、博弈,这似乎不是我们要研究的主要问题,不需要我们去为某级政府争利益。
从整体上说,中国的财政税收体制是有问题,而且是大问题。但很可惜,就如我们现在的城市化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国企国资问题、证券市场问题一样,媒体上讨论很热闹的往往并不是真问题,流行的反而是一些空话、套话甚至以偏概全、以假乱真的噱头。前几天一位媒体朋友对我说,好多话其实他们不采访自己也会说,只是迎合读者需要借名家之口罢了,因此他们自己去采访也觉得挺没劲。如果我们财经界拥有话语权的人落到这种空话、套话代言人的地步,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中国财政体制首要问题在于卖地财政
下面我先讲财政体制。中国的财政体制现在面对的首要问题是什么?我认为中国财政体制现在有三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解决卖地财政问题。财政收入中相当大的一块是非税收入,而不是税收收入。税收是国家的法定收入,非税收入本来就不够正规,只能是偶然性和零星性质的。非税收入搞这么大,这就很不正常。同时,我们这个非税收入非常重要的一块是靠倒卖土地得来的。我们学的是香港的办法,香港的地本来就是官地,就是港府的地,我们这儿还不是自己的地,是征收了农民的地倒卖,所以准确地说咱们不是土地财政,我们是“倒地财政”。
这个倒地财政我觉得是财政体制改革的第一件事情。有没有决心、有没有毅力来动这个倒地财政,这是新一届领导人在经济上第一个大的挑战。很可惜,媒体,包括学界,对这个问题说法不一,起码没有把它视为重要问题,更不是首要问题,而去扯一些什么分权之类的鸡毛蒜皮。在我看来,新一届政府的改革如果说在政治上是反腐败,那么在经济上面能不能有突破,第一个试金石、最重大的考验,就是对倒地财政采取什么态度。不先对自己开刀,土地乱局就不能拨乱反正。就目前来看,可以说“倒地财政”在新型城市化的口号下还在蓬勃发展,媒体也在推波助澜,市场上炒作的基本也都是这一套。
其实,倒卖土地的财政是和原来的旧式城市化配套的东西,新型城市化是不能搞这个的,这是财经媒体并没有搞清楚的事情。这就跟计划经济一样,计划经济是专门为那个“一大二公”时代配套的,现在倒卖土地的财政也是为少数人服务,不能给新型城市化配套的。2006年我曾经给政府提过批评和建议,我说你们讲的新农村建设不是当今这个时代的主要矛盾,21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是新型城市化建设,抓住新型城市化建设才是抓住了城乡统筹的龙头,相应的新农村建设才有空间和合理性。
那么,什么叫作新型城市化?原来那个旧在什么地方?这个新又新在何处?我觉得政府还只是刚开始有了点儿模糊的意识,如果媒体和学界自己更糊涂就没希望了。当时我说,新型城市化最主要的就是要新在不能光有数量没有质量上,这就需要解决城市的科学规划和布局问题,特别是解决人口和户籍问题。旧城市化的要害就是土地的城市化与人口和户籍的城市化脱节,少数人利用土地发财牟利,把地价房价搞得很高。现在要搞新型城市化,其核心就是要让土地为外来人口落户服务,让土地的成本、城市化的成本大大地降下来,这样农民工和其他外来人口才可能安居落户,人力资本才能积累提高。但是直到今天,我看过的所有的文件都还基本没有这个内容,媒体上渲染的也是开发商怎么疯狂拿地为了迎接新型城市化——那不是迎接新型城市化,那是迎接旧式城市化。因为新型城市化首要是解决人落户的问题,解决土地制度的改革怎么转过来的问题,从过去为大楼大广场服务、为开发商赚钱服务、为城中村和城郊农民补偿服务、为囤了土地和多套房的城市精英服务,转到低成本地为城市化的主体即农民工及其家属和其他外来移居的人口服务,这才是新型城市化的本质。
财政体制要为新型城市化服务,我认为要打的第一个大仗就是改变倒卖土地的财政,但是现在这方面可以说还没有什么准备。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准备和动作,所谓的新型城市化最后必然还是走老路,还是少部分人获益、大多数人被排挤在外的城市化,就是我们今天的状态。所以,我认为财政体制要改革,第一仗就是要动摇倒卖土地的财政。动摇这个东西会带出来一系列的问题,因为批评它是容易的,但是要替代它,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现在土地还在招拍挂,如果按照中央文件里面说的“严格区分公益性和非公益性用地”(当然这个口号其实也是有问题的)去做,很快就没有经营性土地可卖了,就不能招拍挂了,那么城市建设、城市发展怎么办?现在我们在这方面可以说没有做任何准备。没有准备就只能沿着现在这条老路走下去,一方面被迫付出的土地补偿费越来越高,一方面招拍挂又进一步推高城市土地和房产价格,结果只会造成土地资源的集中和一部分人的暴富,从而堆积越来越大的资产泡沫、地方债务和金融风险。
中国财富榜上有那么多大房地产开发商,这在世界上都是少有的——只有中国香港有,因为我们是从香港学来的拍地模式。这个模式就是把土地资源集中给少数大开发商,所以中国财富排行榜才会有这么多地产商,政府一说新型城市化,地产股都上涨。我说这完了,这不是新型城市化,这是旧式城市化。许多人没有意识到,新型城市化其实首先是对财政体制的重大挑战,即我们的财政体制用什么来替代过去我们称之为“土地财政”的旧模式?土地如果不用征收和拍卖的方式,用什么方式?现在又有新的建议,说可以搞城郊农民自主城市化,还有人推荐深圳原住民自发城市化的模式。但深圳富起来的只是城中村的农民,他们成了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深圳外来打工者是本地户籍人口的近十倍,房价那么高,有几个能安居?挤在工棚、握手楼和地下室里能叫安居吗?我们不能打着农民的旗号,为只占很少数的城郊农民谋利益。如果只是让少数人受益,只是让政府、开发商、城市精英以及城中村和城郊村农民这些既得利益者进一步分利,是解决不了新型城市化问题的。
这就是我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倒卖土地的财政问题。现在土地财政在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已经占很大比例,如果不从根本上动摇这一块,设计一套新的制度完全替代这一块,那么新型城市化拉动经济发展的设想就会完全落空,因为靠少数人发财拉动不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只有几亿农民工和他们在农村的家属、留守的儿童,还有大量从中小城镇转移到一线大城市的外来人口,这些人分享到了土地权利、住房权利、完全融入城市生活的权利,才会真正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才能够实现可持续增长。从根本上说,这本来并不是一个经济增长问题,而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和不可剥夺的权利。他们是国民,他们在这个城市有工作,就有给自己搭一个窝的权利。所以我认为财政体制第一个问题,也是最大的挑战,就是对倒卖土地财政的态度和措施。
财政资源的歧视性分配与特权分配
财政体制的第二个问题,是财政资源歧视性的分配。这些可能都不是现在媒体上讨论的热点,但我认为这是主要问题。我们中国之所以贫富差距大到今天的程度,除了市场本身的马太效应,很重要的是因为财政资源分配加重了一部分人更好、一部分人更差的境况。财政资源的分配首先跟刚才说的我们的住房分配有关系。我们城市保障房主要是针对户籍人口,外来就业人口基本上住在地下室和工棚里面,教育方面现在还在争论外来人口能不能参加本地高考的问题,医疗更是向城市人口特别是体制内人口倾斜,社会保障体系也是如此,这一切大大加剧了我们财产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客观地说,这一点是跟我们国家的计划经济历史相关联的,因为我们从计划经济时代保的就是城市户籍人口。当年很困难的时候,城市户籍人口有布票、有粮票、有油票,保证了至少最基本的供应,但其他人是没有的。我们的公共医疗资源主要是集中在城市,而且主要是集中在体制内,这些人口占据着绝大部分的医疗资源。所有这些过去习以为常的东西,跟我们的财政体制都是有关系的,就像广州市财政,稍微公开一点儿,马上暴露出来其财政里面有一部分资金,有几千万元是拨给省级或者市级机关幼儿园的,其实像这类财政资源分配严重不公平的现象太多了。其他国家财政资源的分配可以减弱市场本身分配所造成的差距,而我们的财政分配从整体上强化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这是我们财政体制的一个主要问题。
当然,这个改起来非常不容易,因为财政体制现在的分配完全是有利于城市居民的,特别是完全是有利于体制内人口的。体制内绝不仅仅是几百万公务员,更有文教卫生新闻出版等好几千万事业单位的从业人员,加上家属人就更多。这样会触动巨大的既得利益,其中就包括我们各界精英的利益,而且这绝不仅仅是权力精英,还包括我们的财经精英、艺术精英、体育精英、文化精英,都是这个体制的受益者,要动摇这个难度是很大的。所以,我一直说收入分配的改革第一步不能盲动,要放到后面逐步去撼动。
这是财政体制第二个主要问题,就是我们财政资源歧视性分配严重地强化了我们的贫富差距。
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财政资源的特权分配,这个就更难了。现在新一届领导班子开始了新一波的反腐败浪潮,受到了各方面的欢迎和好评。反腐败本来就很难了,但腐败还只是非法的权力滥用,而特权是合法的权力滥用,因为特权是法规承认的,因而可说是合法的。而反腐败要深入,最后肯定会触及特权。实际上从一开头就触及了,比如说过去领导一出门就要封路,现在不封路了。这个碰的是什么?这个碰的不是腐败,碰的是特权。当然,这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总之,一个反腐败,一个反特权,后者可谓更难。这两件事真做到了,政治改革就完成一多半了。
我们原来的财政分配体制是向特权倾斜的。举个办公楼的例子,最近有的地方把办公楼搞得富丽堂皇,比人民大会堂还气派。这不是个案,全国的办公楼都膨胀,这就涉及权力的滥用。我曾经去过日本众议院议员办公楼(日本众议院议员不是我们的人大代表,首先人少,只有几百人,更重要的是谁在议会里面占多数谁就能组成政府,所以议员是真正的权力精英,他们的众议院议员至少相当于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他们的办公室,每个议员一间房,当中挂一个布帘隔一下,秘书坐外面,他坐里面。我还上了一趟洗手间,厕所很小,不太方便。反观之下,我们的财政资源用在特权方面的太多了,从办公楼到各种各样的楼堂馆所,到各种各样的培训中心、疗养中心,到给各种各样的权贵安排的休息、疗养、出游的地方,再到各种高档消费和各类礼品的馈赠,这些就是三公消费中公开和隐蔽的地方,耗费了我们财政资源相当大的部分。另外巨大的一块,则是维稳和花钱买平安的财政开支,花费的随意荒唐和支出的天文数字,更是令人瞠目结舌。
所以,反腐败的深入必然要碰到对特权的限制,包括对人均办公面积的限制,更不用说办公以外大量的设施、安排等支出。我曾经应邀去参加过美国国务院开的会。美国国务院自己是没有地方招待的,找一个公关公司安排全部议程,客人来了安排在商业化的宾馆里面,会议都是在外面开,而我们基本上都是用自己限制对外的内部设施。
所以,真正的财政体制改革在我看来是这三大问题。首先要突破的,我认为是第一个土地财政问题,因为它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而且它的收益很明显。我们现在想要经济增长,想要持续发展,必须解决倒地财政的问题,否则就不能前进,其他的问题只能是循序渐进。所以财政体制的真正问题,根本不是什么中央和地方分权,地方的钱是不是少了一点。我想全世界都有这样的问题,其他国家也都是转移支付的,中央财政占大头,各个国家都是如此,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我们不值得在这上面耗费脑筋。关于财政问题我就简略地说这些。
中国税制的问题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
下面我再讲税制。如果说财政问题上是一片混乱,税制问题上则基本是错误思潮占主导。刚才我们的主持人还在说结构性减税只见结构不见减税,我觉得这个套话其实并不客观。因为营业税改增值税实际上就是在降低增值税税率,我们原来增值税都是17%,现在推广到服务业、交通运输业,把17%降到了7%、5%,实际上也确实会减相当一部分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