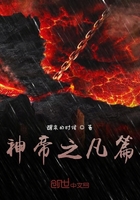意大利诗人贾科莫·利欧帕迪曾在书中声称,对古人而言,“悲情”这个概念是所谓“神圣的自然主义”的一种体现。这需要联系上下文来考察,即作为一种持续的辩护,为了反对利欧帕迪认定并强烈反对的在当代浪漫主义诗歌里存在的一种过度感伤的诗歌类型。对利欧帕迪而言,“自然主义”即激发读者(或观者)强烈感情的能力,也意味着在错综复杂的体裁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净化和宣泄情感的深层次的需要。
从文艺复兴的美学角度而言,一个类似拉斐尔的艺术家的“自然主义”,必须被视为以下两者的对应物:一是米开朗基罗很多作品里拥有的让人敬畏的力量;二是惯用一种格调的完全依赖于各种妙计及精湛绘画技艺的矫揉造作者。正如丹尼尔·阿拉赛指出的,对拉斐尔而言,“自然主义”就像优雅,是“一种表面上对艺术明显不屑而深处其实隐藏着艺术的自然优雅的结果”。
瓦萨里用“令人敬畏的力量”来正面地形容米开朗基罗与传统手法截然相反的了不起的表现力。但与这位艺术家同时代的某些人并不完全赞同,而认为米开朗基罗的作品缺乏“自我约束和尊重”,如果没有这种自我约束和尊重,任何艺术作品都无法称为优雅或真正伟大。他们批评米开朗基罗的作品“技艺精湛却单调乏味”—— 很不讨好地将其与以“多样化”和“丰富的独创性”为典型特征的拉斐尔作品进行比较—— 由此进一步赞美拉斐尔相比米开朗基罗的“天赋”。
“米开朗基罗总是试图寻找难以表现之处,而拉斐尔总是考虑实际创作上是否简易,以一种看似不费吹灰之力的方式创作作品。这正是完美的标准。最好的作家是那些写作对他们而言自然而然毫不费力的人。”在《关于绘画的对话》这本书的其中一个段落里,16世纪的学者洛多维科·多尔斯最早提出了利欧帕迪的观点,援引了维吉尔、西塞罗、彼特拉克和阿里欧斯托(Ariosto)为例证。
特别是在拉斐尔中年时期,他似乎主张“优雅”是绝对自然主义的产物这样一种观念。换言之,描绘题材是为了表现这些题材本质上的特性,无论是物质上或精神上,并在不过分注意其潜在的促使这个“真理”形成的代表性的专门技能的情况下,揭露所叙故事的“真理”。同时,拉斐尔也会注意从不冒险超越表现上的限制,以保证观者在他的作品里得到共鸣和亲近感而不是感到陌生和疏离,即拉斐尔的作品是隐藏着艺术的艺术之作。
使不可见成为可见一个可以代表拉斐尔的“自然主义”的光辉杰作是他的《弗利诺圣母》。
这幅祭坛装饰画是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一位怀有人道主义精神的朋友西吉斯蒙多·德·康蒂奉命于1511年底或1512年初创作完成的。西吉斯蒙多?德?康蒂是尤利乌斯二世的秘书,此外他还奉教皇之命监督了圣彼得大教堂的创作工作。
瓦萨里把这幅祭坛装饰画描述为命中注定是为罗马的阿拉科利圣玛利亚教堂的神圣祭坛而作。其创作者西吉斯蒙多也于1512年2月18日长眠于此。这座建于卡比托利欧山坡上的教堂,是献给圣母玛利亚以纪念她在基督诞生之时,在同一场地归于奥古斯都大帝的传奇性现身。这幅画中的圣母和圣子都笼罩在启示性的太阳光环之下的表现方式,其灵感来自于一座中世纪大教堂(毁于1564年)的教堂中殿里一位13世纪的艺术家皮耶罗?卡瓦利尼的绘画作品。
根据资助人的意愿,这幅祭坛装饰画要表现一种清晰的奉献性,即要传达一种明确的感恩之情。因此,圣母与圣子现身时下方的由彩虹形成的半圆形,包含了对弗利诺的理想化形象的明确指向,表现了河道、桥、塔楼和房屋,也包括西吉斯蒙多自身的居所,曾被闪电或陨石雨击中但幸运地留存下来。
在前景中央,一位天使举着一块上面题词已无处可寻的匾额。右边是这位艺术家的资助人,在保护者圣杰罗姆的陪同下,双膝跪地,热诚地祈祷着。在左边,施洗者圣约翰和圣弗朗西斯双目凝视并双手指向天国,在作品和教堂里的会众之间创造了一座生动有力的“桥梁”。换言之,这种捐赠者和圣徒献身式的姿势与作品的整体结构相结合,愈发增强对观者情绪的感染力。
圣母和圣子出现在前景上,像悬浮在发光的云层上,整体营造出一种周围人物离此幻象非常接近并被其光辉照亮的效果。一系列完整的光影使人将“令人激动的”情景和暴风雨逼近弗利诺之前的云层,与位于作品上方的托住圣母和许多天使的云层联系起来。这些天使本身也是用和云层一样的物质塑造表现出来的。
色彩和光线意想不到的相互作用赋予作品中各式各样的元素及背景风光一种不同寻常的完整和和谐感,消除了景物本身和其目击者之间可能存在的任何破裂感。此外,画中各种人物脸上流露出来的伤感,赋予圣杰罗姆“介绍”西吉斯蒙多?德?康蒂给圣母的那个约定俗成的仪式性姿势一种新的力度和强度。最重要的是,作品左边那两个人物的表情和姿势强调了拉斐尔要把教堂里的会众描绘进画中,使他们成为画中的一部分的意图,他企图通过描绘一个有示范效应的事件来提高和加强这些会众的献身意识。
图中吸引并抓住教堂会众目光的施洗者圣约翰这个人物,很明显地让人联想起列奥纳多·达·芬奇的作品;在这幅画中必须把他与背过身去面对圣母的圣弗朗西斯—— 正如瓦萨里指出的,描绘他时使用的色彩见证了他“燃烧与消耗善意与爱”的崇高境界—— 联系在一起观察。圣弗朗西斯左手握着一个小小的十字架,右手伸向会众,为他们祈求调解。他的这个姿势十分贴切,尤其是当观者回想起阿拉科利圣玛利亚教堂是在圣方济各教会的秩序下运行时,更进一步强调了作品与会众之间的联系,把后者带入传说中发生在此教堂中的历史事件之中。
《弗利诺圣母》标志着拉斐尔重新定位祭坛装饰画的角色和性质的重要一步,即作品与观者在物质上和情感上的关系。这个重新定位的过程,也与拉斐尔对教皇住所和西斯廷教堂的墙面上那些装饰性故事的戏剧性和“悲剧性”的潜质逐渐觉醒的过程平行进行。
拉斐尔在佛罗伦萨未创作完成的《伯得奇诺的圣母》,在对人物三维空间的调度上相当具有革新精神。然而,它依然坚持遵守了祭坛装饰画创作上基本的“建筑学”传统;这个传统始于皮耶罗·德拉·弗朗西斯卡为费德里科·达·蒙特费尔特罗创作的乌尔比诺装饰画,在15世纪后期及16世纪初期的意大利得到广泛认可。但在《弗利诺圣母》中,拉斐尔明确地远离了这一传统。这并不意味着拉斐尔认为这项传统毫无价值。《弗利诺圣母》本身很可能受了吉兰达约受托纳布欧尼(Tornabuoni)家族之托为位于佛罗伦萨圣玛利亚诺贝拉教堂创作的《玛利亚与圣徒们》的影响,此画起先藏于芒奇(Munch)的皮纳克提克美术馆(AltePinakothek)。然而,承认这些潜在的灵感来源,非但丝毫不能减弱《弗利诺圣母》的原创性和启发性力量,也不能降低拉斐尔企图让观者直接参与进来的尝试。拉斐尔坚持使用这种创作方式—— 直到晚期的作品《圣容显现》。
似乎拉斐尔刚刚创作完《弗利诺圣母》,就奉命开始创作另一幅圣坛装饰画。这次是为一个献给皮亚琴察的本笃会修道院的圣西克斯图斯教堂创作的。这位圣徒被视为迪莉亚·罗维尔(Delia Rovere)家族的保护者,而迪莉亚·罗维尔教皇,即尤利乌斯二世,在担任红衣主教的时候,曾为圣西克斯图斯教堂的重建做过贡献。拉斐尔可能在1512年间接受这个任务,与击败法国军队之后派遣过来重申城镇对教皇政权效忠的代表团的到来正好一致。
瓦萨里把《西斯廷圣母》形容为一幅“为皮亚琴察的圣西克斯图斯修士而做的独一无二和真正令人赞叹的描绘圣母、圣西克斯图斯和圣巴巴拉的圣坛装饰画作品”。关于这幅圣坛装饰画原意打算摆放的位置,有几个可代替的假设。比如,可能意欲放置在尤利乌斯二世的墓冢之上,也可能作为宗教游行时使用的旗帜,甚至可能被悬挂在教堂正厅,作为一扇可以窥见天国的象征性的“窗户”。其中的每种可能性都在某些因素上符合对该画作的研究结果,与画作构图上的某些特别之处也是相一致的。但所有的假设尚未经过当代史实文献证实。简言之,不存在什么充分理由去怀疑瓦萨里的判断,更何况从随后这幅装饰画的架构被摧毁这点来看,基本排除了画作和会众之间存在意欲达到的必然联系这种可能性。
与《弗利诺圣母》或拉斐尔在此之前的其他圣坛装饰画作品进行比较,《西斯廷圣母》最引人注目的革新之处,在于其创作过程之中完全放弃以陆地或其他固定物体作为参考系的方法。画中的圣母怀抱着婴儿基督从天堂降临,尽管沐浴在背景明亮的光线之中,圣母或圣子的头上都没有光环。圣母踏着裸足穿过云层走来,云层则像《弗利诺圣母》中的一样缓慢地显露出天使的样貌。从圣母垂下的长袍和她肢体的位置可见其动作的优雅。圣西克斯图斯的手势和圣巴巴拉避开的目光明确暗示了虔诚等待圣母降临的广大“会众们”。但拉斐尔拒绝描绘“底部”的情景,反而提升了祈求的圣徒的形象,使其成为神圣集体中的一部分。
对所有辅助性质的肖像绘画元素的彻底舍弃使得人们更容易集中和聚焦于这幅装饰画本身:它不再代表一件特定的事件,反而是在一种不同寻常的自然主义之下表现了“神的显现”(一种对神迹的呈现)。如果你接受“特异现象”(这暗示了一种强有力的和潜在的集体性经验)和“幻象”(具有杰出的智力性和主观性)这两者之间在神学上的区别,那么《西斯廷圣母》最好被定义为“一种特异现象的描绘”。这种解读也在对这幅装饰画的帷帘的研究上得到了确认。
把这幅装饰画作为“幻象”的这种频繁和经常的解读,主要是建立在陆地和天国相分离这个想法上—— 这种分离表现在画作底部的栏杆和画作两旁的帷帘上。关于装饰画两侧帷帘的重要性,只能在一种情况下得到解读,即这幅装饰画遵循了肖像绘画的创作传统,而这种传统拥有为数众多的先例,比如弗拉·安吉利可(Fra Angelico)的《圣坛装饰画》、皮耶罗·德拉·弗朗西斯卡的《帕托的圣母》以及佩鲁吉诺和拉斐尔更为熟悉的其父亲乔瓦尼·桑蒂的先例。这些形象使人回想起描绘安置在帷帘拉开的木质橱柜里的使徒们的肖像画,以及卡洛琳艺术和奥图艺术手稿中相似的使徒形象。它们的主旨也是常见的表现基督诞生和天使报喜的主题,也因此而具备了祈求最神圣的地方—— 耶路撒冷神殿的圣殿之中通过帘子与外殿隔开的内殿的神圣祭坛的典型价值。
圣母和圣子都目视前方,直接凝视着绘画之外的“会众”,基督躺在圣母像摇篮一样的臂弯中,像一个祭品。这些促使H. 格里姆(H. Grimme)把这幅装饰画和一本轮唱赞美诗集的祈祷词联系起来,比如Salve(西班牙“欢呼”)、Regina(拉丁语“皇后”),即“lllos tuos misericordos oculos ad nos converte”(请用您仁慈的双眼注视我们)和Ostende nobis Jesum(引领我们吧,基督)。在祈祷是殡葬仪式的一部分这个错误的观念之下,格里姆进一步提出《西斯廷圣母》与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墓冢之间存在某种方式的联系。
然而,就这件事件来说,在装饰画和《万福,圣母》之间建立一种联系至少给以下这种解读—— 即把圣母作为人类救赎这个戏剧性事件的调和者—— 增加了权重。应该说,不一定在死亡的那一刹那,尽管无可否认的是,这些前后之间的肖像研究都是建立在拉斐尔的圣坛装饰画和米开朗基罗为尤利乌斯二世之墓所作的以圣母和圣子为主题的雕塑作品之间的相似之处上。
总而言之,圣母在这些信徒的面前“现身”,从而向会众显示了她在通过基督化身和牺牲达到的对人类的救赎过程之中的核心角色。这幅画“超自然”的方面不再是纯粹的智力性和主观性的了:它具有明确的形式。
在致力于模仿的造型文化上,正如文艺复兴时期的大部分作品,要表现一种“特异现象”需要和这幅作品一样准确的形象。也就是说,要尽力表现它们所有的二元性以强调两个不同的“现实”板块的瞬间联系,因为其实它们可能风马牛不相及。称拉斐尔为“最客观的画家”是正确合理的;也正因此,他并不准备牺牲场景的内在自然性。相反,他决定忽略任何关于自然的虚幻性的展现,因其可能扭曲作品内部以及作品和观者之间的三维空间关系,并突出结构上动态的对称性。以这样的方式,拉斐尔实现了他的目标,即描绘有效“表现特异现象”的作品。
观者,即这些会众的位置,并没有被明确地界定。画面中没有一条有可能是表示地平线的线条,也没有任何对距离远近的暗示。观者的目光可能被栏杆和栏杆上两个向外望去的天使所吸引;也可能,他们的注意力会集中在圣西克斯图斯伸出去的双手上;或者,他们的目光停留在圣母和圣子这两个人物上。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视点或单一的角度,相反,它是多角度的。任何关于这片布满云层的模糊和无形的背景的距离感都会马上被近处实实在在存在的栏杆、罗马教皇的冠状头饰、固定住帷帘的栏杆和环状物,以及置于两侧的帷帘本身所打消。这一切共同导致画中的两位圣徒与圣母和圣子惊人地接近。
这些帷帘不仅仅在肖像描绘上十分重要:在整体构成上它们也是决定性的组成因素。它们与栏杆一起构成了这场幻象的“框架”,造成一种模棱两可和稍微互相矛盾的相互作用的视点,多多少少挑战了传统理性的解释。如果到了“真正的”框架被摧毁的程度,这幅装饰画的整体冲击力也只能被部分地重现了。然而,可以明确的是,拉斐尔使用了一种典型的文艺复兴式的“窗户”或框架来架构一个非典型和难以下定义的空间,并在这样一个空间里表现这场超自然的特异现象。远非通过勾画所占据的空间来固定物体,栏杆成为划分地面和天国两个领域的神秘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