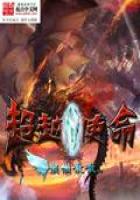对天生不是吃那碗饭的人。
抽一把剑让他抓,
扔些铜钱让他拿,
给人让他陷害了再医好,
给蛇让他去玩弄并诱惑。
他会被自己的剑刃所伤,
蛇会不听从他指挥,
本领的拙劣使他泄气,
受他愚弄的人嘲笑他!
天生的变戏法的可不同!
一撮灰土或一朵枯萎的花,
投来的水果或借来的杖,
足够他大显他的身手,
令人入迷神往或笑声大起。
The Jugglter’s Song。
跟着忽然有个自然的反应。
“现在只是我一个人-完全一个人,”他想,“全印度现在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茕然一身!要是我今天死掉,谁会传出噩耗而且传给谁?要是我活着,天对我好,就会有人悬赏我的头,因为我是一个符咒之子-我,基姆。”
极少白人但是许多亚洲人,只要反复叫自己的名字,就能使自己的脑筋毫无拘束地揣测所谓的个人面貌究竟是什么,人渐渐大了这种能力就消失,不过它有的时候随时会来。
“谁是基姆-基姆-基姆?”
他蹲在声音叮当的候车室一个角落里,心移神驰,不受其他念头所扰;两手交叠放在膝上,眼睛瞳仁眯成针头。再过一分钟-再过半秒钟,他觉得他就可以解出自己是谁的莫大疑团;可是在这里,情形总是如此,他的念头忽然像一只受伤的马一般、从崇高的境界蓦然跌落。他用手在眼睛前晃一晃,又摇摇头。原来是一位长发苦行者刚买了车票,在他面前突然停下,对他目不转睛地望。
“我也已失去了,”他黯然说,“那是得道之门之一,可是对我早就关闭了。”
“你讲些什么?”基姆赧然说。
“你元神出窍,在想自然的灵魂究竟是什么。这种念头是突如其来的。我知道,除了我以外别的人凭什么会知道?你到哪里去?”
“到凯安(贝纳尔靳)去。”
“那里没有神灵。这我已经证明了,我第五十次去普拉耶格(阿拉哈巴德)-寻找顿悟之道。你是信什么宗派的?”
“我也是个寻求者,”基姆说,那是喇嘛的口头禅。“不过-”他一时忘掉自己身上的北方服装,“不过只有真丰知道我寻求什么。”
车站上宣布到贝纳尔斯去的火车要开了,客人快上车。基姆站起来,那老圣者便把拐杖夹在腋下,坐在一块赤豹皮上。
“满怀着希望去吧,小兄弟。”他说,“走向世尊足下的道路长得很,可是我们人人都要到那里去。”
此后基姆便不怎么感觉孤寂了,在拥挤的火车上坐了才二十里路,他就讲起一连串关于他自己和他师父法术的极动听的故事,以使同车的人高兴了。
他再也没想到贝纳尔斯是个脏得出奇的城市,不过人人见到他的僧衣都很尊敬,这点倒令他觉得愉快。全城居民至少有三分之一经常求神拜佛,津崇各式各样的苦修圣者。基姆是由一个偶然碰到的旁遮布农夫指点来到特丹卡庙的,那庙在城外大约一里,离萨纳斯不远。那农民是属于坎波阶级,家居朱伦多尔道。他把家乡所有神祗都拜过了,求他们医好他的小儿子,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好试试贝纳尔斯看。
“你是从北方来的?”他像他家里那条心爱的公牛一样,排开又窄又臭的街道上的人群,问道。
“啊,我知道旁遮布。我母亲是个山地姑娘,我父亲是安里察尔省的亚拉人。”基姆油嘴滑舌地说那老走江湖的话。
“何处的亚拉-朱伦多尔?哎呀!那我们等于是邻居。”他对自己怀抱着的那个哭泣的孩子充满慈爱地点头,“你替谁服务?”
“特丹卡庙里一位极有圣德的人。”
“他们大都是极有圣德也极贪心的人。”那位贾特农夫愤然说,“我在多处寺庙里把脚都走得皮开肉绽,可是我那孩子一点都没好,他妈也病了……嘘,别做声,小宝贝……他发烧的时候我们替他换了一个名字。我们给他穿上女装……我们什么都做了,除了-他妈打发我到贝纳尔斯来的时候-她其实应该跟我一起来的-我说萨基·萨瓦苏丹对我们最灵验。我们知道他多么宽大仁慈,可是南边的这些神对我们是陌生的。”
那孩子在他父亲肌肉虬结的粗臂形成的软垫里转过身来,透过沉重眼睑望着基姆。
“难道都不灵验吗?”基姆轻松地带着兴趣问。
“都不灵验-都不灵验。”那孩子说,嘴唇烧得干裂。
“神至少给了他一个好脑筋,”那父亲得意地说,“再也没想到他那么聪明地听我们讲话。前面就是你那个庙。现在我穷了,许多和尚跟我打过交道-可是我的儿子究竟是我的儿子,要是把这个礼给你师父便能治好他的痛-我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基姆思量了一下,心里不无得意。三年前他会迅速利用情况赚到钱便毫不考虑地溜掉;如今那贾特农夫对他的尊敬证明他是个大人了,他自己也已尝过一两次这种发烧的滋味,而且一看就知道是饥饿造成的病象。
“你把他叫来,我会把我最好的一对公牛抵押给他,请他把我孩子的病治好。”
基姆在雕琢的厢门前停下。一个从阿兰米尔来的奥斯瓦尔阶级放债的刚消尽了放高利贷的罪,问他做什么。
“我是西藏圣者德秀喇嘛的弟子-他在庙里,是他叫我来的,我在外面等着,请你告诉他。”
“别忘了我的孩子,”那可怜的贾特人回过头来说,跟着又用旁遮布语大声喊道:“啊,圣者-啊,圣者的徒弟-啊,全世界的神灵-请看门口坐着病患!”这种哀号在贝纳尔斯遍处可闻,路人根本不理会。
那赎了罪与世人无忤的奥斯瓦尔发债的把话传到他身后黑暗处,那从容而不计究的东方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溜过去;因为喇嘛在他禅房里睡觉,没有僧人肯叫醒他。等到点球咔哒咔哒的声音又打破有塑像的内院恬静时,便有个沙弥轻轻说:“您的徒弟来了。”老喇嘛急忙神情肃穆的从阿罗汉神像所在的内院大步走出去,连祷辞也忘了收尾。
喇嘛修长的身子在庙门一出现,那贾特人便跑上去,举起他的孩子,喊道:“瞧瞧这孩子,圣者,如果神要他活下去,他就活得了-活得了!”
他在腰带里探索,掏出一枚小银币。
“什么事?”喇嘛的眼睛转注在基姆身上。他说的鸟尔都语显然比许久以前在那门参参玛大炮下清楚得多;可是那贾特人不给师徒谈话的机会。
“只不过是发烧罢了,”基姆说,“那孩子营养不良。”
“他吃什么都不舒服,他妈又不在这里。”“只要您答应,我可以治这个病,圣者。”
“什么!他们把你变成一个郎中了吗?等一等。”喇嘛说,一面在庙阶最低一级那贾特人身旁坐下。基姆一面用眼梢儿望,一面打开那小槟榔盒,他曾经在学校里梦想以洋大人面貌在喇嘛面前出现-先戏弄那老人一番,然后显露出自己的真面貌-这完全是孩子的梦想,他皱着眉在药瓶中找来找去的时候,这出戏还没有演完,停一停想一下,又不时念念有词。他有奎宁片和深褐色的肉汁片-极可能是牛肉做的,但是这不关他的事。那小孩不肯吃,只贪婪地吸吮肉汁片,说是它的味儿像盐。
“那么你拿这六片去,”基姆递给他,“赞美众神,把三片放在牛奶里煮;另外三片泡在水里。他喝了牛奶之后再给他这个(半粒奎宁丸),要把他盖得暖,给他另三片泡的水,等他醒了再把这白药丸的另半粒给他。这里还有一片褐色的药他一路可以吸吮回家。”
“神哪,多么高明!”那个贾特农夫一面迅速把药抓过去一面说。
基姆对于自己患秋疟时的治疗法只记得这么多-除了嘴里的念念有词,那是做给喇嘛看的。
“现在你走吧!明天早上再来。”
“可是医药费-医药费,”贾特农夫扭回他熊肩说,“我的儿子是我的命根子,现在您要是把他医好了’,我回去怎么对他妈说我在路边求医却连一碗奶酪都没给人聊表寸心?”
“这些贾特人,都一样。”基姆柔然说,“一个贾特人站在他的粪堆上,国王的象群走过。‘哦,赶驴的,这些小驴子你要卖多少钱?’”
那贾特人听了哈哈大笑,几乎气也透不上来,频向喇嘛道歉。“那是我们家乡的老话-一点不假。所以我们都是贾特人,我明天再带孩子来;愿土地公公保佑你们俩-他是很好的小神……现在儿呀,你可以又好了,别吐出来,小宝贝!我的心肝,别吐出来。你明天早上就会变得又壮又大,像摔角手和舞棒汉子那样。”
他连哼带唱地走开。喇嘛回顾基姆,细细的眼睛露出一片慈爱。
“医病是积功德。可是先要有这种学问,你做得很好,世界之友。”
“圣者,是你教导我的。”基姆说。他像回教徒那样弯腰屈膝去触摸那耆教庙口泥土中他师父的脚时,忘掉刚才所演的那一小出戏;忘掉圣查威尔学校;忘掉自己的白人血统;甚至于忘掉“大游戏”。“一切教导都是你赐给我的。我已经吃了你三年饭,我的训练时间过完了,我离开了学校、我现在到你这儿来。”
“我的报酬在此,进来!进来!一切都好吗?”他们穿过了内院,下午的斜阳映得那里一片金黄。“你站着别动,好让我看看。原来这么大了!”他仔细端详。“不再是个孩子而成了一个大人,满腹智慧,走起路来像医生。我干得好-那个黑夜里我把你放弃给那些武装的人,我干得好,你还记得我们在参-参玛大炮下那次相见的情景吗?”
“记得,”基姆说,“你还记得我跳下马来,一到了那-”
“那学问之门?完全记得,那天我们一起在勒克瑙河边吃糕。啊哈!你替我要过许多次饭,可是那天是我替你要饭。”
“很有道理,”基姆引述喇嘛当时的话,“我那时候是学问之门的学生,穿的是洋大人装,别忘了,圣者,”他戏谑地说,“我还是个洋大人-凭你恩惠。”
“对,一位极受尊敬的洋大人,到我的禅房来,徒弟。”
“你怎么知道的?”
喇嘛微笑:“先是我们在兵营里碰见的好心苦僧人来信,可是他现在回团了,我便把钱寄给他兄弟。”在维克托神父随着团队回英国之后,克莱顿上校就成了基姆的监护人,不过他并非维克托神父的兄弟。“可是我看不懂洋大人的信。必须翻译给我听,于是我选了一个更稳当的办法。许多次我寻求归来,回到这个对我永远是安乐窝的庙,便有一个企求悟道的人-一个从列亚来的人,他说他以前是印度教徒,可是对那些神祗实在厌腻了。”喇嘛指着那些阿罗汉。
“是一个大胖子吗?”基姆眼睛闪出异彩。
“非常肥胖,可是我有点察觉他一脑门子尽是没有用的东西-例如魔鬼、符咒和我们寺庙里喝茶的礼节和方式以及训练沙弥的途径等等。一个非常好问的人。可是他是你的朋友,徒弟,他告诉我你将成为一个很有地位的书记,我现在看到你成了医生。”
“不错,当我是洋大人的时候,我是个书记。可是以你的徒弟身份来的时候,就不是了。我已完成了一个洋大人规定要受的训练。”
“就像一个沙弥吗?”喇嘛问,一面点头,“你是不是已经读完了学校?我可不要你没有修完。”
“我已经完全读完了,将要在政府担任书记-”
“不是个战士,那好。”
“可是我先来跟你一起去漫游。所以我到这儿来。这些日子谁替你行乞?”他说得很快,这个问题问得他战战兢兢。
“我常常自己行乞。可是你知道,我除了再去看我的徒弟,很少在这里,我从印度这头走到那头,有时徒步有时坐火车,真是美妙的大地方!可是这里,我一来住的时候,就像在自己的西藏老家。”
他向干净的小禅房环顾一下,颇为自得,有个蒲团,他盘膝趺坐在上面,面前有张不到二十寸高的柚木茶几,上面放着铜茶杯。一个角落里有个小祭坛,也是雕花柚木的,上面供着一尊镀金的如来佛像,佛像前面有一盏灯,一个香炉和一对铜花瓶。
“一年以前,妙屋那位佛像画片看管人把这些给我,积积功德,”喇嘛跟着基姆的眼睛看去,“一个人远离家乡,这些东西带来了乡土之念;我们必须敬佛因为它点出迷津,你瞧!”他指着五颜六色的米堆,上面有个奇形怪状的金属饰件。“我在获得比较清楚的证实之前,是我自己寺庙里的住持,每天都以这个祭佛。这是把整个宇宙奉献给世尊。我们西藏人就是这样每天把整个世界献给妙法。我现在虽然知道妙法不是烧香念佛就能得到的,现在还是这样做。”他闻闻鼻烟。
“做得好,圣者。”基姆低声说,他朝垫子上一坐,非常愉快也实在累。
“而且,”喇嘛笑说,“我也绘制轮回图,三天画一幅。他们带来你的消息的时候,我不是在忙着画图,就是在稍微闭一会儿眼睛养神。有你在这里真好,我一定向你表演,不是为了自美,而且因为你必须学习。洋大人并没有这世界所有的智慧。”
他从几下抽出一张有异香的黄色中国纸、笔和一锭印度墨,他以极简洁的轮廓画出六幅巨轮,当中是相连的猪、蛇和鹄(愚、嗔及慾),每一格里都是天堂与地狱以及人生的一切机会。人们说是佛陀自己率先用谷粒在灰中画的以教导弟子一切因果。自古以来已把它结晶成最美妙的习俗,圆中充斥千万个小圆形,每根线条都有意义,没有几个人能诠释这种图画式的比喻;全世界只有二十人能不依样描绘而画得一笔不讹;至于既能画又能诠释的则只有三人。
“我已经稍微学了一点绘图,”基姆说,“可是这个实在是妙得无以附加。”
“我制图已有多年,”喇嘛说,“从前只要在两次点灯的时间之门就能完成一幅,我将把制图之道传授给你-不过要经过适当的准备。我还要把它的意义讲给你听。”
“那么我们先去漫游?”
“一面漫游一面搜寻。我只是等你来一起出发。我得过一百次梦,每次梦里都说得清清楚楚-尤其是那学问之门初次把你关起那天晚上所得的梦-没有你我永远找不到我的河,你知道,我一再排除这种想法,生怕这只是个幻念。因此那天我们在勒克瑙一块吃糕的时候,我不肯带你走,我一定要等到时机成熟而且吉利的时候才带你走。我曾经从山走到海,又从海走到山,可是始终白费功夫,后来我记起本生经的故事。”
他向基姆说出他常对耆那僧人讲的象与足镣的故事。
“不再需要什么证明了,”他恬然说完,“你是奉派来援助我的,没有你援助,我的搜寻是白费功夫,所以我们将再度一起出门,我们的搜寻一定有把握。”
“我们到哪里去?”
“这有什么相干,世界之友,我说寻求白有把握,必要的话,河水会在我们面前从地里涌出。我把你送往学问之门去,并且使你获得智慧之宝。你的确回来了,我现在就可以看到一个医王信徒,医王的神坛在西藏很多,这就够了。我们如今在一起,一切都跟从前一样-世界之友-星辰之友-我的徒弟!”
他们然后讲起俗事。值得注意的是那喇嘛从不询问在圣查威尔学校里生活详情,对洋大人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也一点不好奇。他的脑子完全想的是以往的事,追忆他们第一次的美妙旅行的每一步,一面搓手低笑,直到像一般老年人那样忽然蜷作一团睡去。
基姆望着尘埃飞舞的残阳余晖在内院中消逝。把弄他的鬼匕和念珠。贝纳尔斯在神祗面前苏醒的世间最老城市,市籁昼夜喧嚣,声撼墙垣,就像海浪拍堤。偶尔有个耆那僧人走过内院捧着一点东西祭神,一面走一面扫视,惟恐伤生。一盏油灯亮起,晚课声随之而来。基姆注视星星在深沉浓黑的暮色中一个一个升起,直到后来在祭坛脚下昏昏睡去,那天夜晚他梦中所说的都是印度语,没有一个英国字……
“圣者,有个昨日施药给他孩子的要来。”他说,那时是凌晨三时,喇嘛一醒了就要出发上路。“天亮时那个贾特人会到这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