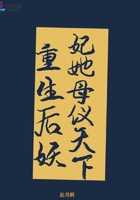画屏来给郡主取书,等画屏拿书走人,蜻蜓急忙回头去找云奂,却只找到他绑头发的一根丝带。
蜻蜓满腔甜蜜顿时化成苦涩,她在藏书楼一圈圈乱转,越想越觉得没有底气。
他没有回答她的话,最后她亲他的时候感到他有些心不在焉,是他不想和她一起离开王府还是他已经看穿了她的性别?
随后几天云奂始终没来找她。
蜻蜓拎着酒壶倚门而立,浑身酒气。她没吃解酒药,去找贺小莺要钟情丹的念头也打消了,甚至觉得自己先前的想法十分可笑,把绣花枕头拘禁在身边岂不是等于限制了自己的自由?
她知道王府对她来说并不安全,尽快离开这里才是最稳妥的选择,可是在云奂给她答复之前她不能走,她要等他亲口告诉她答案,即使最后死在王爷手上她也还是要等。
放到一个月以前,如果有谁告诉她会为了相识不久的人痴迷发狂,甚至不惜搭上性命,她一定认为那人是个疯子,可悲的是现在她就成了那样的疯子。
时间如此难熬,每一秒钟都变得那么漫长,充满了失落、焦虑和思念。
并未想过逃避,可也不想过得太清醒。
一壶酒很快喝光,她将酒壶丢到一边,微微低着头,纤细的手指按压着酸涨的太阳穴。片刻之后,她迷迷糊糊地看见王爷的忠实干将也就是王府护卫首领丁耀文横眉冷目地大步走了过来。
丁耀文早就认定了蜻蜓对王爷动机不良,对她一直没什么好脸色,此时见她公然在藏书楼喝酒,脸立刻阴得比锅底还黑,“沈石,你的职责是看守藏书楼,怎么能在这里喝酒?”
蜻蜓一阵不耐烦,口齿不清地抗议,“沈大头领,你什么时候……管到我……我头上来,难道你不当......护卫首领,改当管......管事啦?”上前将手搭在他肩上,“我跟你说,别看我只是......看守......藏书楼,也不轻松,不信你......来试试。”
丁耀文嫌弃地甩开她手,差点把她掀个趔趄。
“沈石,把你那副醉鬼的模样收敛收敛,随我去面见王爷。”
蜻蜓靠在墙上,笑嘻嘻地伸指点了点他,“你去告诉那个……绣花枕头,我很忙,没空搭理他。”
丁耀文伸手握住腰间的刀柄,“大胆奴才,你敢对王爷不敬?”
蜻蜓晃晃手指,“不不不——”慢慢摇了摇头,“我不是奴才,你……才是奴才。”
丁耀文大怒,握着刀的手猛然抬起,正午的阳光射到雪亮的刀身上,杀气弥漫。
蜻蜓哈哈一笑,“你这是要杀我?”
她是真的醉了,不但没跑,还向前进了一步,“你杀啊,不动手你就是……狗熊,就是王……八蛋!”
丁耀文握刀的手青筋暴起,目光中凶气涌动,但是他最终还是收刀入鞘。
杀沈石的理由有一万个,不杀沈石的理由只有一个——他不能违背王爷的旨意。
他森然说道,“要不是王爷下令不准动你,我今天非杀你不可。”
蜻蜓快要笑死了,“大笨蛋,我告诉你吧,他骗……你的,他想杀我,他……想杀我。”
丁耀文不再跟她废话,拽住她的胳膊把她扔进一边的轿子,而后对几名轿夫下了命令,“把这家伙抬过去。”
蜻蜓醒来时已经到了掌灯时分。
她撑着头坐起身,只觉得口干舌燥,胃也难受得厉害。
打起精神看看四周,奢华至极的桌椅床塌,旁边低垂的金丝锦帐,熏香炉中绵软的清香,这里无疑是王爷在南楼的卧房。
她怎么会在这里,还躺在王爷的床上?依那个绣花枕头的脾气应该把她扔在地上才对。
她费力地想了半天,依稀记起来丁耀文好象说了句王爷下令不准动她。或许真象云奂说的,她误会了王爷?
蜻蜓不知不觉中微微一笑,心情骤然好了很多。
想起自己曾在黑暗中和解子殊两手相握,异样的感觉再次从心底生起,就象一道无形的影子,无法捉摸,令人困惑。她有些意外,刻意忽略掉了那种感觉,将全部的心思重新转移到了云奂身上。
她担心在她离开藏书楼的这段时间云奂会去找她,当即决定趁王爷不在赶紧溜回去。
结果还没走到门口就听见王爷在外面问话。
“他还睡着?”
一个怯生生的少女声音,“奴婢刚才进去看过了,他还没醒。”
她话音未落,王爷已经走进房里。
蜻蜓垂手站在一旁,战战兢兢地看了王爷一眼,“小的喝酒误事,请王爷赎罪。”
王爷怔了怔,“你醒了?”
蜻蜓的不安倒不全是装出来的,这会儿她已经把自己喝醉时对丁耀文说的话想起了七七八八,暗地里猜测丁耀文一定向王爷揭发了她叫王爷绣花枕头这事。既然王爷没想过要杀她,那她何苦要得罪他?这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王爷缓缓踱在她背后,一只手不轻不重地放在她左肩上,“听说有人给本王起了个绰号,你想不想听听?”
蜻蜓厚着脸皮胡扯,决心来个死不认帐,“王爷英明神武,不是威武响亮的绰号绝对配不上王爷。”
“哦?是么?”修长的手指移到蜻蜓颈边,有一下没一下地抚摸着她散落在那里的长发,“他叫我......绣花枕头。”
蜻蜓呆了一呆,倒不是因为他说出的话,而是他指尖的触感格外熟悉,那种感觉随之卷土重来,这次任凭她如何努力也无法忽视了。
她定了定神,小心翼翼地避开他,转身干笑两声,“说这话的人一定是个丑八怪,明摆着是嫉妒王爷英俊潇洒风度翩翩,照小的看王爷根本犯不着跟这种人一般见识。”
王爷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她,良久,轻轻吐出三个字,“小骗子。”
蜻蜓有些发懵,他那句“小骗子”明显是在说她,可是他说话的语气十分奇怪,似乎很无奈很生气,却又带着明显的妥协和纵容,几乎象是在对闹了别扭的情人说话。
蜻蜓心里怦怦乱跳,这样实在太奇怪了。她不自觉地后退几步,磕磕巴巴地说,“王爷,要是没......没什么事,小的先......先回去了。”
“你等等。”
解子殊走到她身边,轻轻摸了摸她左面的脸颊,“这里划伤了,怎么弄的?”
蜻蜓白天喝酒的时候迷迷糊糊地摔了一跤,脸都被划破了,当时也没在意,他一说她才想起来。
“没事儿,就一个小口儿,反正也不疼。”
解子殊微微皱起眉,“怎么这么不小心?你站着别动,我给你上点儿药。”
蜻蜓正琢磨着他今天是不是吃错了药,微凉的带着一股清香气息的药膏已经涂到了伤口上。解子殊比她高出一头,给她上药的时候微微弯着腰,眼神中透出不容错认的疼惜。
他们之间离得那样近,近得几乎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蜻蜓浑身僵硬,浑身的血液都冲到了头上。
他侧过头,在她的伤口上轻轻吹了吹,然后抬起眼睛仔细看了看她,一只手抚上她的脸颊。
蜻蜓心里突突乱跳,过了好一会儿才如梦苏醒,猛地推开他,转身冲出门外。
刚才解子殊抚摸她的时候,她竟然不由自主将脸颊地贴近了他的手心,虽然只是很短的一瞬,他也一定感觉到了,因为他的眼睛在那一刻蓦地睁大,似乎十分高兴。
绣花枕头吃错药也就算了,落蜻蜓也吃错了药?一定是酒喝的太多了才会这样。娘的,古人不是早就云过酒后乱性么?她怎么就没当回事?蜻蜓抱住脑袋一阵猛捶,大骂自己是个猪头三。
在外面转悠了半天,回到藏书楼时已经是深夜,一上楼就看见云奂伏在桌上睡着,漆黑的长发散在精致的雪裘上,头枕着右手手臂。
蜻蜓的心立刻化成了一汪春水,慢慢走过去挨着他坐下,心想虽然她酒后乱了那么一小下,但幸好没做什么对不起大美人的事,以后一定要引以为鉴,千万不能再胡乱喝酒了。
她握起自己胸前的一缕头发,用发尖在云奂脖颈上轻轻拨了拨,云奂动也不动,依然睡得很沉。她凑近了一些,刚想再拨,云奂伸手搂住了她的腰,但仍伏在桌上没有起来,只是张开眼睛望着她温柔一笑。
蜻蜓学着他的样子伏在桌上,痴痴地凝视着他。
云奂轻声问,“你去哪儿了?”
“我在外面......转转。”
云奂坐起身,毫不费力地把她抱到怀里,“转够了才回来?”
蜻蜓不习惯坐在他腿上,脸腾地一红,“你......你什么时候来的?”
云奂想了想,“我来的时候,月亮在树梢那里。”
现在已经月上中天。
蜻蜓先是内疚让他等了那么长时间,随后又一阵紧张——那天的问题,不知他会给她一个怎样的答案?
蜻蜓有个毛病,越是紧张越想表现得轻松一些,她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问,“你考虑好了没有?”
“考虑好了......”
“等等,”蜻蜓将他上次遗留的丝带放到桌上,嘿嘿干笑两声,“我数三个数,你把它拿走就代表不愿意,三个数数完你要是不拿,我可就当你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