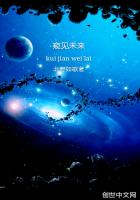黄昏时分,表哥用一辆板车拉回了“现行反革命”大憨和二憨的尸体。悲痛压弯了他的腰,他像头苍老的牛那样迟滞地行走着。身后的板车上躺着两具遍体鳞伤的尸体,兄弟俩的头僵硬地枕在母亲的腿上,表妹俯下身,一动不动地凝视她的儿子,仿佛要看着他们复活。大颗的眼泪一滴一滴掉在他们青紫的脸上。
表哥向伫立在街道两边的居民们凄凉地笑了,说道:“我的儿子死了,大伙……清净了……”
陈雨燕在过了十七年养尊处优的日子后,遭受塌天大祸。
由于“踢开党委闹革命”,她的“管十个吃咸鸭蛋老蒋”的高干父亲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活标本”,母亲则是“美蒋加苏修”的“双料特务”,双双关进“牛棚”,由一伙四肢发达的“四四”派红卫兵严加看管,家也抄了。突遭变故的陈雨燕像迎头挨了一板砖,先是被打懵了,之后才有了痛觉
父母被清理出党后,陈雨燕也被清理出红卫兵组织。“红造”副司令艾红旗(原名艾红菊)带领三位“女干将”气势汹汹找到她。艾红旗抬手抹掉陈雨燕的绿军帽——
“你也配!”一记耳光扇过去。
一把撸下臂上的袖章——“你也配!”一记耳光扇过去。
又一把拽掉胸前的像章——“你也配!”一记耳光扇过去。
再一把扽开武装带——“你也配!”一记耳光扇过去。
三个红卫兵轮番上阵抽她的脸,“你也配!”
陈雨燕捂着浮肿的脸,颤声道:“我……我已经划清界限了。”
“那也不行!”艾红旗叉着腰喝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你长得就像大毒草林美兰!”一个女红卫兵指着她的鼻子说。
“勾引得革命男生只看你,不看别人!”另一个女红卫兵充满怨妇的愤恨,“批判地看!”她补充道。
陈雨燕一夜之间沦为“接受改造的子女”,每天在根正苗红的红卫兵的监管下,写关于父母“反动夫妻二人店”的罪行录。艾红旗隔三差五地来审查一回,扇上几耳光,用她的话说——
“我三天不抽你手就痒。”
陈雨燕娇嫩的脸上青紫交加,她一辈子也没有挨过这么多的耳光,这还其次,更糟糕的是所有人都跟她保持了距离,害怕惹火烧身,担上与“黑五类子女”同流合污的罪名。“批判地看”她的革命男生则放肆地吹着口哨——
“燕子,雨燕,陈雨燕……嘿,陈圆圆!走那么快干嘛,还当自己是根葱,等着谁拿你蘸酱呐!”
一个癞痢头的“红五类”男生觉得有机可乘,庄严地递上一张字条:与我私奔。
遭受三重打击的陈雨燕常常的发呆、叹息,还喃喃自语,有点像魔怔了。
其间,欧司令曾来巡视过两次,他背着手在陈雨燕面前踱来踱去,替她惋惜: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哇……”
他用一贯严肃的口吻对陈雨燕说:“如果你还有什么重要的问题需要交待,可以单独向我汇报……还有,你的父母也归我管。”已升任“联造”参谋长的欧晓南双眼放光。
“红造”三连内也展开了针对陈雨燕“深挖资产阶级根苗”的帮教批判会。其实,文化大革命到这个份上,谁都看明白了,就是找活靶子,群起而攻之打成筛子,证明自己的“革命立场”了事,可一根筋的罗夏萍还往“灵魂深处”联想呢。
罗指导员作了开场白——“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会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为帮助陈雨燕改正身上的不良作风和思想,使她回到正确的人生轨迹上来,下面请大家踊跃发言。”
与陈雨燕有积怨的陈冬花首先站了起来,厉声斥责:“陈雨燕的父母对党和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是历史罪人!可陈雨燕为什么直到今天才与他们划清界限?过去的日子里却沆瀣一气?毛主席说过,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她的立场显而易见!我的话讲完了。”
“说的非常好!”罗夏萍赞扬道,“陈雨燕不能决然一刀两断,说明她的侥幸心理和消极的革命态度。”她在小本上记下这一条。
结巴的劳动委员也站起来发言:“陈雨燕在大、大、大扫除的时候,拈轻怕重,不、不干重活,还边干边哼小曲,都是靡、靡、靡靡之音,不热爱劳动还算什么劳、劳动人民?问、问、问题严重!”
他说得青筋暴跳,害得罗指导员也跟着口吃:“你你你说得很对,这是资产阶级享乐主义和不劳而获的思想在作怪。”
轮到刘丽发言了,明显的底气不足:“嗯,我注意到,陈雨燕的袜子上没有破洞,旧袜子她就不穿了,也不缝补,换新的,太浪费了,应该节约闹革命嘛。”
“是啊。”罗夏萍扶扶眼镜感慨道,“一双小小的袜子就能看出人的本质,有没有破洞,有没有补丁,就是有没有艰苦朴素的革命观,雷锋同志的袜子上就打了很多补丁。陈雨燕,同志们的意见你听清了吗?”
“听清楚了,以后我穿破袜子……”
土肥站了起来,抓耳挠腮想了半天才说:“陈雨燕的绰号叫洋娃娃,顾名思义,就是洋人的娃娃,说明她崇洋媚外,对自己的祖国……”
钟鱼越听越离谱,挥手打断他:“得了,贾洪军,别瞧着别人的脸脏,看不见自己的满身屎,你的绰号还叫土肥呢,一特务,牛端午还叫牛二呢,一泼皮,都他妈超级反革命!”
肖巧狠狠瞪了他一眼说:“你还叫赤鱼头呢!”
钟鱼摆摆手——“别冲我来啊,干嘛呀,演双簧,唱夫妻双双把家还呐?”
“你嘴巴干净点!”
“到底谁不干净!”
罗夏萍急忙出来打圆场:“革命队伍要团结!开陈雨燕的帮教会,你俩吵什么?要吵出去吵!”
“你没听见赤鱼头说什么!?”
“你也有不对的地方!一个巴掌拍不响。”
“罗眼镜,你别里外装好人!谁不团结?谁搞分裂?你开陈雨燕的批斗会,控诉人家十大罪状,同学这么多年,你也不脸红?”
罗夏萍霍地站了起来,“你这话什么意思!”
肖巧也站了起来,“没什么意思!”
牛二看着剑拔弩张的两人,嘿嘿一笑:“我早就说过不要开什么废话连篇的辩论会,窝里反了吧?革命嘛,就要真刀真枪的暴动!哎,你们知道什么叫造反嘛?”
“什么叫造反?”众人洗耳恭听。
牛二跳下课桌,“造反就是——”“刷”来了一个标准的忠字舞亮相,“吃他娘,喝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
一片哄堂大笑,连挨斗的陈雨燕也低头窃笑不已,批斗会在闹剧中草草收场。
钟鱼注意到,在整个过程中魏援朝始终阴着脸一言不发。
因为陈雨燕一直没有找欧司令“单独汇报”,艾红旗被指使的寻衅也从未停止过。这一天,艾红旗一干人又来进行例行的审查,顺便止止痒。今天的题目是:《深夜不平静——特务母亲给谁发报?》,一个铁定让陈雨燕挨抽的题目。艾红旗磕着瓜子,悠闲地把瓜子壳吐到她头上和脖领里。
魏援朝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艾红旗的身后,用指头点点她的肩膀说:
“差不多了,该歇歇了吧?”
“我不累,为革命再累也甘心。”艾红旗自豪地说。
魏援朝铁青着脸绕到陈雨燕身旁,从桌上拿起墨水瓶看了看说:“墨水快干了。”
他放下墨水瓶,右手从腰间抽出一把匕首,伸出左手,对准食指“蹭”一刀切下去。
“哎哟!”众女兵一片惊呼。
一股血流蚯蚓般地顺着食指滴落进墨水瓶。
魏援朝面不改色,又挥刀对准中指切下去,不是“蹭”地一挥而就,而是缓慢地“蹭——”地剌开。刀口很深,割断了肌腱,白生生地翻开,三秒钟后鲜血才急遽地涌出。皮开肉绽的细腻展示骇得众女兵脸色惨白,浑身发抖。
他再次挥刀,“蹭——”地切割了自己的无名指,像切黄瓜那样无知无畏,延长了自己的痛觉,震撼了旁人的视觉。三股殷红的血汩汩汇聚一处,“嗒嗒嗒”地滴进墨水瓶,很快灌满了。
众女兵抱成一团,艾红旗哆嗦着嘴唇问:“你……你想干什么?”
魏援朝瞟了她一眼,平静地说:“墨水瓶干了,有血,我的血干了,还有别人的血。”——
“嘭!”他把匕首扎在课桌上,盯着艾红旗脖颈突突跳动的动脉血管。
艾红旗落荒而逃,神色紧张地向欧司令报告魏援朝的“割指救美”:
“三连的魏大叔,哦,不,魏胡子,他到底多大岁数?……他放了自己的血,还扬言放我的血,怎么办?怎么办?!”
欧晓南怔大眼睛,张着嘴巴,然后拍案而起,正要发作,猛然看到对面墙上他手书的条幅:慎思。他又缓缓坐下了,扶着额头开口道:
“此事暂缓。”
“他同情反动子女,向革命组织示威,就这么算了?”
欧晓南看一眼艾红旗,这个暴牙齿的“亲密战友”没有爱情经历,自然不明白“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他叹了一口气说:“暂缓,暂缓吧……”
悲情诗人独自发了半天愣,在“革命日志”里痛苦地写下“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他用鲜血浇灌了它。”
魏援朝自戕的“三刀”得到了陈雨燕的悉心包扎,钟鱼看到他的表情“痛并快乐着。”
“一切牛鬼蛇神”被统统打倒,再踏上一万只脚后,玉宇澄清万里埃,红卫兵小将们胜利“夺权”。可是掌了权的用******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战士却像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军一样开始内讧,各自为王。“红造”内部也是派系林立,呼拉拉冒出一片各种名目的造反团队;“红一军团”,“风展红旗先锋队”,“反资灭修战斗队”,“井冈山赤卫队”,“驱虎豹英雄连”,“狼牙山五壮士。”连欧晓南的亲密战友艾红旗都打出了“映山红女子造反团”的旗号。尽管“红造”司令欧晓南声嘶力竭地呼吁“只有众人团结如一人,才能试看天下谁能敌。”但是“欧氏”造反团仍不可避免地土崩瓦解,大势已去。
魏援朝熟读兵书,深知“乱世出英雄,时势造豪杰”,顺势而动,成立了“长缨在手战斗团”,人马是原“红造”三连的人,魏援朝自任司令,牛二副司令,还别出心裁地设了一名“旗手”。钟鱼深谙魏援朝的军人梦,蛊惑他说:
“老魏,建制不全呐,差一名旗手。”
“什么旗手?干嘛的?”
“军衔呗,副司令级,你想,海军有旗舰,陆军有军旗,空军有旗语,造反团不得有旗手?显得正规。”
“也是……那谁当合适?”
“谁比我更合适?”
指导员罗夏萍激烈抨击这种“山大王似的举动”,可大家还是愿意跟义气笃厚的“魏三刀”闹革命。
各造反团之间互相倾轧,党同伐异,争斗进入白热化,从辩论会到群殴几乎不存在过渡时间,“红一军团”率先贴出一张大字报,揭发“驱虎豹英雄连”连副的父亲过去曾是国民党旅长家的厨子,“奴颜婢膝地位反动派尽忠”,把他养得白白胖胖,去屠杀革命志士。并由此上溯到一九00年,从那时起,他的爷爷就在满清走狗的厨房里卖命了——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驱虎豹英雄连”迅速回击,贴出了“杨彭氏的包子店生意为什么那么好?很不正常!!”的一张大字报,经过一系列合理的假定推测,得出“红一军团”司令的母亲是“破鞋”的定论——“包子出笼了,牛鬼蛇神出笼了吗?”
大规模火拼随即开始,双方皮带狂舞,砖头乱飞,酒瓶猛砸,都有人头破血流,躺进医院。
那边“狼牙山五壮士”与“反资灭修战斗队”一言不合,抡起“狼牙棒”将“反队”队长后背砸出一百多钉子眼。“反队”倾巢出动,五十多人前去寻仇,双方的决战在水泥厂的空地上展开。“狼牙山五壮士”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以为可以以一当十,结果一场混战后,“五壮士”全被撩翻在地。
欧晓南的“红色造反团”和原学生会副主席的“风展红旗先锋队”更是水火不容,两人一直面和心不合,从前共事时脸上挂着的都是外交家式的微笑。他们有一个共性:都对明火执仗的“杂牌”造反团不屑一顾,认为自己领导的才是唯一“正规”的革命造反团。矛盾产生了:“唯一”和“唯二”的势不两立。“风展红旗”的“神枪手”夜袭“红造”司令部,用气枪在两位副司令的屁股上又开了一个洞。第二天,“神枪手”便被自制土雷炸成龟田小队长,自此冤冤相报无尽期。
“映山红女子造反团”是最摇摆不定的一个,由于女人的特性,她们很难“独立”。最初她们依附于“狼牙山五壮士”,因为“五壮士”个个彪悍,看上去很有安全感,不料这么快就被翦除。转而投靠“红一军团”,可“一军团”在与“驱虎豹”持续的火拼中渐渐势弱,她们常常遭到“驱虎豹英雄连”的调戏。马上风向一变,加盟“风展红旗先锋队”,因为他们手里有“枪”,枪杆子里出政权嘛,谁想到“神枪手”又被炸得鲜血迸流。这支“红色娘子军”墙头草似的串场并没有使自己发展壮大,反而有两位战友在转战途中搞大了肚皮,退出战斗。她们因此落下一个不雅的绰号:“映山红破鞋造反团”。
相比之下,“长缨”显得安分多了,从不参加派系间的武斗。魏援朝谋略过人,满脑袋战国七雄的霸业思维,深谙在“鹤蚌相争,渔翁得利。”他捋着胡须道——自打当上司令养成的习惯动作,刘备是向下捋胡须,魏援朝的络腮胡长在两边,只能左右捋——“自古为将,贵于持重;两军对阵,戒于轻动。”对于屠夫型副司令牛二的蠢蠢欲动,魏援朝意味深长地告诫: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
当“映山红女子造反团”有意投靠是,众人心花怒放,两眼放光,魏援朝立刻左右捋着胡须斥责:
“胡涂!红颜祸水,君等不见董卓、吕布、夫差、隆基之事乎!”
魏援朝满口之乎者也地闹革命,牛二很不满,他说:“老魏兵书看多了,走火入魔了,老拿自己当统兵十万的骠骑大将军,操!这么造反岂不是扯蛋乎?”
“长缨”的逍遥派日子没持续多久,就和“井冈山赤卫队”结了仇,起因是牛二和土肥的挑衅。
“井队”的头头苟彪本是个泼皮破落户,天生斜视。左眼险些要“夺眶而出”,绰号“歪把子”,意思只适合用这一型号的冲锋枪,无需瞄准。生理上的遗憾曾让他受够了老师的窝囊气,即使他上课再聚精会神地盯着黑板,给人的感觉还是走神瞟向窗外。当他在放学路上堵住心仪的女孩,殷勤地递上一封情书时,深情的“岔望”让女孩和身旁的女伴同时脸红。女孩无法确定地询问:
“这是给我的?还是给她的?”文革开始后,“歪把子”咸鱼翻身,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一目二看”起到了同时震慑两名“牛鬼蛇神”的效果。他纠合一伙心狠手辣之徒,拉杆子成立了“井冈山赤卫队”,自任司令。往日里矮人三寸,如今是顶天立地的人。歪把子的“井队”从不开批斗会,贴大字报,因为讲不来那么多的“废话”。他们惯于以“破四旧”的名义打家劫舍,认为这才是革命的精髓。其他的造反派都对这群滚刀肉敬而远之。
这一天,“井队”再次行动,把一个老翻译的家抄了,罪名是“吃中国饭,放外国屁。”一家老小都被赶到院子里,三个人负责看管,其他人在屋里翻箱倒柜,查抄“四旧”。牛二和土肥闲来无事,跑去看热闹。此时抄家已接近尾声,歪把子脖上挎着缴获的战利品大摇大摆地走出屋子。战利品是一架构造精良的望远镜。牛二和歪把子同属“天棒”一流的人物,平时惺惺相惜,交情不错,所以打着招呼询问:
“歪把子,又搞到什么好东西了?”
“啊,牛二。缴了一架望远镜,苏修的。”歪把子拍拍胸口的物件。
“噢?我看看。”牛二凑上前,把望远镜架到眼前,四处观望。
“怎么样?牛二。”“啧啧,不赖不赖。”“那是,上次我缴了一架美帝的,都没这个倍数大,苏修的东西是牛逼。”
牛二放下望远镜,来回摆弄着,爱不释手。
“老歪,让给哥们儿怎么样?哥们儿请你喝酒,上‘老进’。”他涎着脸说。
“不干!”歪把子把望远镜抽了回去。
“一条恒大,一把军刺,怎么样?”“不干不干!”“操!你再缴嘛,咋那么抠逼!”“哪儿那么好缴,你当玩呢?”
——“操!”牛二急了,“就你那对斜巴子眼,一看就双影,有个单筒的就行,用它不白瞎了吗?”
这句话戳中歪把子的软肋,他吊泡眼一横,“******妈牛二,你敢这么说我,找揍呐!”
他伸手摸向腰间,那里掖着一支火药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