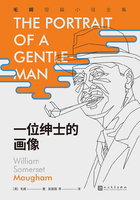“到了长安之后,我们王发现事情果然如他所料,身边被霍光安满了亲信,一举一动都要经过霍光允许,哪像一个天子。我们王气不过,暗暗部署心腹侍卫,准备在七月初七乞巧节这天斩了霍光,却不料走漏消息,霍光反咬一口,以皇太后的诏书废黜了我们王。虽然我们王之前也拿到了霍光的一些谋反证据,可惜兵力不足,功败垂成,最后只能束手就擒。之前他把这些证据交给了我和我的前夫,让我逃出去交给广陵王。怎奈霍光早有准备,去广陵的路上密布关卡,我们根本没法到达,只好先潜回家乡瑕丘,见机行事。我前夫死于逐捕中所受的箭伤,今上即位之后,我知道事无可为,终于冷却了再去广陵的心思。”
我突然想到了什么,打断她道:“前些年霍光已死,他的亲族也都以谋反罪被今上族诛,今上为什么还要逐捕你?就算你身上藏有当年霍光谋反废黜昌邑王的证据,也对今上毫无影响啊。”
“唉,你到底还是稚嫩,想事情总是这么简单。你想想,今上是霍光拥立的,而拥立的理由是昌邑王淫乱,现在我手中的证据能证明当初昌邑王是受了冤枉,那么今上的即位还能算名正言顺吗?今上岂能容忍这种情况发生?何况今上生于民间,地位卑微,当上皇帝完全是邀天之幸,自然格外敏感。”
我恍然大悟,男人们的世界实在是太复杂了,真让人不寒而栗。我吸了口气,道:“我明白了,前两年广陵王谋反自杀,他的奴婢没入县官,其中就包括你的姊姊李惠,而事隔两年,李惠被揭发出和昌邑王还有关联,经过拷问,最终牵扯出了你,所以今上才下诏急着逐捕你。是不是?”
她颔首点头道:“你这个判断不错。其实我从来没想过散布那些和霍光有关的文书。那些事已经是过往烟云,我活到六十岁了,这点事还看不开吗?然而他们是不会这么想的。也好,既然下诏购赏我,我正好趁机帮我的汤儿一把,我这个做母亲的,临死还能发挥这点作用,也算是死而无憾了。”
“你想清楚了吗?”我看着她平静的面容,心里酸酸的,母爱真是伟大,就像我母亲,虽然我做下了那么见不得人的丑行,可是母亲始终站在我一边。她对我父亲崇拜得五体投地,可还是最终承认,在嫁我给王家的这件事上,我父亲做错了。如果不了解母亲对父亲的感情,就不可能理解母亲那个承认是何等不容易。
“当然。根本不用想。”她神色淡然。而陈黑又凄怆地呜咽起来,边呜咽边责怪自己的穷愁无聊,竟然害得儿子入狱,害得妻子要舍身救子。我从他的哭声中努力分辨他的号诉,大意是这么点内容。不过最后几句算有点新鲜,他说,没有妻子,他自己也不想再活下去了。
我终于鼻子一酸,泪水夺眶而出。我能想象陈黑此刻心中的感受,他本来身体残废,没人肯嫁给他,年近四十才从天上掉下一个女人给他做妻子,而且这个妻子不是一般的乡村鄙妇。她曾是王侯的贴身侍女,文雅善书,机敏豁达,给他生了个聪明的儿子,那个儿子虽然有些顽劣,但总是因为不甘心一辈子居贱处微,才做出一些有悖法令的事情。他和这个女子相伴二十来年,相濡以沫,有了她,他才发现了人世间的温暖,现在她下决心要离他而去,他怎能不痛断肝肠?然而,如果不这样,他们的儿子又必须死,两者之间选择一个,他能作出怎样的选择?就算是他想选择,他的妻子又怎么会给他选择的机会?他能做的,只能是面对生死离别的那一瞬了。
李中夫柔声安慰陈黑道:“不要哭了,这么大年纪,在客人面前也不好意思啊。”
陈黑收住了哭声,哽咽道:“你叫我不哭我就不哭,我一向都听你的。可是这次……”他的肩膀一耸一耸。
李中夫道:“别任性了,时间不早了,还是赶快和乐君商量正事罢。”
嫁给王君房也不是没有好处,往常非常困难的事,现在变得很轻易。我直接把李中夫给我的漆盒交给了王君房,由王君房上呈给他的父亲。他父亲大概做梦也没料到会得到这么一次立功受赏的机会,非常兴奋,在堂上走来走去,声音颤抖,连声对我说:“实在灵验啊!实在灵验。我第一次去你家的时候,带了一个相士去,那个相士说你有大贵之相,可以旺夫,看来我们王家今后的发达,还要靠你啊!”
我哭笑不得,如果我真有旺夫之相,应该对子公有利才对。我和子公虽无夫妻之名,却有夫妻之实。而且我还怀着他的孩子。我有点羞愧,感觉实在对不起他们家,垂首道:“阿舅,陈汤的母亲告诉我,一定要救他儿子一命,那么她死亦无恨。母子深情,希望阿舅一定要成全。妾身一向听说凡是治狱,应当尽量多积阴德,让生者不怨,死者不冤,后世子孙就一定会兴旺发达当大官的。”
王县长越发兴奋了,他捻着颌下数根枯黄的胡须,连声道:“对对对,现在朝廷的御史大夫于定国,他的父亲于公,当年也是这么说。于公的家乡就在我们邻近的东海郡郯县,他是当狱吏的,据说凡是由他经手判决的犯人无不心悦诚服,死亦无恨。真是广积阴德,广积阴德啊!后来他的儿子果然当上了御史大夫。依我看,丞相的位置,不久也是他的。你放心,为了我的子孙,陈汤一定会没事。何况按照律令,他本来就算立功,不但不会有事,还能受赏。我现在就去县廷提审陈汤。”
他吩咐立刻驾车,和我夫君一起驰往县廷,我则忐忑不安地在家里等他的消息。黄昏时候,两个人都回来了,王县长见了我,似乎有点怅然若失,说:“我以为劝说陈汤告发他的母亲会费一点劲,没想到我一开口,他就爽快地答应了,真正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啊!唉,枉费他母亲一番爱子之心啊!这陈汤据说还饱读诗书,擅长属文,品德却如此不堪一击,不堪一击!”
我又一次听到他人对子公的指责,心一点点沉了下去。也许子公在道义上真的很不堪罢。一想起他母亲在我面前婉转求情,慨然决心就死的神态,就觉得子公的爽快实在有点说不过去。但是我想看到什么?看到子公严词拒绝、不愿告发其母吗?唉,我不想考虑这么多了,我只知道心里仍割不断对子公的爱,即便子公无耻之尤,十恶不赦,我也放不下,爱情真是一种可怕而盲目的东西,它也是不讲究礼尚往来的,我的夫君对我这么好,可我就是不爱他。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很淫贱无耻。
“他母亲是诏书名捕的重犯,再有爱子之心,又值得什么敬佩了?阿舅难道同情反者吗?”我嘴里无端蹦出来这么一句。
王翁季脸上有点惊愕:“阿萦,你怎么能这么说?陈汤的母亲确实罪不容诛,但在道义上却不是没有可敬之处。那个陈汤自小苦读儒书,岂不知道‘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他的儒书难道都白读了吗?白读了吗?”
唉,大汉的官吏真是越来越呆,个个都把《论语》背得滚瓜烂熟。我知道他刚才说的是《论语·子路》里的话,那些话是说得不错,不管怎么要求公义,如果这世上父子夫妻之间都被迫要互相告发,那实在很可怕。所以今上特地在地节四年颁布了一道诏书,规定父子和夫妻之间的互相包庇是允许的事情。我对这诏书也很赞同。但是,现实中有时又免不了会碰到一些难以取舍的事,比如明明亲人破坏了公义,也曲为袒护,那不就没有公正可言了吗?就拿眼下这件事来说,如果子公假惺惺地表示拒绝,不过是闹得母子俱丢了性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以愚蠢的孝心将母亲的苦心轻易抛掷,这恐怕不是他母亲乐于看到的。我想如果他那样做了,在黄泉之下,他母亲也会恨他的。我脑中快速地这么为子公辩解着,不知道是不是被某种东西蒙蔽了理智。
于是我嘴里又脱口而出:“母子相隐,固然说得不错。不过涉及大逆无道的重罪,也只能弃私恩而取公义了。妾身从小也诵读一点儿儒书,曾闻孔子说:‘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如今陈汤以义断恩,似乎也没什么不妥,就算论起儒家大义,也是说得过去的。”
王翁季的眼睛都直了,良久才叹了口气,道:“你要是个男子,一定可以去长安游宦,凭着这种辩才,俯拾金紫不在话下。”他又转过头对他儿子说:“君房,阿翁为你娶妇如此,也算是功德一件了。永远不要忘记阿翁我的恩德,永远不要忘记。”
我的夫君喜笑颜开,又吃力地张开他那抽屉般的大嘴连声道:“大人,说得是,臣永世,不忘,大人恩德。”
我突然觉得腹中一阵翻滚,干呕了几声。王翁季脸上掠过一丝惊讶,转瞬又欣喜道:“君房,我们王氏快有新苗了。快去叫你的母亲,让她带你妻子去找医师看看。”